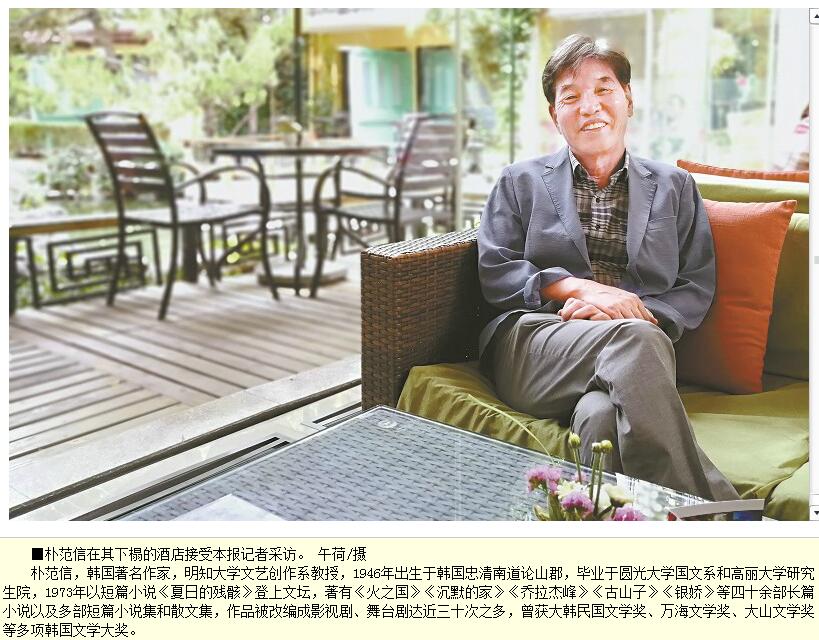  说起韩国文学,一些读者难免将其与韩流、韩剧画等号,然而,有位韩国作家的作品,却一举打破了这样的认知。他,就是被誉为“韩国国宝级现实主义作家”的朴范信。 8月22日晚,2018年中韩文化文流活动在北京驻华韩国文化院拉开帷幕。专程从韩国来华的朴范信,无疑是此次活动的主角。在睿智而风趣的中韩文学对谈中,中国作家毕冰宾(黑马)盛赞朴范信的小说《肮脏的书桌》“充满了力量”,让人感受到了“真正的韩国文学的魅力”。 那么,《肮脏的书桌》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作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什么是韩国文学的主流和特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国作家与中国文化、文学有何关联?如何发挥文学翻译在中韩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等,活动前后,记者就此分别与韩国著名作家朴范信、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思寅进行了对话。 如何转换历史和现实的写作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肮脏的书桌》算得上是您的自传体小说吗? 朴范信:可以这么说,因为里面有很多自传性的要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说过,比起作家的称号,您更喜欢被称作 “艺人”。那么,“艺人”该如何转换自己所拥有的历史和现实的写作资源? 朴范信:我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也说过,每个人内心可能都会有一个恶魔或是野兽,它是极为敏感的,它常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感到伤痛。比如身边掠过的一丝微风,或者是坐在那里的一位老人,这可能像是幼年未成熟的野兽那种非常敏锐的感觉,可能是内心存在的所谓艺术性的自我。这种艺术自我是非常敏感的,可能在路上走的时候,在和人谈话的时候,在看报纸的时候,突然间就伤感起来,这种伤感又会唤起我的种种记忆。我会把现实中受到伤害的自我和那些伤痛唤起的记忆放在一个篮子里,花很长时间去观察它们,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有一天我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我的小说就开始进入构想阶段了。《肮脏的书桌》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把现在的我和过去的历史回忆放在一起思考,揭示和阐明二者之间的关联,从而构成了小说的基本构造。 小说家重要的是想象力,但是想象力不是躺在那里就会出现的东西,只有当作家所处的现实环境,或者遇到的种种事物和其潜意识两者相遇,并发生某种因果关系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想象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韩国媒体称“《肮脏的书桌》是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孤独徘徊的少年的报告书”。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16岁和56岁时孤独的不同状态,以及他在不同阶段反抗孤独的种种尝试,让人感到了一种悲壮和诗意之美。您认同《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吗?孤独对于作家是否具有多重意义? 朴范信:我同意马尔克斯的话。孤独感是文学的子宫,这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讲应该都是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从十几岁到三十出头,曾经有过四次自杀未遂的经历。年龄大了以后,我对自己这种经历有过很多思考。我经常在想: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那么想自杀?这种对于死亡的渴望到底是一种反抗还是顺从?这种思考促成了《肮脏的书桌》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开端。但是最终写出来之后,却只写了十几岁时那两次自杀未遂的经历,20岁后半期和30岁出头那两次没能写到这部小说里,或许将来会写一些短篇。 我出生在一个并不和睦的家庭,从小认识的世界就是不和睦的,充满了冲突。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长大的我,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也是不和谐的、充满冲突的。在开始读书,有了相对客观一些的思考之后,我眼里的世界仍旧充满了冲突。这个时候我就有了疑问:如果我是正常的,那么世界就是疯狂的;如果世界是正常的,那么我就是疯狂的。自我和社会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构成了根本上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的根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人生来就是不自由的、有限的,这种不自由和有限性,这种天生的孤独和对世界的不安,就构成了第一个层次的生命的孤独感。第二个就是进入社会以后,与社会之间沟通不畅所产生的孤独感,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孤独感。我在写小说的时候,主人公与生俱来的孤独感,和他在与社会交流过程中产生的绝望和反抗心理所带来的孤独感,这两种孤独感作为经线和纬线相互交叉,像织成一匹布一样,构建着我的小说。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会拥有这两种孤独感,它们总是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我现在已经70多岁了,依然无法克服这两种孤独感。可以说,《肮脏的书桌》就是一部想要探讨这些问题才着手撰写的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这部小说中,56岁的 “我”,以第三人称讲述16岁、17岁、18岁、19岁和20岁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注视、审视着过去的自己,同时交叉讲述现在的自己,这种形式非常独特,却让人读起来毫无违和感。这是在写作时自然而然形成的,还是对结构进行了一番精心设计? 朴范信:不能说只是其中任何一个。在我年龄大了以后,常常会陷入一种无力感。于是,我有意把年轻时候最热烈、最有热情的“我”呼唤出来,希望他能重新附在我身上。写这部小说时,有一部分像是韩国的巫师在施行巫术时神灵附体一样,是很自然地产生的。但是小说的创作是无法脱离理性的创造化的过程的,所以这两者无法说更重视哪一者,其实是两者的结合。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