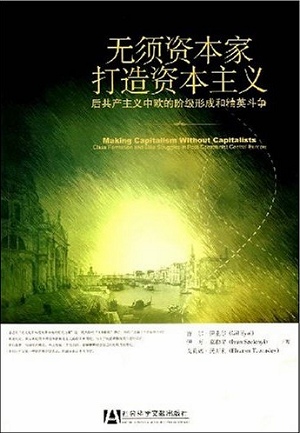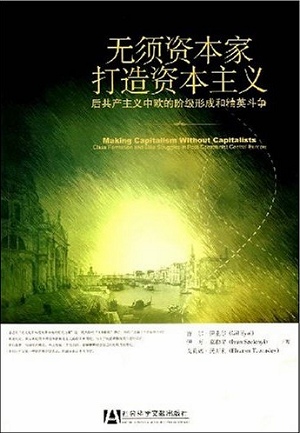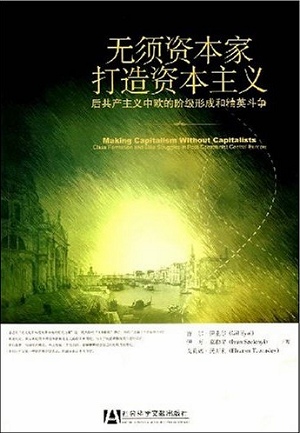
米格
□在读博士生,香港
“从社会主义导向资本主义的轨迹是多重的。”在为《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撰写的中文版序言里,身为作者之一的耶鲁大学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及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伊万·塞勒尼如此总结这本著作的最重要假设。这本著作在十年前正式出版了英文版,并立即成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领域的经典。
通过讲述与分析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资本家缺席的后共产主义中欧地区如何打造资本主义,全书提出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所谓“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指的则是在那些“市场机制被引入之前没有私有财产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技术专家—知识精英所采取的独特的新转型策略”。你或许觉得这段话有些拗口,那么不妨听听塞勒尼教授的一位老朋友、一名澳大利亚工党的忠实支持者对全书精髓的概括:“你们是在告诉我,那些在东欧把社会主义弄糟的家伙,现在又要来把资本主义搞垮吗?”
社会出身的重要性
其实,正如作者在第一章里对20世纪中欧社会结构变迁所发出的感慨,“越是发生大规模的变迁,越是成了同一回事”。面对剧烈的社会变迁时,没有改变的恰恰是社会出身的重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中欧,可以为一个人带来荣耀和特权的因素包括“拥有财富、虔信基督或是贵族血统”,而那时对一个人的羞辱称呼包括“臭农民”或者“腐朽堕落的无产者”,足以引起别人的不信任和猜疑的身份则包括“社会主义者、左翼分子或是无神论者”。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晚期,家族财富与贵族血统却成了遭人歧视或者斗争的凭借,富家子弟与贵族后代成了“从错误的篮子里取出的臭鸡蛋”,相反,“贫农或者无产者的出身,和你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对党的忠诚一起,都是通向权力与特权顶端的快速通道”。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五十年过去了,世界再一次剧烈转向,对社会出身与社会制度可怕的“否定之否定”的诅咒又发生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每个人必须遗忘许多曾经熟识的词汇和逻辑,但同时要清晰地回忆起所有曾被视为异端的行动与历史。
匈牙利学者艾勒梅·汉基什和波兰学者雅德维佳·斯坦尼茨基斯等中欧问题研究专家曾预言,从前的党国精英的主体在改革与市场化过程中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只是借助自己在改革前获得的权力、地位与优势,由再分配体制下的政治精英转变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变迁的事实与这种精英的“再生产”理论丝毫不差:旧的“红色贵族”转变为新的有产阶级,政治权力转换成经济财富。
但出人意料的是,根据本书中提供的数据,在1993年的中欧,只有1%到2%的大企业管理者在1988年时是党务或者政务工作者,读者或许会据此认为上述判断有所夸大。但事实上正是由于理论家们的警告,才“足够使媒体、议会及其专门委员会、社会科学家以及警方开始密切关注私有化的进程,从而使得旧官僚很难轻易盗取国家财产”。如此自我毁灭式的预言未能充分实现,或许未尝不是幸事一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