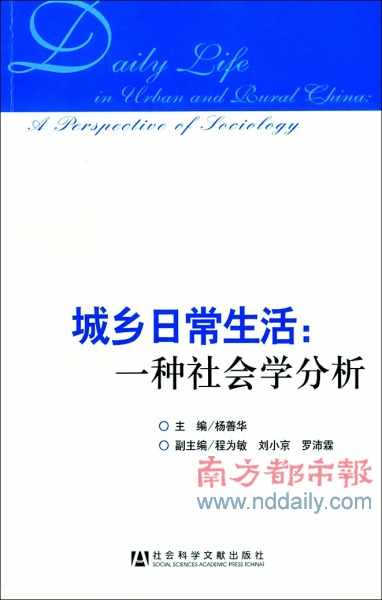 米格 □在读博士生,香港 私人手机 “一个私人的电话号码和一台私人的手机”,当提摩·科坡玛在《口袋里的城市:移动信息社会的诞生》一书中如此表达年轻人购买手机的欲望时,也许不会想到,同样的渴望正在手机生产量占世界市场总份额一半以上的中国生长,甚至正在广东省内只属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群体中蔓延。 罗沛霖与彭铟旎在论文《关于中国南部农民工的社会生活与手机的研究》中向我们揭示的这一微妙事实背后或许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伴随着手机的迅速扩散,面子、性别关系等等在广东的农民工中那些传统的文化要素正在经受冲击;但与此同时,手机使农民工可以与四散各方的家人保持频繁的联系,传统的亲属关系也得到了增强。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工购买和使用手机的最初原因是为了能够与家人的联系更方便更频繁,但当他们被这种永久性的联系吸引后,他们对家庭物质福利的关注却变得更少了———“他们在手机上花费了更多的金钱,虽然他们比以前挣得更多了,但是他们给家里寄去的钱却比以前少了”。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自我意识与群体联系,都通过这样一台小小的机器、这样一个生活细节而奇妙地交会在一起,令人着迷。 这种以社会学的视角来透视城乡日常生活并对其进行探究和反思的方法论思想,正是收录上述论文的《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书中各篇文章共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们都试图对处于变迁之中的中国城乡社会进行学术探索与记录,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把握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的脉搏”。总的来说,它们既本着“长时间、宽视野、远距离”的研究设想来重新检视转型期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又努力去精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种种社会现象以及背后更为深刻具体的意义。 “不爽” 例如,我们或许已经对“农民工”这个名词熟视无睹,但却并不知道,正如王春光早已指出的那样,如果将80年代初次外出的农村流动人口算作第一代,那么我们目前主要接触的90年代后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村流动人口则应该被视为“新生代”:他们年龄更小(外出时平均年龄只有23岁)、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人具有初中以上学历)、没有务农经验、外出动机从经济型转向生活型或者两者并重。只有明白了这点,我们才能理解彭铟旎在《非正式规则:珠江三角洲新一代流动民工的行为策略》一文中的心痛———新一代流动民工群体作为一群依然处于社会底层而且前途渺茫的人,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已经无法使他们在社会夹缝中获取流动机会,而勤奋努力的表现也无法消除他们所体验到的不公平与相对剥夺感。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打破常规的社会运行规则来获取行为意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基础。所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不能为他们自己带来长久的利益与福祉,甚至在短期获益的背后掩藏着更为严重的后果与代价,仅仅是一把流动民工在反抗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双刃剑。但这毕竟是“在一个社会整体结构内部因为社会制度和社会资源安排的不公正所导致的亚群体利益长期被忽视的结果”,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抗与控诉,以及以“即时享乐”的理念在绝望的生活中获取生活的意义。 农民工频繁地辞工或者换工行为正是非正式规则的一个很好例子。这一现象背后不再是简单直接的经济利益因素,而很可能具有发泄愤懑的非理性色彩。台湾某大学科班出身的徐某为了使得企业的管理更趋于现代化,要求每位工人在辞工时都要填写一份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辞工”。出人意料的是,一位工人只用了两个字来回答这个问题:“不爽”。正是这两个字,使得徐某试图了解工人内心想法的努力化为泡影,却也正是流动民工周遭生存状况与焦躁不安的心态的真实写照,是他们为那个带来各种限制与制度壁垒的主流社会的“深度失望与不满”。雇主之所以能够约束员工,是因为手中掌握了工人希望能通过遵循主流社会规则而获得的资源与机会,但当新一代流动民工意识到自己能获得的雇主青睐、社会认可与资源机会极为有限时,“他们便不再忌惮对主流社会规则的破坏所带来的惩戒,因为主流社会已经无法从他们那里再夺得更多的资源了”。这样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