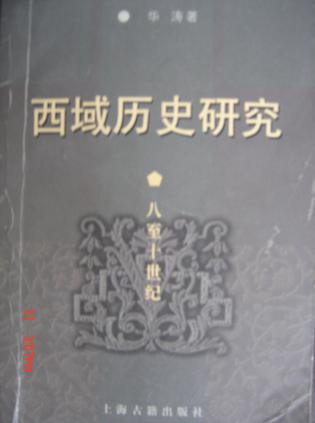 华涛先生《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直接、系统地利用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内陆欧亚史,在我国内陆欧亚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华涛先生《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直接、系统地利用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内陆欧亚史,在我国内陆欧亚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书着重研究的是天山地区伊斯兰化前夕突厥语族的历史。全书分为四章:一、8世纪中期以后葛逻禄在西域的活动;二、回鹘西迁及突厥语部族在西域的活动;三、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四、西部天山突厥语部族的分裂和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活动。前三章研究伊斯兰化前夕和伊斯兰化开始时期天山地区诸部族的构成,及其与周邻居民,特别是与河中穆斯林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第四章研究该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附录包括两篇独立成文的专题研究:一、喀喇汗王朝王室族属问题研究;二、扎马勒·哈尔息和他的《苏拉合词典补编》;以及史料及主要参考文献(包括穆斯林文献、古今汉文文献、现代西方文献)、阿拉伯、波斯等史料书名对照表、缩略语表等。 正如作者所指出,天山控扼着欧亚大陆上最重要的东西交通线——丝绸之路,古代世界东西南北几大文明在此交汇,历来是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公元六世纪起,突厥语诸部族也向这一地区发展,并在八世纪中后期和九世纪中期唐朝和吐蕃分别退出以后,成为天山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降至十世纪中期,西部天山地区的突厥语诸部族更开始了意义深远的接受伊斯兰教及其文化的历程。由此可见,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不仅有学术的兴趣,而且具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这一时期的天山历史便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东西方各国的优秀学者。其中最有成就的当推俄国/苏联学者巴托尔德,他的一系列论着,如《七河史纲》、《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突厥斯坦简史》、《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等,均脍炙人口,至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巴托尔德之所以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注意发掘和利用阿拉伯波斯史料。 如所周知,随着古突厥碑铭的释读和突厥学取得长足进步,以及对天山地区实地考察的逐步深入,与这段历史有关的穆斯林史料也开始受到关注,陆续被整理出版。就资料研究而言,最有成就的是米诺尔斯基。他翻译、注释了《世界境域志》、马尔瓦兹著作的有关篇章和《塔米姆回鹘游记》等,为这段历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国对天山地区历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兴起,而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因接受了西方的治学方法,研究有所深入,但从整体上看,直至本世纪70年代末,仍远远落在外国学者的后面,与国际水平差距的缩小,可以说只是最近二十年内之事。 按理说,由于相对丰富的汉文史料的存在,我国学者对于上述课题是有较大发言权的。汉文资料有其优长之处,自不待言。问题在于涉及这段历史的许多问题仅凭汉文资料无法解决或彻底解决。国内有关研究之所以长期落后,原因之一便是我国学者对于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史料亦即穆斯林史料的注意非常不够。 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的研究虽然功不可殁,但他们的共同欠缺在于不能直接利用有关的汉文文献。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研究均侧重于天山西部,未能将天山地区突厥语诸族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因而也就不能不留下许多缺憾。 由此可见,要使8-10世纪天山地区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在现有基础之上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必须将有关这段历史的两种最重要的资料即汉文和穆斯林史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华氏著作的出版,可以说迎合了这一时代的需要。 作为中国学者,华氏在挖掘和利用汉文资料方面自然应该比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外国学者略胜一筹。尤其可贵的是他精通阿拉伯语,能够直接读译穆斯林史料原文(全书引用重要的穆斯林史料近三十种),具备了将这两种基本史料参照、对比、补充、印证的基本条件。这弥补了无法利用汉文史料的西方史学界和较少关注穆斯林史料的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的缺憾。由于作者不是将这两种史料简单地剪接拼凑,而是凭借过人的史识驾驭之,使之水乳交融。于是,一些历来没有被注意到或者一直被误解的问题得到了较好的阐明。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否定了国外一些著名学者关于伊斯兰化前夕(公元十世纪)中期天山地区存在一个突厥语部族大帝国的论断,阐明了当时天山地区的突厥语部族正处于大分裂中的历史。这对于了解公元十、十一世纪的天山地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正如许多古代欧亚史的课题一样,有关原始史料往往有好多种。纵然对于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作用并不相同,而在很多情况下,任何一种都不可或缺,研究者只有充分调动各种史料,才有可能逼近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华氏书除运用汉文和穆斯林史料外,也充分注意利用和田语、突厥语和藏语的有关资料,从而使历史的画面更加清晰,使结论更趋精确。 除阿拉伯语外,华氏还精通多种现代语言,使他能够充分借鉴和利用各国学者有关的成果,除上述巴托尔德、米诺尔斯基外,其研究上承沙畹、伯希和、哈密屯,旁参日本(羽田明、安部健夫)和国内学者的论着。正因为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使他对穆斯林史料和其它原始史料的利用,与一些只能直接啃原始史料者,其效果又不可同日而语。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