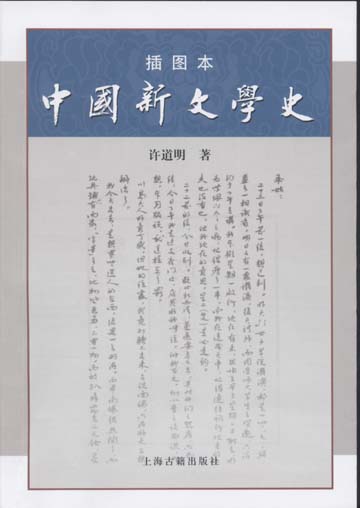 何为中国新文学,胡适先生曾经赠其八字:“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文学工具的革新,“人的文学”指文学内容的革新,从这两个革新,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学是相对于传统旧文学而来的,这也说明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许道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插图本)》,所选取的时间范围大致是从19世纪初到解放前30多年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历史,之前还上溯到18世纪末的近代文学寻求新文学萌发的种子,从行文开始,就显示了旨在厘清传统、西方和中国新文学关系的目的。而整本文学史以“回望五四”作为结束,书写了七月派、九叶派、《文艺复兴》月刊在主流文学——人民文学的巨大阴影下对“五四”传统的景从。这样的安排方式给了读者一个暗示:这本文学史所专注的并不是那争论不休的现代文学时间上的考订,而是对解放前中国新文学的“五四”传统从起于萍末到濒于式微一个阐释。 何为中国新文学,胡适先生曾经赠其八字:“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指文学工具的革新,“人的文学”指文学内容的革新,从这两个革新,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学是相对于传统旧文学而来的,这也说明新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厘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许道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插图本)》,所选取的时间范围大致是从19世纪初到解放前30多年的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历史,之前还上溯到18世纪末的近代文学寻求新文学萌发的种子,从行文开始,就显示了旨在厘清传统、西方和中国新文学关系的目的。而整本文学史以“回望五四”作为结束,书写了七月派、九叶派、《文艺复兴》月刊在主流文学——人民文学的巨大阴影下对“五四”传统的景从。这样的安排方式给了读者一个暗示:这本文学史所专注的并不是那争论不休的现代文学时间上的考订,而是对解放前中国新文学的“五四”传统从起于萍末到濒于式微一个阐释。这本文学史的第一章《“五四”话语的形成》是整本文学史的统摄灵魂,渗透到其后面十三章内容的编写中,这十三章又可以说是对“五四”话语的解释和演绎。 《进化论与近代文学》居于这本文学史的开篇第一节,彰显了作者对中国新文学史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认识:中国的文学史虽是西方各色学理催生出来的产物,可也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文学这一方沃土,中国的新文学从来都不是和旧文学断裂的,中国新文学这个逆子也是从传统中国文学的痛苦分娩中诞生出来的,新文学的血液中天然带有传统的因子,这是推动新文学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让新文学得以反省自身的动因。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所具有的“小传统”,也就是李欧梵称之为“抗传统”的异端思想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偶像崇拜的态度核心。 在这一节中,作者标举了三个近代精英对进化论的拥护,即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这三个精英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并且以思想的复杂性见著于世,作者也别有用心地提醒读者,梁启超既有启发五四之功,也有和五四相左的立场,质疑科学万能,嘲讽写实文学,而王国维拿来西方的新理论却治旧学,他们既是现代的,又是反现代的,同时作者还给出了一个俯瞰中西方的视角:“中国知识者醉心于西方,而西方世界本身却已日渐暴露出难以克服的弊端”,以上种种都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发生、发展、流变、反思做了注脚。透过貌似单纯、激进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表面,作者向我们揭示了五四新文学倡导者良苦的用心:全盘西化只是手段,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中西贯通,生出一个中国文学自己的“宁馨儿”。这是五四新文学的曲折之处,也是作者在编写三十多年的中国新文学史时极力揭示给读者看的。“现代性”与“反现代性”,“西方”与“传统”,就是在这样惨烈的双重夹击下才有了鲁迅反抗的绝望,有了周作人从大鸣大放的文学革命到闲适小品的转变,有了京派作家群对理想的“乡土社会”的虚构,有了张爱玲、苏青们的新市民文学,有了胡风在新人民文学主流下的战叫;浮泛在表面的是问题小说的天真,普罗文学的简单激进,新人民文学对“五四”改写的粗暴。作者以五四新文学传统在中国三十多年历史的流变作为切入口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化与民族化进程”这一宏大主题,关于对这个主题的把握散见在整部文学史的各章各节中。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