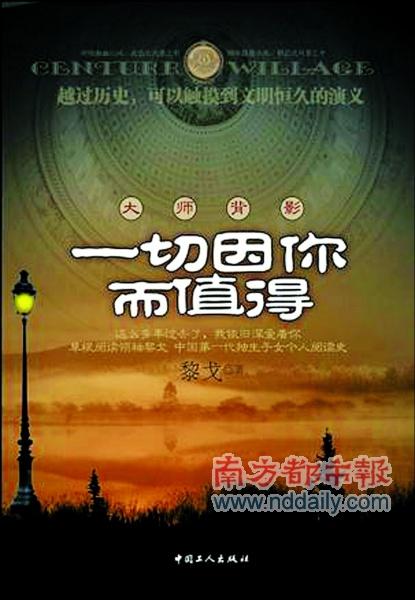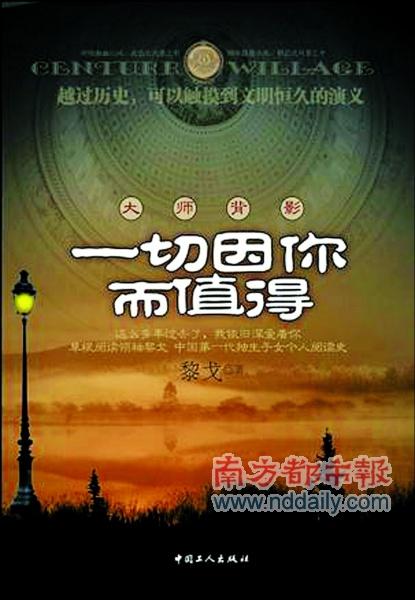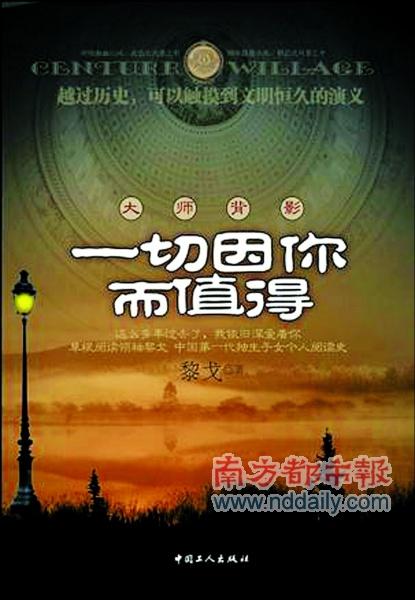
□自由撰稿人,上海
早上起床,窗外是个薄云天,我便就着半昧的天光继续看,这一看就看出这本书有很多技术上的不足:译笔喑哑无光,文字密度忽高忽低,流速不均匀,兴奋点的分布是散乱的———这些都使它文气不畅,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它是一部书信集和回忆录而不是一部小说,它的文字不精纯,但是它……性感,它有灼热的欲力渗透其中。我如此细究它的煽情技术,实在是可笑和罪过的,那是一个正在爱的女人,在爱的光影遮蔽中,她淹然百媚,字字关情,而我,我时常希望自己是个通媚人之术的女人,至少———是个行文妩媚的女人,然而,这两点,我都做不到。(黎戈《圣·埃克絮贝里:玫瑰信札》)
四年前,我表白过自己的阅读立场:“我自以为是个文学美色的追逐者,见到漂亮文字,双脚立刻发软,立场立刻动摇,心意立刻扑腾,情感立刻投诚。向天下好文抒发我的‘登徒子好色赋’,乃是我自封的人生使命。”当我在“清明上河图”般嘈杂的文字市廛里蓦然邂逅黎戈,顿有“正撞上五百年前风流业冤”之感。暗想,在我近年阅读中,如以女性散文家为限,之前读到周晓枫的散文,隐然亦有此感。坦白一下,即使把标准扩充到男性散文家,黎戈和周晓枫在我心目中的前茅地位,仍然纹丝不动。你要知道,我对文学美色的理解,本身是超性别的,并不会随作者的性别而犹疑不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