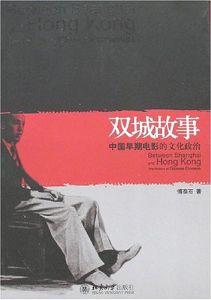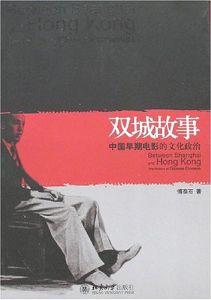“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
傅葆石的《双城故事》强调:“电影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浸透了生产时代背景中的各种社会状况。”
罗 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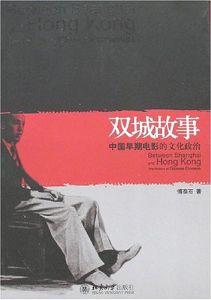
《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
[美]傅葆石著
刘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2月第一版
245页,38.00元
将“早期中国电影”和生产这些电影的城市——“上海”联系起来,并不是近年来随着“上海热”的兴起而产生的叙述策略。早在1983年,柯灵发表《试为“五四”与电影画一轮廓:电影回顾录》时,他就注意到“电影”与“上海”的关系:“鸳鸯蝴蝶派,文明戏,电影,孳生地都在上海,鸳鸯蝴蝶派和文明戏一样,集海派作风之大成,是同气连枝的兄弟行。要了解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结晶状态,‘十里洋场’的社会面貌,都是最完美的标本。电影正当童年,天真未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自然容易和鸳鸯蝴蝶派、文明戏合流。” 尽管他的论述依然服从于中国电影史的主流叙述,套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准,把中国“早期电影”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的受“鸳鸯蝴蝶派”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复杂化为好莱坞电影模式和都市大众趣味的结合——的“海派电影”,和第二个阶段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复杂化为阶级分析话语和新文学趣味的结合——的“左翼电影”。因此,从这种叙述出发,中国电影的黄金时期兴起于三十年代初期,孙瑜、蔡楚生、吴永刚和程步高等导演的电影作品成为“左翼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典范之作”。但不容忽视的是,柯灵却并不认为这两个阶段是“断裂”的,相反他在文章中不断地强调两者的“连续性”:“早期电影作品中,也不乏制作态度严肃,内容较有意义的作品”……即使到三十年代“左翼电影”兴起时,早期电影中的著名导演如“郑正秋、程步高、李萍倩、张石川、卜万苍,都创作了和他们旧作迥然不同的进步影片”, 这些导演的转向本身就证明了电影历史的延续性。
然而,与柯灵这种注重“转折”的“延续性”叙述不同的是,近年来海内外对“早期中国电影”——特别是“左翼电影”——的研究却倾向于消除“转折”,放大“延续”。一种倾向是着眼于电影模式的“延续性”,发现“左翼电影”虽然在政治态度上堪称“激进”,这种激进性却由于模仿美国好莱坞电影形式及风格——尤其是模仿连贯性剪辑和通俗剧(melodrama)类型——而被削弱。譬如毕克伟(Paul Pickowicz)就认为孙瑜的《小玩意》虽然抨击压迫和社会不公,却无视“五四”社会分析原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细腻之处,“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情节剧式的两极处理,包括善与恶,城市与乡村,母亲与情妇,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现代的外来时尚”。他甚至有点夸张地指出,《小玩意》一片的 “马克思主义入门有赖于通俗剧模式的夸张修辞来赢得大众”。(《“通俗剧”,五四传统与中国电影》)毕克伟的观点虽然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譬如著名电影史学家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就认为这一批评不仅对情节剧理解单一、态度鄙夷,而且禁锢于文学标准(“五四”现代主义的标准),不愿考虑视觉、叙事和表演的风格——这些为电影特有的品质使这批电影在世界无声电影中跻身于最成熟、最激动人心的作品之列。(《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但这些批评大多还是停留在具体问题的讨论上,没有更深入地发掘毕克伟之所以会得出如此结论,全因为在他眼中,“早期电影却比五四小说更‘现代’。小说家们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中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而电影则因为本无传统可言,反而免了这一转化中的情感纠葛。” 尽管在这段论述中,毕克伟给“现代”特意打上引号,他却没有仔细辨析自己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从上下文看来,他似乎把“现代”等同于“美国好莱坞”:早期中国电影“因为以营利为目的,拍电影的人完全照搬好莱坞那一套,因为那一套在生意方面行之有效”。实际上,包括电影和文学在内的“叙事作品”都应被视为“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叙事行为”(literatur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不能简单地将其归类为“现代”或“传统”,在讨论与“早期电影”差不多同时的“鸳鸯蝴蝶派文学”时——众所周知,“鸳鸯蝴蝶派文学”与“早期电影”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唐小兵指出,“鸳鸯蝴蝶式通俗文学在表意上可能会认同传统的前现代的价值和观念,但在运作上却是对现代平民社会的肯定,对等级制和神圣感的戏仿和摒弃。”(《蝶魂花影惜分飞》)所谓“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运作”指的是这类文学的生产、制作和发表方式必须依赖于“现代”的商业和传媒业,同样,“早期电影”的“现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得以成立,但难道你能说,“五四新文学”就自外于这一由大众传播媒介以及相关的社会、文化机制所决定的“现代性”吗?
与这一仅仅从电影内部出发的倾向相区别的,是另一种关注“早期电影”商业环境的倾向,正如毕克伟说的:“中国影业的先驱们是从商业利益出发,有效地利用了电影这一媒介”,如果从“商业性”的角度来看,“左翼电影”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鸳鸯蝴蝶派”所创造的商业环境。由此,盘剑提出了所谓“海派电影”的概念:“海派电影既指一种与特定文化形态密切相关的电影流派,同时也指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阶段,即以现代商业大众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海派电影阶段”,按照他的划分,“左翼电影”也属于“海派电影”,在培养“现代大众”方面继鸳鸯蝴蝶派之后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功。(《选择、互动与整合——海派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及其与文学的关系》)尽管柯灵早就注意到“左翼文人”对当时电影界的全面渗透是相当成功的,而这种成功首先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用当时通行的表述就是大量由左翼文人参与的电影,获得了社会的欢迎:“夏衍、阿英、郑伯奇就是冒着冷淡和歧视的洪流,接受明星公司邀请,去当编剧顾问的。不但自己去,而且输入一批文学、话剧、音乐、美术方面的进步分子。聂耳、任光、贺绿汀就在此时开始创作电影歌曲,许幸之、吴印咸也是此时加入电影界的。艰苦的工作从不亏待人,坚冰融解了,局面改观了,电影界终于以成批面目一新的作品,赢得社会批准,争取到和其他姊妹艺术(包括文学)携手共进,平等相处的地位。” 然而,在盘剑那儿,则将同样的事实加以反转论述,与其说是“五四”精神在1930年代初期凭空创造了“左翼电影”的奇迹,不如说是受“五四”影响的“左翼文人”克服了以往的精英文化偏见,有意选择了1920年代鸳鸯蝴蝶派因“通俗化”而成功的电影叙事模式,推进当时电影转型中“革命文艺与商业文化的双向选择”的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