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 作者:(美)彭慕兰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作者:(美)彭慕兰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8月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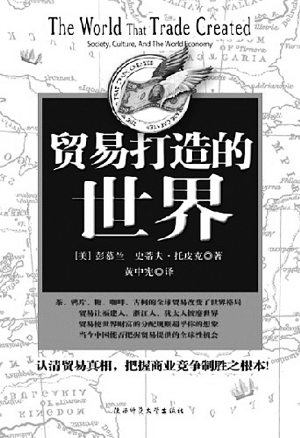 《贸易打造的世界》 作者:(美)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定价:38.00元 □本报书评人文木 陆地与海洋 新世界的展开 1400年的世界,是我们通常所谓的中世纪的尽头。 1405年,刚刚从侄子手中篡夺了皇位的明成祖朱棣派遣规模巨大的舰队远航西洋。在今天意义上,西洋是指南中国海与印度洋海域。据《明史》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无论是踪迹惠帝(即靖难之役后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还是耀兵异域。两者的目的,都是强化成祖继位的政治合法性。史家考证,郑和舰队载有两万的兵员,这支极其庞大的远征军,曾经成功平定南洋某岛国的内乱。成祖的继位者明仁宗与宣宗废弃了大规模的下西洋之举,1430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中国古代王朝动用国家力量征服海洋的事业至此终结。在新世界即将诞生的前夜,中国告别了世界。这,是我们熟知的历史叙述。 彭慕兰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中为明王朝的海洋政策做了辩护,彭慕兰认为,明帝国的军事中心并不在于武装拓殖海外殖民地,而在于对抗北方少数民族的防御性战争。对于明帝国来说,失去海洋,并没有任何政治和商业意义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彭慕兰又从商业角度论述了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东南亚,这一区域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始终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商业区域,来自西方的阿拉伯和印度商人与中国(尤其是福建)商人以马六甲海峡为中介,沟通整个亚洲大陆。这些商品甚至被阿拉伯商人大规模地贩往欧洲,以获取暴利。瓷器、茶叶与丝绸,成为中国在欧洲的代名词。 然而,新世界的展开,不在于明王朝温和的“耀兵海外”之举,也不在于南洋商业的繁荣,而恰恰是赤裸裸的武装殖民拓殖战争与屠杀。彭慕兰说,新大陆(美洲大陆)的“发现”,正是一个极端的巧合。曾经的职业海盗、四处钻营巴结的无耻小人、深信中世纪天圆地方说的愚昧教徒哥伦布以对黄金的无限渴望,从错误的航海方向发现了今日的西印度群岛,并终身不悟地以为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道。哥伦布带给欧洲的惊喜与激情如果说是创造新世纪的冲动,毋宁说,是欧洲对于黄金的冲动。新世界的开始,源于黄金的渴望。或许,还可以加上一个温情脉脉的理由,是欧洲向世界传播基督教的渴望。 1500年,新世界的曙光即将到来,在欧洲大陆泛起武装拓殖掠夺财富激情的时候,东方世界仍处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与对抗之中。 海洋的冲动 泛欧洲化与现代世界 在彭慕兰的另一本引起国际学术界轰动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彭慕兰通过大量的例证证明,迟至19世纪初,东西方的“大分流”才真正形成,而在这之前,中国的江南区域在19世纪之前一直是世界最为富庶的地区。在后设史学的论述中,欧洲(尤其是西欧)成为经济现代性的典型范例,中国的江南则成为“资本主义萌而不芽”的反面例证。西欧的经济现代性的动力,往往被归因于17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彭慕兰从反方向设问,是什么使得经济落后于中国江南的西欧发生了工业革命?答案是生态危机。 在资本、劳动力高度密集,商业与短途贸易高度发达的中国江南区域,至18世纪末,遭遇了发展中最大的瓶颈“资源与生态”危机。江南的瓶颈,表现在手工业与制造业需要的煤无法自给,由于巨大人口压力,无法实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大量种植,比如棉花。由此导致了技术革命的落后。与之相反的是,作为17至18世纪海洋武装拓殖最成功的国家英国则突破了生态瓶颈,本地浅层大量的煤矿的发现解决了能源不足的问题,北美殖民地的大量的良田解决了土地的受限。新技术的革命,首先是煤炭使用方法的革新(蒸汽机)与沟通欧洲与美洲的远洋运输技术的革新(轮船)。江南与西欧的“大分流”,根源正在于海洋事业的展开与否。《贸易打造的世界》一书告诉我们,江南的商人(尤其是福建人)大批前往马六甲海峡,将中国的产品贩卖给印度人与阿拉伯人,但这一活动并没有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在大多数时候,作为内陆帝国的国家反对(或者不支持)这种有辱国家身份的贸易活动,更遑论派出大规模的舰队保护商民的利益。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