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保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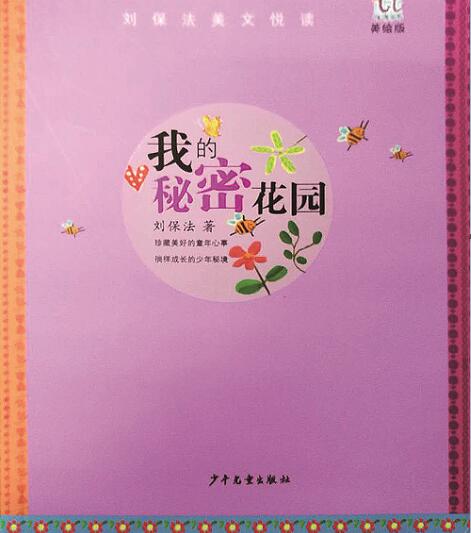
《我的秘密花园》
读刘保法先生的散文集《我的秘密花园》,不禁为作品中的“童年体验”和“生命情怀”所打动。50篇诗文,分成“童年回忆”和“城市生活”两个小辑。初看,两者分属“童年”和“成人”两个年龄范畴,时间跨度大不说,还各自独立叙述,似乎有种疏离感;细品却顿觉前后呼应、珠联璧合,有内在逻辑和深刻关联。不仅如此,该诗文集还涉及到一个深刻的文学命题:在儿童文学中,童年和成年的关系该如何把握,如何表达。
其实早在18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华玆华斯就曾以“儿童是成人之父”这样的诗句道破了童年之于人生的意义。童年是人生之基,是生命的源头。当孩子一天天长大,固然可能逐渐丧失了天真、单纯、率性、自然等许多童年心性,但是,童年体验和记忆却早已经融合为潜意识,化入了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当中,成为他心灵结构的一部分,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生命观和情感态度。基于此,“童年与成年”的关系,可谓儿童文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从《小意达的花儿》到《铁路边的孩子们》,从《北风后面的国度》到《长袜子皮皮》,从《我亲爱的甜橙树》到《追风筝的人》,从《绿山墙的安妮》到《哈利·波特》……一部世界儿童文学史,很大程度上,就是“童年”与“成年”的关系变迁史。
而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涉及这一命题的作品也很多,如凌叔华的《搬家》、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任大星的《双筒猎枪》、刘健屏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张之路的《羚羊木雕》、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一个女孩的心灵史》《小青春》《宝塔》、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等等。
刘保法的《我的秘密花园》也涉及到这一儿童文学主题领域。所不同的是,以上所列中外作品,多从虚拟角度,从“自我”和“他者”的关系方面表达这一命题,而《我的秘密花园》却是从写实层面,由“童年自我”到“成年自我”的纵深感视角展开,从自我童年记忆到成年生活态度的内在拓展来揭示童年与成年的内在关系。
首先是“童年”向“成年”延展、拓进。这在作品中,体现为“秘密花园”体验对于“城市生活”的孕育。
上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新童年社会学”研究曾提出“社会建构论”。社会建构论认为,童年是变动不居的,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童年形态。在此基础上,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共同性、普遍性的童年,童年的千姿百态是儿童以自己活跃的行动、积极的态度在成人社会、成人文化的缝隙里建构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更不是成人恩赐的结果。
《我的秘密花园》里,作家以清新的文笔、饱满的情感追述了童年时代“我”徜徉在“秘密花园”里读书、种树、捉鱼、 捕虾、嬉戏的生活,这是属于“我”的独特童年体验。在这份体验里,“我”不仅仅是自我童年的经历者,更是自我童年的发现者和建设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童年回忆”小辑里,很多篇什的叙写中,“我”的观察和体验都是在“空中躺椅”上完成的。而“空中躺椅”是怎么来的呢?是“我”用树枝在老榆树上搭建而成。于是,这个“空中躺椅”成了“我”读书、唱歌、看月亮、吃番茄、藏秘密的好去处。“我”的诸多快乐体验由此而来。除了“空中躺椅”,“秘密花园”的另一个焦点是“小树林”。小树林是怎么来的呢?“童年记忆”系列散文一开篇就交代了,“那时候,我正迷恋于种桃树”,“我在那里开辟了‘米丘林园地’,种桃树、种李树、种葡萄,学着嫁接,忙的是不亦乐乎。我还在池塘边挖城堡,捉来小昆虫养在里边……”所有这些描述无不表明,“我”的“秘密花园”一部分是大自然的赐予,另一部分则来源于我的童年发现和创造。这就写出了儿童在生活面前的主体性。他们在特定时代相对贫瘠和单调的现实生活面前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而是心思活泛、朝气蓬勃、行动活跃的生活参与者、发现者、创造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整个“童年回忆”小辑的22篇作品都是以“我”的个体性视角回溯童年往事,写的是一个人的童年体验,但实际上,通过“我”对“秘密花园”的发现和创造,作者写出了孩子在生活面前纯真、自由、昂扬、乐观的童年心性和他们善于在生活中发现乐趣、创造惊奇、捕捉美丽、追求超越的精神风貌,因此,这种看似独属个人的“秘密花园”其实已具备了书写一代童年的典型意义。原因就在于,在“我”对“秘密花园”的发现和创造中寄寓着不同时代儿童生命中默默流淌、生生不息的童年精神。
其次是“成年”向“童年”的回溯、复现。这在作品中具体表现为“城市生活”对“秘密花园”记忆的反哺。
通观整部文集,如果“我的秘密花园“仅仅只有“童年回忆”一部分内容,那么这本书是单向度的,它充其量是当下诸多童年回忆散文中的普通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城市生活”成人视角的28篇诗文,彰显了“秘密花园”的特色,也让此前的“童年回忆”显出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和深度。
在阅读中,我注意到,在“城市生活”这部分文字里,作者花了诸多笔墨写自己的“森林情结”。无论是购房时不辞辛劳四处寻找森林时的满怀期待,还是为窗外蝴蝶的出现而欣喜若狂;无论是为早春竹笋逃亡忧心忡忡,还是替夏日小区花园里树木焦渴而心急如焚……无不透示着作家童年记忆的影子。童年的“我”对小树林里栽种树木的迷恋,对在“空中躺椅”上自由阅读的陶醉,对在林边池塘中捞鱼捕虾的眷念……全部在“我”寻找城市绿地和都市森林的渴念中隐隐闪现。这不是作为成人闲极无聊的附庸风雅、刻意安排,而是童年记忆在成年生命里的返照与复现。这不止是情感迁移后的心灵慰藉和替代性满足,更是童年生命在跃上新阶梯后,在更高层面上显现出来的一种生命观和价值态度。正如作者在《买了一个森林》中所说:人追求诗意居住的最高境界,不仅是美化环境,更应是自己的灵魂跟森林的互相契合……人无法成为永恒,但人的灵魂却因为森林而能成为永恒。
在这里,从童年的“秘密花园”到成年后的“城市森林”,固然光阴荏苒,时移世易,但童年所奠基、所铸就的那份对生命的珍惜,对自然的眷恋、对自由的热望、对诗意的求索却渐渐随岁月在心底沉淀下来,由涓涓细流而浩浩荡荡,最终澎湃成城市森林里的执著求索、静观默察、潜心叹赏、流连忘返……及借助文字,对这份情怀、体验的多重渲染和尽情书写。
在笔者看来,在《我的秘密花园》里,作家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完成从童年“小树林”到成年“城市森林”的情感升级和心灵对接,就在于“童年是成年之基”“儿童是成人之父”,成长不仅仅意味着失去,更意味着生命的不断扩张与超越。而一个趣味清雅、心神安定、境界高远的成年人,当他一路走来,其生命之树的健硕、繁茂必然离不开童年所给予他的自由、昂扬、清新、明媚的情感、记忆的滋养。
这里的全部奥妙就在于:童年与成年一样,同是生命的基本结构,两者之间是和谐共存、相融相生的。童年滋养了成年,成年在更高层面上又延续和复活着童年,其中一脉相承的则是生命成长的内在逻辑和精神旨趣,具体说就是自由、率性、真实、磊落、无畏、超越的童年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秘密花园”其实是一个意象,如同彼得·潘的“永无岛”、泽泽的“甜橙树”一样,它不仅表征着“我”的童年心灵渴望,也寄寓着作家成年后对逝去童年的缅怀和珍惜。面对斑驳迷离的现实,是让曾经的“秘密花园”沉寂荒芜,还是让它在心灵层面重现生机与活力,这无疑就成为一个成年人心灵生活的分水岭。刘保法本性是个诗人,他不仅在物质贫乏的童年时代发现并创造了绿荫如盖、清波荡漾的“秘密花园”,而且成年后,还能够于喧嚣迷离的现实生活里拥有一座小鸟啁啾、古木参天的城市森林。这很令人羡慕。这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生命观、价值观和人生境界的生动体现。希望在都市这个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每个人都能和刘保法一样,诗意地栖居,寻觅到属于自己的“秘密花园”和“城市森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