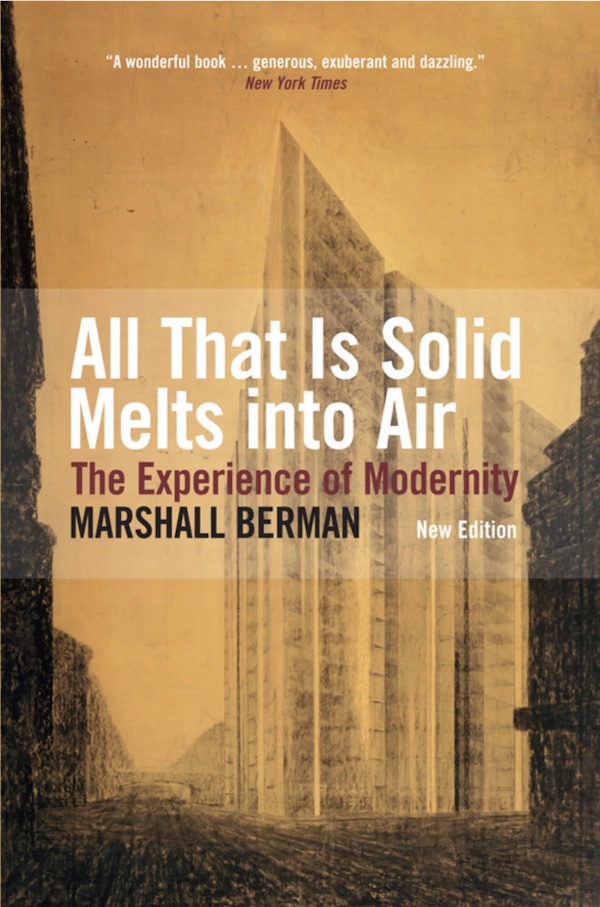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这里,我们不妨把盖伊的专著和其他现代主义论述略作比较。马歇尔·伯曼同样以纽约为自己的写作基点,他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英文初版1982年,中译本2003年)同样纵论一百年间的“现代性体验”。但如果说,盖伊满足于现代主义固化为新的“审慎趣味”并成为“新新人类”们的大学功课,那么伯曼的落脚点则是呼唤先锋文艺恢复十九世纪的辩证能量,克服二十世纪的扁平商品化,重新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场。伯曼上世纪的激情不仅是文化抱负,更是政治欲望。而在盖伊总结现代主义的今天,对更具批判力的新现代主义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已经式微。盖伊直言自己是历史学家而不是算命先生,不准备展望未来,而只保持谨慎乐观(387页)。但当他说现代主义可能“死而复生”(第九章)时,“死”已经是毋庸讳言的结论,显然他觉得落幕未尝不是大团圆结局:“从往昔一路走来”,现代主义已经够长命、够好命了(389页)。  詹明信:The Modernist Papers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对现代主义的“历史化”也和盖伊的“历史化”大异其趣。如果说盖伊表面上回避“大叙事”,却又以资产阶级作为不可置疑的历史主角的话,那么詹明信则勇于探求“总体性”并由此对现代文化做全面诊断。在詹明信看来,一切现代性都是同一个现代性的代名词,那就是资本主义。现代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始强力推进但又尚未完成的历史冲突过程中。今天现代主义渐次隐退,并非因为创新能量已经耗尽,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然完成,原有保守和革命的各类冲突不再构成核心的历史体验。于是现代主义失去土壤,晚期资本主义进入享受一切先锋派既有成果的后现代主义和超稳定结构。如何跳出这一结构,跳出已知的历史叙事套路,重新体认过往现代主义的文化政治能量,是对任何后来者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