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头记会真》 海燕出版社二○○四年五月出版十卷共计五百万字 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校订 此刻执笔为 文,是2004年6月25号。回忆56年前的这一时节,正是我走访胡适先生并借得《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一珍贵典籍,携回燕京大学“四楼”(未名湖畔的第四座“画楼”宿舍)。就在这年暑假期间,我与家兄祜昌费两月时光,抄得一部副本,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有正书局的《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 这是第一次提出“三真本”概念的历史纪程,这三部抄本是当时仅为世知的佳本。 《程乙本》是胡先生提倡,由亚东图书馆排印的,行世至解放后亦达80年之久。 我彼时年轻,说话憨直,胡先生并不计较,却立即复信说:“我对于你最近的提议———‘集本校勘’———认为是最重要而应该做的。但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1948.7.20) 暑假后,自津返校胡先生就烦孙楷第先生(中国版本小说研究的首席学者)把一部二十册两大函的大字《戚序本》捎给了我。此书当时也很稀少,胡先生用报纸包好,以很浓的朱笔大字写在外面:“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 这就是“五十六年一愿酬”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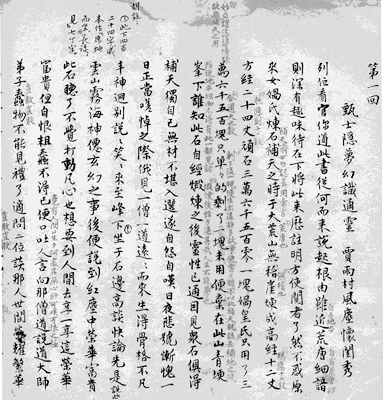 手抄甲戌本第一回 正如胡先生所云,这个工程是太繁重了———但问题不仅仅是个繁重与轻易的事情。五十六年的经历,罄竹难书,也非局外人所能想象,那真是“为芹辛苦”,磨难千端,灾秧百态。 今天,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方告梓成。一愿已酬,百感交集! 胡先生早作古人,那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而家兄祜昌亦在1993年辞世。他们俱不及目见这部印本,我不知以何言词表我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56年了,在《红楼梦新证》的倡导和影响之下,早有专家本着捷足先登的精神作出了各种“校本”了。这时又印出《会真》,还有意义吗? 56年了,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难道如此意义重大的工程,就无一个“热情、侠义”之士,肯为伸出学术道义的援手,给以关切和支助吗? ———这么一问,问得我可真是满怀惭怍,自愧无词以答。 实际上,为了酬此夙愿,矢志无悔,也是曾经千方百计,不惜“捨脸”,向人求助过的。但命运还不如刘姥姥,她是脸没白捨,幸运非凡。我则一计无成,只能“忆昨西风秋力健,看人鹏翮快云程”。这五十六年的人情世态炎凉,是不寻常的。 56年的经营缔造,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特点吗?书名为何题曰《石头记会真》?此名有何意旨在内? 第一,这是个80回本,应服膺原作者最后定名《石头记》,以示有别于120回假“全本”《红楼梦》。 第二,“会真”是以真为终极目标,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斥伪返本,扫荡烟埃”;而“会”者,是会集已然发现的十多部旧抄本而进行大汇校,并在大汇校的基础上试行“写定”一部较近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头记》;而“会”又含有体会、领会、赏会的复合意义。 “会”与“汇”的有同有异,就在于“汇”只表明是一个聚集;而“会”则在汇校异文、如何抉择取舍上更需要体会、领会、赏会,这种文化造诣作为一种无形的“尺度”。所以,这种大汇校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异文大罗列”的技术性工程。 这个尺度,不是玄虚的吗?其实古人早就说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每有会心,辄然忘食”。没有这种会心,亦即谈不上欣而且赏。这个尺度,可以是因人的水平而各有高低长短,却不能说它是玄是虚,那儿有“标准”在。 第三,“会真”的真,包括存真去伪,不必多说;还有一个“去疑”。这是说,在种种异文中,发现或有或无的字句,而那字句的风格笔致不类雪芹的,就成为“去疑”的触目点———我们将它用特定符号标出,以示可疑,恐怕有出于他人后笔增入的可能。 这也是鲁迅先生早已指出的:旧时小说的文字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即小说“闲书”不受尊重,读者主观认为“不好”之处,他提笔就在书上乱改。佳例就在面前:《甲戌本》上,有个孙桐生的浓墨乱改字,看了令人“中心作恶”。《庚辰本》也有很多无名氏的胡乱塗改,半通不通———这种自作聪明的妄人,至今也并不缺少。如不严辨,就糟蹋了雪芹,犯下了文化罪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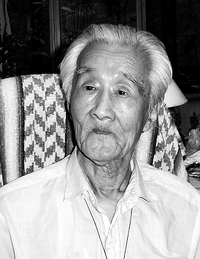 作者周汝昌近影 作者周汝昌近影第四,我们在十分复杂的异文情况下而抉择取舍,如何掌握一个“原则”,不是“死规矩”所能尽其能事的,比方说,常见的作法是“从众”,即以多数版本一致的则依,而舍其个别、少数。又如有一个“择善而从”。这听起来再好不过了,可实际上怎么才算“善”?就人各异见了。“字从字顺”,人们习以为“善”,奇一点儿,僻一些儿,即认为“不善”———于是校订的结果是将雪芹原笔的特色奇文,一一弄成了“千篇一律”的俗字俗句,不许这位大文豪有任何自己的“这一个”。我们引此以为戒,力避“一般化”的倾向与可能。 当然这就会出现一个认为我们“好奇”的嫌疑,发生一个“接受美学”的问题。把字定得冷僻奇异一些,“习惯”吗?能“接受”吗?这势必引发争议乃至批判。 举例而言:第五回凤姐的“曲文”不是“意悬悬”,是“意憗憗”。憗憗即齗齗,有执着、坚持、锲而不舍之义,与“悬悬”(担心,提心吊胆……)大异其趣。 又如,探春是“千里东风一舰遥”,不是“……一梦遥”。 又如,宝玉隔花窥见龄官画蔷,时当暑热,是“扇云可以致雨”不是“片云……”。扇是动词,在此念shān,阴平,若作“片云”,即是常言俗语,大大“一般化”起来,把雪芹的造字铸词的本色,全然“消灭”了! 此类甚多,不便尽列。 第五,我们的校订,还有“离开”了常规的特例,这主要是由书法知识而能以判断抄手之讹,疑不认识雪芹手稿的行草书体,一经点破,十分明了,也饶有趣味。这也属于能否接受的范围,因为从校勘常规来说那就“没有版本依据”而不敢相信了。 这种例,显得太大胆,逞臆断,不谨严……。但既能判断又何必犹沿旧错。这样作法是功是罪,留与公论讨究,如不足为训,存此一说,似乎亦无不可。(因行草书体在此无法排印,只得从略实例)。 这么说,我们的定字就一定都对了吗?谁也没有这么自封自证;只能是希望学习愚者的千虑,或有一得;而不敢自夸是“智者”———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若只有“一”失,又何其幸也。我们的意愿是可取的,但实际作到什么地步那是又一回事了。但愿区区微悃能够得到读者研者的理解与原谅。 这部书是连正文带脂批一起校订的全本,因为这“全”是指当日作者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已规定脂批是书文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有异于后人的批点只是附加物,而可有可无了。 为创此书,不止“三易”其稿,也经历了“三抄”其家——— 说来话长,今只简叙。三易其稿,是说这样的大汇校,异文繁複惊人,怎么表现在既展示全面情况而又显示出抉择取舍的理路,可以令人比较方便清晰地一目了然,并且留有思忖讨究的余地?这个“体例”以往无有先例可循,如果只是枯燥死板地罗列出千万条“某本作某字”式的校记,这非但不能“卒读”亦且不能成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我们作了各种试验,都不理想。最后才创成了本书现状的这种表现法,中间所费心思、精力、时间,难以尽言。实际是稿不止“三”易,至少有“五”了。 又怎么叫“三抄其家?”为了节省篇幅,我今只叙三次抄家的主题目与总因由:亡兄祜昌在每日力作苦耘之时,有一邻居“告密”,说他与胡适有“海外关系”,闭门在写“反书”!于是有一伙人就借题兴事,在我的所生地当作一件特大政治案件行动起来,几个部门联合行动,声势惊人,三抄之后,书籍手稿,一切资料片纸无存。最后是“扫地出门”,八口之家,因此没了立锥之地。…… 现在印成的十卷本《石头记会真》,是在变故之后,落实政策允许著作之下,重新开始,是“白手创业”式,坚持不懈,百折不回而终于完成的。 经历已成历史,原不必说起;所以在此一提,是为了说明我们的物质条件、工作环境的艰难简陋,这会大大影响这部书的质量,就不言而喻。例如,祜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并无工作桌椅,是趴在一个小凳子上作这种繁重至极的大汇校的!其他可不必絮絮而陈了。 
胡适致周汝昌信 我们兄弟二人一直力作到古稀耄耋之年,我目早坏,只能“读听”合作定稿。这种艰苦,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凭着一点虔诚,加上女儿伦玲的协作,由我将80卷大书逐字定稿,并为交待学术见解、定字理由,以“按语”的形式一一写明。———这不算“告成”,还有出版的大节目,多年碰壁,无人肯顾。最后得到二三位仁人君子之助,破格破例,玉成了此事。出版社为此一部书所费的心力,是可惊可佩的;仅仅社方设法特邀得力编辑与审校,就又花去了5年的光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