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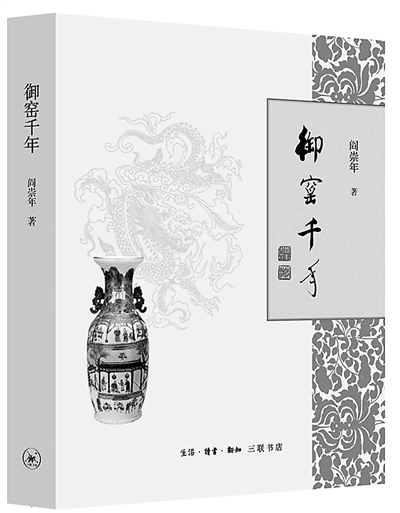

阎崇年先生以清史研究闻名,并通过“百家讲坛”赢得了大量读者。最近,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名为《御窑千年》,是一部简明的瓷器文化史,这不免让人有些诧异,难道他的研究发生了转向?
“历史主要有三个面向,第一是人,第二是文,第三是物。这么多年我主要摸索的是前两个,也就是通过文献档案,来研究袁崇焕、努尔哈赤、康熙等历史人物,我觉得自己有个很大的缺憾,就是通过物来反映历史,这方面做得不够。”阎崇年先生告诉青阅读记者,他想“挑战自己”,从物入手,来探讨物和人的关系,中国和外国、东方和西方的关系。而最适合的“物”,无疑就是中国的瓷器。“在历史上,我们通过瓷器和世界对话。在英文里,中国和瓷器是同一个词,这是瓷器非常特殊的地方,要想理解大写的‘China’,就不能不懂小写的‘china’。”
阎崇年先生说自己过去对瓷器“了解得太少”。其实,早在1992年,在海峡两岸开放后,作为第一批前往台湾访问的学者,他曾进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山洞库房,看到了许多珍贵的瓷器。“库房里恒温恒湿,箱子包着铁皮,每件瓷器都用丝绸层层包裹,用丝绵衬着,还是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时的样子。”这次难得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前些年,在“百家讲坛”讲完《大故宫》之后,有观众建议他讲讲瓷器。从此他开始“备课”,一边大量阅读相关图书,一边借去外地考察的机会,四处看窑址。“江西景德镇、福建德化、浙江龙泉,还有广西、广东、河北的窑口等等,‘南海一号’沉船的水下博物馆也去参观了,有的窑口只是遗址了,而像福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现在还在烧瓷。”
《御窑千年》集中谈的是皇家制瓷,对此阎崇年先生也有自己的考量。“为什么选御窑呢?瓷器的历史太复杂,各地的民窑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官窑和民窑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制瓷的官样从皇宫出来,是由当时最好的艺术家、书法家绘制的,民间没有这个条件。乾隆时期一年投入三万两白银,民间没有这个财力。一些制瓷的原料,比如清代的珐琅彩,一度由皇家控制,从进口到自行研发,特别昂贵,民窑也用不起。御窑瓷器,是精华里的精华,最能代表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工匠们的智慧。”
阎崇年先生曾多次前往景德镇,逐渐了解到制瓷的七十二道工序。从采瓷石、采高岭土开始,他目睹了今天的工匠们怎样把瓷土粉碎、淘洗、制成陶泥,怎样做瓷胎、绘画,以及满窑、烧窑、开窑等一道道工序。他经历过几次点火的过程,整夜守候,看工匠们如何凭经验而不是靠仪器来观察窑内的温度。他也见证了开窑之后,工匠们把瓷器抱出之时满脸的喜悦……“瓷器是工匠用血汗凝聚出来的。我亲眼看到,那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非常让人钦佩。”
亲身经历的这一切,也让阎崇年先生把目光投向古代的制瓷工匠,他努力挖掘有限的史料,在《御窑千年》里向历史上的名工雅匠们致敬,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的督陶官兼制瓷高手唐英甚至专列一章。“御窑千年史,唐英第一人。”阎崇年先生感叹道,“他在今天相当于一个厅局级官员,下到地方,却能和工匠们一起劳作,从外行变成内行。而且他非常清廉,他有一句诗叫‘真清真白阶前雪,奇富奇贫架上书’,品德非常高尚。这都值得我们今天的公务员学习。”
瓷器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在亚洲、非洲、欧洲都留下了鲜明的身影,并直接影响到西方历史上的“中国热”。阎崇年先生表示,古代的“瓷器之路”和现在的“一带一路”基本重合,贸易的历史也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他说:“中国创烧的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仅是一条锦绣斑斓的彩带,而且是一座跨越四洲三洋的津梁。”同样,瓷器之路、工匠精神,《御窑千年》似乎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