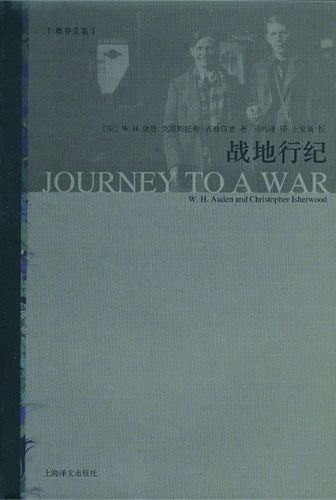 《战地行纪》,[英]奥登、[英]衣修伍德著,马鸣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42.00元 在跟随衣修伍德的旅行日记,走进他们从香港进入中国到从上海离开中国的这段时光,被衣修伍德在这本《战地行纪》中提到的伊文思和卡帕同一时期拍摄的影片和照片,时不时出现在脑海里,让人想起著名战地记者卡帕的那句名言:“要是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不管多少人曾质疑衣修伍德和奥登是否真正直面了战火硝烟,在本书中,他们由始至终也如卡帕一样努力地持续不断地接近他们想要看到的真相,即便面对物质上的重重困难,即便面对种种文化障碍,他们依然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更为精彩的是,在《战地行纪》中,他们实实在在地在汉口亲历并记载了抗日战争中最大规模的空战“四二九空战”。同时细心计算一下他们离开上海归国的日子,正好是“武汉会战”全面开始——安庆失守的日子。因而也可以说,他们在“武汉会战”的前夕,为这场战役做了一次预检。而非仅仅是在上海与四个日本人做了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 在中国如此短短的日子,他们乘火车乘轮船乘汽车甚至竹轿,走过了空袭中的广州,两次进入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汉口。在郑州和西安,衣修伍德写下如斯句子——“若郑州意味着种种疾病,西安则意味着谋杀”,甚至差点“乐不思归”滞留九江,在南昌寻新四军不遇,在金华给三百个学生演讲,与特派记者彼得·弗莱明经历梅溪的失守,从温州乘外籍船到上海……匆匆在路上浮光掠影般的日子,注定他们无法深刻认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仅仅只能一窥当年“武汉会战”前夕的中国陇海线一路的碎影,但另一方面清晰明澈地留在文字里的,却是他们作为“旁观者”的“深刻”或者“犀利”,无一例外地呈现着他们的开放的思想。 随着阅读《战地行纪》的深入,在他们行走在“武汉会战”前夕中国战火纷飞的焦土中,闪过脑海的,不仅仅是衣修伍德和奥登正在经历的时空变换,更是他们所遇见的政界、军界、文化界的那些人物,“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传教士”,特别是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杜月笙,邵洵美、凌叔华,甚至中国生理学之父林可胜等等,一点一滴地在他们的文字里呈现出另一面。 同期阅读此书的好友与我交流的时候说:“这里面有个陌生的中国。”她甚至曾怀疑,在奥登与衣修伍德遇见的那些人物,那些事情,真的是否存在?他们所遇见的,很多很多的,我们从来不曾看见的——那些英文很流利的中国人真的是我的同胞?那个在九江的堪比今日星级的修道士风格的酒店“旅途终点”是不是真的存在?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人物是否真的有他们看见的另外一面?比如:对于那个影响中美交流很深的史沫特莱女士,在他们的眼中是“像极了俾斯麦”,“红军是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整个生命——是她的丈夫和孩子”。更为微妙的是形容蒋介石“看上去就像是个乡村医生”,而“蒋夫人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知道如何应付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类型的访问者”,“基督徒将军”冯玉祥是“那种如鲸鱼般庞大而仁慈的人物,无言而自威”,博古则是一味“哈哈大笑”的,杜月笙是领导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个中国式的斯芬克斯”,等等。至于路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精明而懒惰的老蒋,荣誉感强烈身体羸弱的杨少校,因拍照而索钱的乞丐,强壮的苦力,甚至衣修伍德细致描写的那个拾取他们丢下硬币的小孩等等,这些描写都让中国读者感到陌生和惊异。 扪心自问,那些被衣修伍德和奥登从头至尾深恶痛绝地随地乱吐痰的人,绝对是我们的同胞,他们在“呼啸山庄”清理的那些被褥和窗子,依然在我们身边。看到这些的时候,我想起来去年一直在重看的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深深的一抹人道思想的悲哀,抹不去地留在字里行间,即便衣修伍德描写这些事例时笔下英式的幽默时常能让我莞尔一笑。 而奥登,对于中国人他留下了这样美妙的句子:“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是不是这位著名的诗人用了这样琢磨不透的形容方式表达了只能意会的他心中的中国?还是他那种欧洲人的眼光无法认识中国?奥登说“我们感觉中国人只是在说着他们欲令自己相信的东西”,他们看得多么清晰——因为在那个时代,我们曾经这样回答:“不,没有被打败。”“这是战略撤退。”衣修伍德早就断言:“在这个城市,强权政治的视觉生命比任何言辞都更为无情。”这就是“武汉会战”前的中国。真实么?虚假么?答案在读者心里。 有趣的是,奥登曾言自己对中国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同时,他还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至于最后这一句,是属于旁观者清,还是属于“一个旅行者的认知”,就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