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鸭蛋湖传说》 周静 不久前,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周静的新作《簪花的雷神》,这是“鸭蛋湖系列”第二辑第一册。第一辑中,周静构建了神明的日常生活,其中有湖神泽泽、原野的主人鸭蛋公,还有三寸婆婆麻老太。《簪花的雷神》则是在成为雷公、电母之前,两人相遇的故事。 唯一略显特殊的是《鸭蛋湖传说》,以人的视角展开。作者以笃定的态度书写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鱼在雾里游;龙突然出现,变成一座桥;鸡蛋能磕出宝石……在这里,一切神奇的事件都有可能发生。 童年藏着一个人所有的秘密。在采访中,周静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她生活在神奇之中,乡土、老人交织在一起,屋旁一条大河奔涌。当她长大,神奇就在笔下流淌。 这是一个有关神奇的故事,也是一位儿童作家的成长故事,还是一个家庭里四代人的故事。 以下是她的自述。 和时间一起成长 小时候,我家开杂货店。当时开杂货店的人家少,我妈总是很忙。我爸是老师,后来当了村小校长,也很忙。忙不过来的时候,会接外婆来,或者送我去外婆家。有外婆照管生活,我就不愁了。外婆家在邻村,和我家隔五六里路。我有很多童年记忆和外婆相关。 外婆会把生活安排得很妥当。那时没有太多零食,夏天天气热,晚上多煮一把米,剩下的米饭第二天晒干,做炒米,或者做“甜酒”。“酒药”像汤圆一样,把它弄散,然后撒到米饭里和匀,放进钵子里。钵子盖好,用棉布包起来放灶头。灶头有余温,早上起来“甜酒”就可以吃了。我们那边叫“甜酒”,实际上不是酒,就是酒酿,很甜。 在生活中,外婆有很多这样的小主意。要是实在没什么可吃,她就放一把绿豆到陶罐,把罐子放灶头煨着。等我睡了午觉起来,放一点糖,就有绿豆沙喝。外婆还会去菜园里摘个黄瓜,摘个香瓜,总会让你嘴里有味道。出门前,外婆会换一身平平整整的衣服,从灶里捡一块冷掉的木炭,对着窗边挂着的小圆镜子,描描眉。 外公特别得意一件事——他和外婆结婚的时候,用了花轿。外公总说他,“三岁做短工,六岁做长工”。从小日子很穷,他就这样长大。结婚时,能用一顶花轿把外婆娶回来,他很自豪。外公很温和,他说,我一辈子没和你外婆红过脸。外公很能干,会种很多东西。到了60岁,他心脏不太好,要种橘子园。别人就讲,可能你种的,自己都吃不到。他说,没关系,前人种树,后人吃果。然后,他就开始种树。 在我小时候,作物很贫瘠,地里就那几样。但外公会去种西红柿,种香瓜。这种果子很难种,没有种子,也没有果苗。听说哪里有苗,他就骑单车,骑很远,带米酒作为礼品交换。或者是糯米、豆子、芝麻,在农村这些都可以交换。换来几个苗,先把它们种在一个小钵钵里,看它们长大一点,再移到地里去。 农村的日常是很乏味的。但这些细节就像生活里的糖果,滋润了我的整个童年。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的故事?我想,在外公和外婆身上,我看到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人可以积极地去面对,可以去创造一种生活。我也希望作品里有一种来自自然的甜味,它是甘甜的,是有余味的,甜过之后不是酸的,不知道有没有做到。 你问我之前,我没有回溯过他们的生活。现在想起来,他们挺艰难的,把4个孩子养大,每日劳作,除了照管稻田,外面有菜地的活,家里有灶间的活,但他们会把生活安排好。外公、外婆就是普通人,没有更多的钱去购物,所以就自己种,自己做。在种的过程中,你会有期待。 这一次去,他会告诉你,西红柿挂果了,小柿子青青的。过几天再来,柿子熟了,就可以吃了。要是过几天没去,外公就骑着单车,用个小篮子把柿子一装,停在我家门口。现在长大想起来,那就是一筐西红柿,但对当时的我来讲,意味着每天都有新期待。有时是你主动发现,有时是惊喜突然找上门来,日子好有盼头。 现在很多人很缺乏这种能力,因为不善等待。小时候,人是和时间一起成长的。稻子种下去,禾苗长上来,再长一长有穗子了,大人会说“扬花了”。我们有两个假期,上半年春插,放假回去插秧;下半年有秋收假,这一个星期回去干农活。你会等待和劳作,也会有收获,一切都在眼前展现出来。我们是人与自然养育的孩子,人和作物的生长深刻地嵌入时间的痕迹里。 规则像空气一样 在农村,有很多说不清的规则,大家都是这样做,没人问为什么。比如,做“酒药”的过程很讲究,蓼花必须在向阳的山坡上摘,附近不能有臭水沟。做“酒药”这天要看日头,必须是一连几个晴天。药团得晾干,做一次用一年,如果没干透,“酒药”就存不住,容易长霉。 再比如,端午的雄黄酒要正午12点做,把雄黄酒和肥肉泡在一起。时间卡得很准,必须是12点。古人可能觉得,那一天、那一刻,天地之间的阳气达到顶点,做出来的雄黄酒驱虫、排毒的效果更好。 我家在湖南,屋边就是江,当地人喜欢吃鱼,经常用酸菜煮鱼。平时,酸菜都是随吃随做,不会做太多。把青菜、白菜,或者包菜,过水烫煮一遍,再泡着。但立冬这一天,家家都多做。只有用这一天井水腌的菜,才叫“冬水菜”。 菜是一样的,工艺是一样的,井还是那口井,但人们认为这天水不一样了,所以“冬水菜”更脆,更好吃。直到现在,我妈还会说,“这个是冬水菜”——以和其他酸菜相区分。家里买了冰箱,她会把“冬水菜”拧干、冻上,给孩子们分下去。如果她不说,我是吃不出来的(笑)。但我妈特别认,她可能觉得那一天空气、阳光都不一样。这也很玄妙,说不太清。 在村里,家家都信灶王爷,不光过年祭祀,平时也敬畏。棉鞋打湿了,绝不能放灶上烤。灶眼里有热水,舀水时,洗脸盆可以放灶台上,洗脚盆就不行。这不是一个空悬的规则,里面也有合理的成分。灶台上总放吃的,鞋子、洗脚盆上细菌多,一旦污染了食物,人就容易生病。从古至今,很多巫术都讲禁忌,它可能就是人对生活的总结。 打我记事起,我爸就爱看报,他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也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我们那边平时爱吃腌菜、腌肉,农村都是体力活,认为吃盐长力气。我爸跟谁都说,别吃那么咸,吃多了不好。别人看他,都觉得他很怪。 过年,我妈做了腊鱼、腊鸡、腊猪头,腊肉一蒸油花花的香极了,大家都爱吃。家里来了客人,我爸也会说,少吃点(腌肉)。我妈就容易急,让他别说。客人还劝我妈,“没事没事,周老师说得也对”,一边说,一边夹起大块腊肉,以示自己不在意。 去相熟的人家,我爸也会念叨两句,少吃腊肉。大家都笑,说这报纸说的是“外面人”的事,我们吃的是“老班子”的饭——老一辈留下的老规矩、老习俗。包括在卫生上,村里人都觉得我爸讲究得有点过头。 我爸脾气温和,爱说笑,别人有事找他,他总愿意出主意帮忙,多数也能帮上。我们上学那会儿,学费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当老师工资也不多,挣的钱经常给学生们垫学费。加上村里尊师重教的传统,村里人对我爸那些“怪”也就不在意了,还很喜欢和他聊天。 我妈以前做豆酱,黄豆煮熟以后,让它长霉。家家都这么吃,她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能吃的。我爸说不行,长霉的东西不能吃。现在我们知道了,它是一种菌丝,但那时候我爸不知道,报纸上也没说(笑)。 一到过年,我爸给全村人写对联,从不给自家写,他不信这个。每年我妈都多报一幅,偷偷夹在中间,让我爸写了贴上。这两年他好些了,虽然还是不信,但看着喜庆,也就不管了。 从小到大,我爸给我的印象是,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未必对。生活中,家里总会有点类似的小冲突,所以当我看到一些现象时,不会完全接纳,也不会完全质疑。 故事长在大地上 我家住湘江边,小时候不知道那是湘江,村的人管它叫“河”。打雷了、下雨了,大人会说,这是龙王相亲。 如果雨特别大,他们甚至会争论是哪方的龙王,根据风的方向、云的颜色、雨水的气味判断,各有各的道理。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底下一帮孩子听得津津有味。 你之所以觉得这个场面有点吊诡,因为你没生活在这里。 河的另一侧是洞庭湖,洞庭湖里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一回坐船,我记得是一艘小木船,船上有棚遮着,慢慢往前走,船桨拍打水面,岸越来越远,比感觉中要远。漂在水上,人有一种不安全感,水那么深,那么神秘,水下什么都有可能存在。坐船的时候,人又特别爱讲故事。姐姐讲“金斧头 银斧头”的故事,我感觉一伸手,就能从水里捞出斧头。 在那个环境里,所有神话故事都是真的,你愿意相信它是真的,深信不疑。我在船上听了《柳毅传书》的故事。书生落榜,要回老家,路上见到牧羊女在岸边哭泣,于是上前问询。女子是洞庭湖龙王的小女儿,嫁给了泾川龙王的二儿子,婚后被赶出家门。 柳毅答应帮她送信,他又担心,自己是凡人,怎么到龙宫呢?女子就告诉他,带着书信到洞庭边,有一棵大柳树,敲三下,就有人取信。果然,敲了三下,虾兵蟹将出现,柳毅被蒙上眼,进了龙宫。龙王看了信,把女儿救回来,还把她许配给了柳毅。 小时候,我们那的河边都是柳树。我敲过好多柳树,一般都是敲两下,第三下不敢敲,好紧张,万一虾兵蟹将真的出来怎么办?又期待,又害怕,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民间故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地域性,故事发生在这片土地上,人会对故事产生信任感。我为什么会写鱼在雾里游,因为小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雾很大,天又黑,看不清远处,这个时候有很多声音出现,也许是远处的桨拨动水面。听到水声,我就想是不是有鱼游出来了。 坐在船上,岸在远去,代表着日常的生活远去。或者说,当你需要想象神奇的时候,要适当地迈开一点,走远一点。这就像一个镜像,人通过神话故事看待生活。人对神明好奇,神也会对人好奇。我以前写过一个故事,叫《雨娘子》,讲的是雨娘子进入山村的普通人家,看山里人过冬的悠远日常。 你想,神的世界里没有时间。他拥有无穷无尽的时间,也就没有时间概念。时间没有起点,也就没终点,很多事就没意义。所以神会比较无聊,总想做点什么,当他进入人的生活,故事就来了。 《泽泽的湖》里,泽泽是湖神,她坐在门前吃糖渍桃子,觉得湖面上阳光刺眼,说“来场雨吧”,湖面上就下了一阵大雨。她爱吃麦芽糖,会去赶集,也有人的渴望。神的存在,也许是为了反射人的渴望吧。 我没法回答《鸭蛋湖传说》是怎么来的。其中一篇是《白雁塔》,灰麻的大雁从塘里钻过,变成了大白雁。只有重新被露水淋过,大雁才会恢复毛色。 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我也说不清。“白雁塔”这个地名就在地图上,我看到这个地名,故事就自然地写出来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生活在神奇当中。 人会自己找到答案 家门口就是湘江,我从小喜欢看这条河。黄昏,搬个小凳子,坐在大地上看河。夏天,到了晚上,看月亮。 大堤把河水拦住,围出圩垸(滨湖地区为了防止湖水侵入而筑的堤),垸子中间是大片洼地,种稻子。我家的小屋在大堤和田野间,窗外就是田野。我也喜欢看田野。没书看的时候,就看这些。 我还记得,夏天午睡起来,人迷迷糊糊的,不知道干什么好,坐在后门口,就觉得很安慰,也说不清看了什么,坐那就很舒服。 上初中,我想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为了什么?每天骑单车经过田野,上学看日出,放学看日落,后来也没找到答案。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那么执着了。 在人生中间,我们会碰到各种问题,这是家长无法解决的,只能自己去找答案,自己去化解。自然、田野、乡村能够包容苦闷,她会把美展现给你。但城市里没有,当眼睛看不到美,人会枯燥。 在女儿小时候,我是有焦虑的,她在城市里生活,好像被连根拔起一样。一到周末,你会发现,小孩们个个多才多艺,从家里被送到兴趣班,学二胡、笛子、舞蹈、钢琴……从一个房子走到另一个房子,家是一个房子,学校是一个房子,兴趣班也是一个房子。小孩觉得理所当然,也很开心。 人没拥有过,不会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我有过,我经历过,我知道少了什么。到了假期,我会尽量带她回老家去,上学后少一些。 到老家,她也很开心,玩得开心。一旦累了,她就要回来,觉得老家住得不舒服。她处在一种可选择的境遇,她会选择两者愉快的一面。 大人热衷于把孩子的生活填满,你怎么能无聊呢?孩子的选择面也很广,可以看书、玩游戏、看短视频、画画、打羽毛球,这些都可以做。孩子也无法忍受闲着,自己都要找点事干。 女儿读小学五年级,直到这学期我才报了一个羽毛球的班。班主任都很惊讶,问我为什么不报班,周末怎么能空着,学唱歌、学跳舞都可以,小女孩有那么多可上的兴趣班。 空闲的时间很重要。它让人在生活的惯性中停下来,去观察和发现生活。这和阅读、写作是一样的。“闲着”本身就很愉快。 我给女儿时间,不去干涉,她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她主要做两件,画画、看书,或者一个人躺在沙发上,就是躺着,很舒服地躺着,放空。 这时,她喜欢问问题,比如,为什么要上学?我说,上学不是一件天生的事,这是国家发展了,才能保障每个孩子有上学,上学的机会很宝贵。我给她答案,她不接受,理解不了,我们在两个频道里。我说,那好你自己来回答。她后来找到了,上学可以认字,认字以后可以读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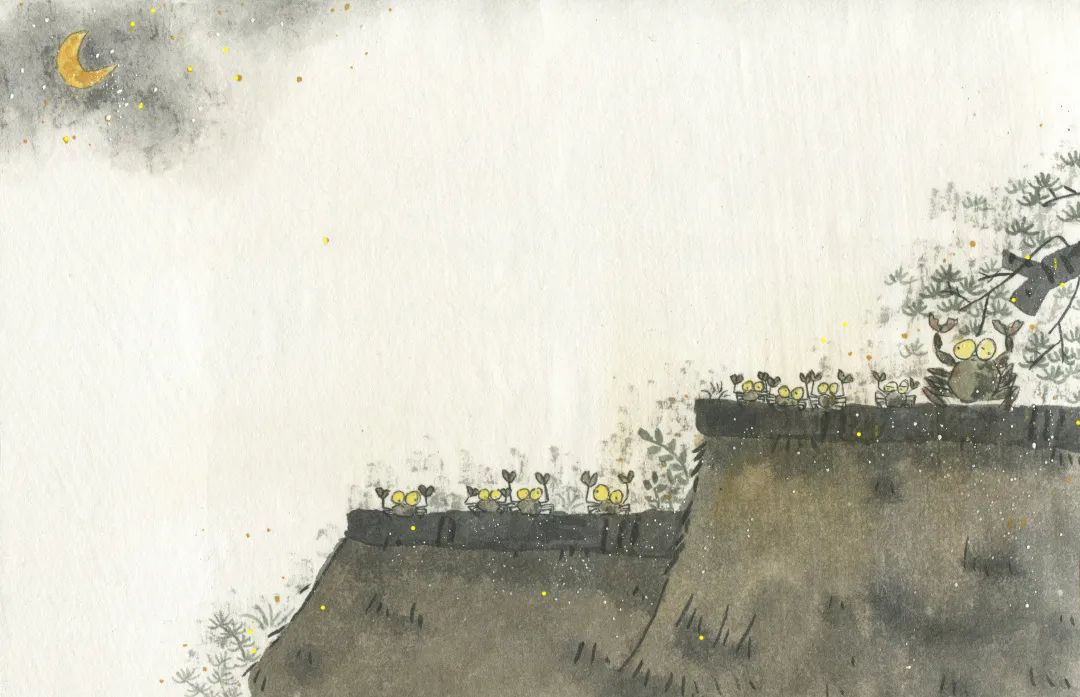 《草帽洲》插图(《鸭蛋湖传说》) 对话 周静& 好书探 01 大地是辽阔的,故事也是辽阔的 Q:编辑工作会影响您的创作吗? 周静:我在《小学生导刊》做编辑,这是一份综合性期刊,发行量蛮大,光湖南省发行量超过100万份。其中有一块是儿童报道。我们会进学校采访孩子,了解他们的生活。 学生知道希腊神话、罗马神话,欧洲民间故事,但说不出太多我们自己的民间故事,说来说去就是《牛郎织女》《夸父逐日》《女娲补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不了解。文化里有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不同。 从古至今,我们的民族都有讲述神奇的传统,比如《聊斋志异》《山海经》。我写过一本书,叫《月光照耀大地》,里面每一个故事都有来历。其中一篇是《月光的盐》。在陆山有一块黑石头,月光照下来,石头上会出现盐。圆月,盐是甜的;弯月,盐是苦的;没有月光,就没盐。还有一篇叫《看门草》,草放在门口可以看门。在我们的古书里,有很多这样的神奇,但在现在的讲述里,神奇消失了。最近我在看贾平凹先生的《秦岭记》,书里讲的都是这样神奇的故事。 为什么乡土中会有这么多神奇?或许是因为生活的枯燥,人会渴望神奇。我翻过县志,里面有一首诗,原诗记不得了。写了一位老农种稻子,头一年是旱灾,第二年是涝灾,第三年又是旱灾,第四年终于收获了。他端着那一碗饭开始痛哭。我看到这,眼泪也哗地下来了。生活的艰难让人更向往神奇,神奇能够安慰到他。 我们的传统里有神奇,它让人觉得温暖、美好,甚至是恐吓。不管是什么样的神奇,它最终把人推向敬畏,对自然的敬畏,对身处之地的敬畏。人有了敬畏,就不会乱来。 Q:当下的孩子仍然需要中国气质的神话。 周静:和我这一代人的童年相比,现在的孩子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迁徙,二是生活更为精细。密布的公路与铁路,让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迁徙。 有一回参加活动,其中一位年轻讲者的发言主题是“另一座城”。她在另一座城上高中,一直在两座城之间奔波,总觉得下一座城才是生活的地方。 还有一次去学校,有个女孩问我,怎么才能写好《我的家乡》?她不知道哪是家乡,父亲说是江西,她在杭州出生,在北京上幼儿园,到长沙上小学,以后可能还会搬家。听她的描述,我当时就呆住了。 我们刊物有习作版面,常常会收到小朋友的作文。一个孩子在作文里写,户口在北京,出生在上海,现在在天津上学,中间还在武汉和杭州生活过。“老师要我们写《我的家乡》,我先是发愁,该写哪里呢?后来一想,哪里都能写啊。它们都是我的家乡!”他说得好。 故乡从哪儿来?从生活中来,从故事里来。故乡与故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体的。有社会学学者发现,人和人的区别往往在于他们相信不同的故事。传说和神话就是同一文化背景下的故事。大地是辽阔的,故事也是辽阔的。中国很大,但再大也是一个中国,在这片大地上,不同的故事,同气连枝,有着相同的东西在其中流淌。不同的故事,组成一个大故乡。我们倾听和阅读故事——读那些世代流传古老的故事,也读发生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新故事——了解我们生活的大地,借此在心中构筑家园。 Q:可以谈谈您最初的文学创作吗? 周静:有次看书,我看到一句话:“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天女魃的命运一下子触动了我。她是黄帝战蚩尤的大功臣,结局却是不得重返天庭,居住在没有雨水的地方。我查了魃的故事。魃在传说里又叫旱魃,是人们驱赶的对象。一个在神话中拯救人类命运的大功臣,最终得到的是被驱赶的结局。这让我困惑,也让我愤怒。魃的命运在我心里纠缠。质疑、曲解、背叛,这不是现代人常常面对的困境吗?我以对于魃的命运的思考创作了《天女》这本书,并由此开始了神话题材的童话创作。 神话不仅仅停留在过去,还拥有丰富的现代性。神话展示的是人在早期社会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开拓家园,呈现出坦然和勇气。儿童需要神话的荒蛮之力,让他们有力量去打破、去创造。 生活塑造人的写作环境,提供思考和写作的素材。反过来,通过写作和阅读,也可以再塑造生活。也就是说,传统可以通过阅读来延续、创造和发展。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塑造孩子们关于民间、关于传统、关于神话的这部分的认知和生活。这是我的野心,也是我的愿景。 Q:写书时,您调动了哪些童年经历? 周静:写“鸭蛋湖”时,我想起的不仅是某一个场景、某一个画面,而是一种萦绕在童年里的气息。在田间赶路,很少能遇着人。田野寂静,总有各种莫名的声响,就会害怕。迎头见着村头的小庙,心头一喜。在小庙前坐下来,歇口气,念叨几句,喝口水,身心都舒坦了。有小庙说明什么?说明这里的人,心里有神明。心里有了神明,就不会有什么大坏事。 一进入腊月,整个乡村都沉浸在一种喜气里。扫尘、杀猪、打糍粑、做甜酒酿、缝新衣、干塘(抽干池塘里的水,捞鱼)、熏腊鱼腊肉,推出单车骑上五里地、十里地,到酒坊去打酒。平日打上二两半斤,是不去酒坊的。到了除夕贴春联,不止门上,各处都要贴:堂屋的墙上必贴“童言无忌”,水缸、米缸、猪栏、牛栏都要贴,贴的内容记不得了。 这是一种弥漫在日常的气息,各安其位的气息。人人在年节说着“金银满屋、马上封侯”的吉祥话儿,过日子却是柴米油盐小心宁静。种地时,好好种下种子;收获时,捡拾起见到的每一粒谷子。节气到了,牙缝里省下的一升糯米蒸熟了,做成甜酒酿,或是打成糍粑。打好的糍粑摞起来,顶上盖一小片红纸,用麻绳系好,拎在手里朴素又好看。我喜欢有滋味的日子,写“鸭蛋湖”也想写出这样一种滋味。 Q:您在书里写到了许多规矩,比如“头鲜”(第一茬收获的作物)用来祭祀,新架了桥要放鞭炮,否则不能过……为什么要把“规矩”揉进故事里? 周静:一方面是“规矩”原本就和“滋味”融合在一起,写“滋味”就离不开“规矩”;另一方面,因为“规矩”建立起一种连接。网眼有大小的规定,要捞大鱼放小鱼,小鱼放走了,明年才有大鱼可捞。把鱼捞尽了,下一年捞什么呢?农民的生活不仅看眼下,还看未来,看过去。 除夕团圆宴,人们给家里的动物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猫的碗里要有鱼,狗的碗里要有肉,牛羊的槽里多加蔬菜。这是人和动物的连接,感谢它们一年的辛劳。 乡间的规矩伴随人的一生。 在外公家,纸的用途是不同的,有的纸用来引火、点灶台,有的纸用来祭祀,有的纸必须单独拿个盆“化”(烧)掉。我至今不清楚这些纸有什么区别。 我妈做过一阵儿衣服,她是跟老师傅学的,盘扣往左还是往右都有讲究。她也说不出原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在乡村,人们会把原理、道理放进规矩里,这是规矩,就这么做。 当然,规矩有时会是一种束缚,有些束缚需要破除。我喜欢描述的是日常那些融合了“滋味”的规矩。 02 我喜欢习俗, 因为习俗上有时间 Q:看完《泽泽的湖》,我感觉泽泽就像一个能在乡村独立生活的孩子。一个人过日子,又能把日子过得很好。 周静: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泽泽是一个孩子气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孩子气。她不是孩子,她是一个成年人,会对小细节感兴趣,会去凑热闹。有一位妈妈看过这本书后跟我说,这是她特别想过的生活,闲适的田园生活。成年人也有这种愿望,不是在压力下工作,生活里有小烦恼、小欢喜。 Q:为什么想以“雷公电母”为原型写故事? 周静:写这个稿子,是在春天。春天桃花儿开。小时候,乡间的屋子大多是土砖建的,墙壁刷着白石灰。日子久了,墙壁颜色会变暗,会有一道一道灰的、黑的、棕的各种痕迹。田野光秃秃的,常常下蒙蒙细雨,天空也是灰的。在这一片灰沉沉中,一声春雷响了,一枝桃花儿开了,一切似乎都亮了,人们都欣喜起来,春天来了。春天总是与桃花、春雷连在一块儿。 儿时,外婆说,雷神带喜。小孩怕打雷,但从不怕雷神。于是,在一个下雨的春日,我想到可以把桃花簪在雷神的发髻上。当我想把春天的欣喜写到文字间,一个有关雷公电母少年模样的故事就产生了。 Q:关于《鸭蛋湖传说》这本书,我有好多想问。比如,当我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拆解《芦溪架起盘龙桥》,发现动不了。无法理解作者要表达什么,就像一个谜团上摞了另一个谜团。“龙”是突然出现的,您也没有解释的意愿。 周静:在乡土传说里,很多神奇的事物都是突然出现的。就像桥猛然出现在那儿,它就是一个神奇,不是由人一点一点修建起来的。生活在这里的人发现了这个神奇。你觉得无法拆解,因为文学理论那一套工具是西方传过来的,遇到本土故事会失灵,里面的思维逻辑不一样。 这座桥是龙变的,为了表示敬畏,人会放鞭炮。同时,人也是讲实用的,既然是一座桥,那就是要走的,放完鞭炮以后,该过桥就过,该摘葱就摘葱,不要耽误生活。就像剪纸里的扫晴娘,当她贴在墙上,她就是神奇的,可以把乌云扫开。没贴到墙上,她就是一张纸片,有实用价值。两者不冲突,既是实用的,也是抽象的。 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确实没想过解释。这就是神奇,不用问龙为什么会出现,而是去感受神奇本身。你的解读很好,你帮我和你找到了答案。《盘龙桥》写的是人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神奇的反应,写了一种生活现象。 我没想到,你读的时候有这么多疑问。很多小孩读过这本书,他们不会提问题,孩子天然地相信神奇和美好,享受神奇发生之后的一切。跟小孩吵架很有意思,你跟她道理,她不听,她就问,你喜不喜欢我?一旦回答喜欢,她就像捋顺毛的猫一样,马上承认错误。孩子的感性要大于理性。 这一系列,我最喜欢《鸭蛋湖传说》。到底写了什么,我也答不上来。当我回头看,它就是在那一刻冒出来,出现在心里,然后我把它写出来。 我喜欢习俗,因为习俗上有时间。我买过一套饼模,木头上刻着鱼、兔子、福字,面团放进去一按,蒸出来的馒头上有图案。在一刻,生活是不一样的,这个图案不是为了果腹,它和过去相连,带着祝福和审美。就像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Q:《鸭蛋湖传说》里有一个赵三和螃蟹的故事。赵三打开门,发现给自己做饭的是一只螃蟹,后来有了几只小螃蟹。这让人想起《田螺姑娘》。它属于“故事新编”吗? 周静:不光是“螃蟹姑娘”,“鸭蛋湖系列”第二辑里还有一本即将付梓的《田螺姑娘》也用了民间故事。这算是故事新编吗,我也不知道。我把民间传说放进故事里,用故事和故事对照,写出新故事,这似乎和传统的“故事新编”有些不同。 “鸭蛋湖系列”以传说为题材进行童话创作,是我自己为民间传说的新变化做的一种尝试。我们总是从人的角度讲故事,认为神仙、精怪只有化为人形才能和人一起生活。在这个故事里,我想写的是人和动物是相通的,可以互相选择。人不止可以用人的状态生活,也可以变成一只螃蟹,生活在海里。 在很久远的过去,人和动物平等,人们甚至会崇拜兽,留下如此多的图腾。然而,在人类强大的过程中,平等消失了,随之消失的就是尊重。 Q:还有一篇《杨梅溪》,写到孙女睡着了,发现妈妈和奶奶悄悄出门。她好委屈,不知道大人去干什么,为什么不带自己,然后一路尾随,钻过芦苇丛,结果发现是去泡澡。为什么要把这段写得像谍战片一样? 周静:有个绘本叫《让我安静五分钟》,讲的是妈妈想要片刻宁静,不用带孩子,哪怕只有五分钟。即便带孩子一起去泡澡,妈妈也不是在休息,她的一双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孩子身上,不由自主地想去关照孩子。 我写的是一个属于女性的空间。溪水只有在端午那晚是温热的,平时都是凉的,没法泡澡。这是一个秘密基地,妈妈和奶奶在这里休息。 在农村,婆媳多数住在一起。她们是家庭里最重要的人,穿衣饮食作息,安排日常生活的一切。婆媳关系不好,家庭处于紧张状态。婆媳关系好了,家里才是柔顺的,柔和的,就像一块揉好的面。 Q:最后一篇《男孩的果树坡》有些不同。更像寓言故事,讲了一个男孩执意要在一块种不出庄稼的地上种果树,年复一年地堆肥。几年后的春天,荒地发出了巨大的,禾苗生长的声音。好像是在说,人要长期去做正确的事。是特地把这篇放最后吗? 周静:把这篇放在最后,是有考量的:前面写的是自然的神奇,最后一篇是人创造的神奇。男孩不是一个精明的小孩,他就是想种树,长不长得出来,跟想不想种是两件事。长不出来,可能是种子的事儿,土地的事儿,但种树是我的事儿,今年没长出来,明年继续种。 故事里是一个小男孩创造了神奇,但这不一定是个人行为。个体上存在概率问题,可能成,也可能不成。一旦放到整个人类的境遇上去看,那就是客观存在的,人类会创造神奇。 03 没有文化,没有故事, 节日变成一种辛劳 Q:刚上班的经历,可以讲讲吗? 周静:当时,《小学生导刊》成立20周年,有一个改版。我是上班后才接触儿童文学。主任说,做儿童刊物就要了解儿童语言,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作品。至少有一个月时间,全部用来看书。我就开始读,就像打开了一个宝库,太好看了。先有一段阅读过程,然后再进入工作,并不是一开始就编稿。那段刚上班的时间太美妙了。 Q:我也挺好奇,您为什么不给孩子报兴趣班?不焦虑吗? 周静:我很赞同人有热爱的事,从小就能找到,那是很幸福的。但现在兴趣班特别不好找。我家小孩喜欢画画,如果给她送到兴趣班,可能这个兴趣就没了。我见过一位美术老师,几年前开了一个美术班。她在黑板上画一双手套,让所有的孩子画手套。孩子的创作是什么?就是在手套上填花纹和颜色。如果把我的小孩送到这里,她可能上了一节课,就不愿意再画了。 我没有什么焦虑,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让她画。我对民间艺术感兴趣,家里也有很多书,看到好看的,就会给她看。她喜欢绘本,家里有很多绘本。我也会关注插画师,插画师身上有故事。去年,我买了一本《如何成为一名插画师》,也会和女儿一起看插画师的演讲。天然出了一本《生活蒙太奇》,她很喜欢,看了两遍。 大人可以拓宽孩子的眼界。我们不光看画画的视频,还看夯土建筑的视频,介绍了现代建筑的特点,展现了建筑的各种可能。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给我看《安徒生童话》,书封写着“[丹麦]安徒生”,我以为他就叫“丹麦安徒生”。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一个国家叫丹麦。 小时候,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作家这回事,从没想过书封上印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名字天然就在那。我也不知道有编辑这样的工作。头天上班,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好事,坐在这里看书,就给你钱,环境还这么好(笑)。 大人的视野只能看到这,孩子的未来,社会未来的发展,我们看不到,也想不到。所以我只能把自己看到的好东西介绍给女儿,有兴趣的话,她可以看一看。 Q:您怎样理解节日? 周静:节日是在故事里建立的。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对圣诞节那么熟悉?因为它是从作品里来的,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氛围、模样。如果节日里没有文化,没有故事,那节日就会变成一种辛劳,奔波嘈杂。情感不同,人会对节日产生不一样的印象。 以前过年,女儿觉得无聊。后来我们带她去“送恭喜”。老家有这个习俗,除夕这天小孩拎个袋,到每家串门,开门就说“恭喜发财”,主人就会拿糖,或者是别的零食。她高高兴兴地说“恭喜”,对方好高兴地回复,人和人之间有交流。 农村不像城市,处处都有灯。她从光明走到黑暗,再从黑暗走进下一户人家的灯光,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平时不给她吃糖果,这天她能搜罗到很多,还有酸酸乳、红薯片。她总会得到想要的,甚至是超出预期的,一整天都充满惊喜。这也像人生,送出去祝福,收获了友善。因为疫情,前年没回老家过年。她觉得这一年索然无味,“浪费了一个年”。 Q:您小时候喜欢上学吗? 周静:我回忆我的小学生活,为什么要去上学,因为上学可以玩。上学才能把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小时候玩“攻城游戏”,今天这一局败了,明天要扳回来,心心念念上学,盼着下课。 学习里有娱乐性,人和人之间有游戏。学校一方面教授知识,另一方面把孩子聚拢起来,大家学会相处,形成一个群体。学校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在于,把孩子丢到一个可控的群体里,有教师引导,大家在一起玩,在群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过于甚至只强调成绩,各种问题就出来了,学习也变枯燥了。 Q:为什么老人给孩子讲故事如此重要?现在小区里,还有老人给孩子讲故事吗? 周静:像我这一代人,还能听到老人讲故事,但到了我小孩这一代,乡土在失去声音,在慢慢消失。如果不把它记录下来,没人会知道这些。我看过一本书叫《精怪故事集》,这是英国一位女作家搜集的民间故事,她在离世前几周一直在编书,最后没来得及写引言。原版叫《悍妇精怪故事集》,书名就有一种粗鲁的力量,也有残忍和凶狠。她没把故事少儿化、文学化,而是保存民间故事的原始状态。 我从小爱看民间故事,长大以后找了很多书来看,包括袁珂先生对神话的研究。在出版过程中,民间传说中丰沛的内容消失了,精炼后的骨架印在书上,人们得到了一个故事的壳,读完以后获得了一个道理。 外公、外婆身上,承载了我对祖辈的情感,所以会那么深厚。事实上,我的日常是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但在老人身边,就感觉处在一种从容的审美生活里。生活有精细,精细建立在生存之上,好像只是顺手做的,但又产生了美感。老人是从容的,生存压力没那么大,不需要着急地往前。 在农村,小孩愿意和老人说话,老人也愿意和小孩说话,因为他俩都有时间。老人对孩子更多的是陪伴,他不需要像父母一样为孩子规划人生,也就不焦灼,很从容。 我们小区也有很多老人,他们和孩子一样,都被连根拔起。在乡村,老人有权威性,他熟悉这个环境,知道哪有蘑菇捡,知道哪个枝上的果子最甜。他的信心在这,这是乡土给予他的。一旦到了城市,生存法则变了,他不熟悉。老人的根扎更深,一旦被连根拔起,他是慌乱的,脸上会显现出惶恐。 老人在农村讲故事,想到哪讲到哪,走到哪,看到什么,想起来就讲。城市没有这些,他看不到,也想不起。偶尔想到一点,小孩缠着,老人讲一下。但坐在亮堂堂的客厅,讲故事也是不自信的,人对故事的信任感没有了。 在农村,老人会讲一棵树是神奇的,有人要做坏事,但被树绊倒了,摔伤了,坏事就没做成。故事是代代相传的,有的可能就是一些小事,但在传的过程中会变,就有了变化。 Q:可以讲讲自己的写作状态吗?接下来有哪些写作计划? 周静:我一般在早上写,这是带孩子以后养成的习惯。晚上光觉得累,早上精力比较好。睡得早起得也早,起的时候天还没亮,四点多就醒了,不用闹钟,自己就醒了,不分冬夏,写到六点二十,最多写两个小时。 也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可能起来走走,或者吃点东西,然后再坐在那。写的时候喝一点茶,但也不是必需的,可能泡了,写着写着又忘了喝茶这回事。 写一个故事,开头会比较顺利。写不下去的时候,一般是到了中间,故事推进不下去。只能写,不行就删,不断尝试。就像揉面,只能使劲揉它,揉上十次八次就软和了。实在不行,放那醒一会,把别的准备好,再回头揉面。像《鸭蛋湖传说》里的故事,一天写一个就很不错了。 唯一肯定的是,我还会继续写“鸭蛋湖”。我们的神明那么多,我们的民俗生活那么丰富,有太多可书写的。我想在“鸭蛋湖”里构建“离地一尺的精神故乡”,这个故乡是丰富的,故事就要丰富,需要一颗豆、一根草、一棵树、一块地、一间屋舍、一个鱼塘、一点星光……这样一点一点构建起来、丰富起来。我希望通过一部部小说构建一个“鸭蛋湖宇宙”,它能成为有天地神明、人间万物的小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