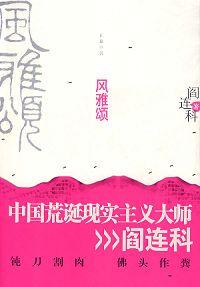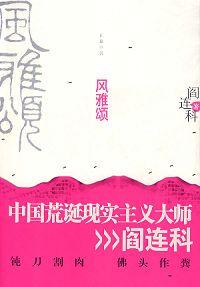无论是用“现实”还是用“荒诞”的标准来衡量,小说的细节都是虚弱而缺乏想象力的,而想象力正是“荒诞”最重要的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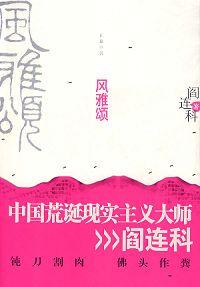
《风雅颂》阎连科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332页,29.00元
两年前在英国时与戴维·洛奇(DavidLodge)聊他的《小世界》,听他眉飞色舞地描述怎么把一大堆校园丑闻、学术猫腻编织到中世纪传说的框架里。这个框架对于整体构思所起的作用,比我想象的更重要———“我在动笔之前盘桓良久,因为我需要某种结构把它们捏合起来”,洛奇说,“当我想到关于亚瑟王、圆桌骑士和圣杯的传奇时,局面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所熟悉的学术环境确实与这些传奇不无共通之处,那些关于荣耀的诗篇,那些长着翅膀的马,那些巫师,都可以成为某种象征。而一旦套用到这样的结构里去,我就可以跳出现实主义的框架,大量运用巧合,加入不少现实主义小说里不可能出现的夸张手法……说真的,我无法抵挡用这种特定的‘罗曼司’类型架构学术小说的诱惑。”
所以,第一次看到小说《风雅颂》的情节从“清燕大学”的八卦开始,而书名乃至各章节名又完全取自《诗经》时,我条件反射地把这两部小说附会到了一起,旋即又自我否定———那可是写《受活》和《坚硬如水》的阎连科啊,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判断,他和洛奇之间的差别,不会比李安Vs张艺谋更小。
读罢全书,验证了附会果然只是附会。据说《风雅颂》发表在杂志上时略多一些现实指向性(比如原先曾出现“无名湖”、“华夏大学”那样让人产生联想的名词,现在只保留了“清燕大学”),但作者自认为这些改动并不影响全局。既然如此,那么我依据成书后的版本所做的判断大抵是可靠的:《风雅颂》离《小世界》很遥远,总体上它不是那种揭秘高等学府、抨击学术弊病的讽刺小说(尽管含有这样的元素,但它的野心远不止于此)。至于所谓的“影射北大”,如果不是纠缠于表象的无厘头批判,便是夺人眼球的图书广告,不值一说的。
然而,阎连科或许在创作过程中,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瞬间,感受到了与戴维·洛奇相似的惊喜———当他想到用《诗经》充当整部小说的线索时,“局面豁然开朗了”。一部企图反映知识分子灵魂的小说,需要一片强大的精神背景,当作者找到,或者说,自以为找到这种依托时,就“无法抵挡”用它来架构整个故事的“诱惑”。于是,在许多段落里,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作者让人物的活动刻意地屈从于预设的框架———惟有在这种刻意性上,它有点像《小世界》,尽管后者的刻意,更多的是出于洛奇所谓的“后现代自觉意识”,是对矫揉造作的反讽。
让我们看看《风雅颂》是如何在《诗经》搭建的脚手架上砌砖加瓦的:杨科是研究《诗经》的大学教授,在无人读诗的年代连课堂出勤率都保证不了。为了让老婆当上名正言顺的“正高职博导夫人”,他五年卧薪尝胆,最后提着《诗经》研究专著《风雅之颂》的书稿回到家,扑面而来的却是老婆与副校长在自家床上肉搏的好戏。杨科步步逼进去,腿一软却跪下来,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誉”,求他们“下不为例好不好”。他们并没有下不为例,但是副校长为了取回丢在杨家的裤头,发了一纸《关于要严格加强〈诗经解读〉课教学的通知》———即便如此,学生仍然以呼噜回报风雅,杨教授在小说中的第一场讲课大戏黯然收场。正当他需要一次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时,沙尘暴适时而来,于是他“爬上某英年早逝的国学大师的雕塑”,进而糊里糊涂地充当了学生领袖,在“还我大自然”的斗争中一夜成名,也影响了“清燕大学”申报国际奖的进程。在副校长的主持下,杨科被众人举手表决,送进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日日以背诵《诗经》打发时光,院长干脆派他对病人实施《诗经》疗法,没想到这一课居然大获成功。院长称,病人只要还有一天为他鼓掌,杨教授就不能出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