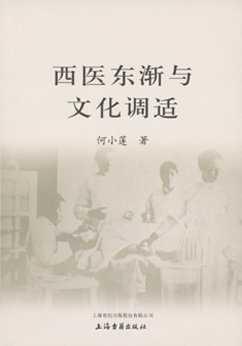 《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是何小莲博士的学位论文。2001年12月19日,她的论文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在这之后,她对论文又作了精心的修改与补充。基于这一研究,她又应熊月之教授之邀,参与了熊月之主持的上海社会生活系列研究中的相关课题。本书行将出版,为这部著作写几句话,当是一名导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是何小莲博士的学位论文。2001年12月19日,她的论文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在这之后,她对论文又作了精心的修改与补充。基于这一研究,她又应熊月之教授之邀,参与了熊月之主持的上海社会生活系列研究中的相关课题。本书行将出版,为这部著作写几句话,当是一名导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医学,因其严谨的科学性、贯穿始终的应用性以及突出的技术性,在现代科学分类中,被划归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之列。医学名家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是以此为依据的。何小莲博士在对西医东传进行系统考察时,注意到西医除去明显的工具性特点以及同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一样精深的知识体系外,作为一种区域医学,更具有极其深刻的人文传统。这种传统与西方哲学传统及基督教传统紧密相关,具体表现为人道主义与有机论立场、生态学与博物学传统、天赋人权意识等等。基于这一认识,本书尤关注西医东传的社会文化内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包括病人托管制度、医生职业许可制度、医生培训制度、医疗档案制度等等在内的医院制度、医疗制度的变革,使本项研究成为一项文化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成为整个西学东渐乃至中国近代化研究的一个缩影。 西医和中医,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不同医疗体系,体现西方与东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根本特征。近代以来,西医又广泛吸取了新兴的人体解剖学、病理解剖学、生理学、细胞学、细菌学及工业技术发展的大量成果,使之又打上了与中医不同的时代烙印。因之,当西医东传来到中国时,与中医、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摩擦乃至冲突便难以避免。尽管西医有其显著的应用价值,要使中国公众自觉接受, 仍必须有效地克服这种因思维方式相异乃至文明相异而引发的文化的、思想的、心理的障碍。 异质文化相遇,从文化摩擦到文化认同,再到文化融合,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进程。本书以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医学活动为中心,对西方医学在晚清中国传播的路径、范围、成效以及其间的诸多困顿,作了系统的审视与清理。作者敏锐地注意到,西医东渐最后可走的路径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这是因为上层精英层处于中华传统的核心位置,对原有的文化依存度最大,对异质文化排斥力最强,而下层普通民众,处于传统文化的边缘地带,对原有文化依存度相对较少,对异质文化排斥力相对较弱。西医东渐之初,也曾试图由中国社会上层即精英层率先突破,但成效甚微,而当转向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下层即民间社会时,反而意外地获得了成功,并反转来影响及于上层精英社会。本书结合西医东渐的过程,研究了在异质文化接触过程中,处于社会文化核心地位的精英阶层与处于社会文化边缘地位的大众阶层对于异质文化认同与接纳的差异,发现处于边缘地位者较易于认同与接纳异质文化是一相当普遍的规律。西医成为东传的西学中最先也是最广泛地为一般民众所接受的部分,原因当即在此。 本书还从异质文化的常态接触传播与非常态接触传播这一视角,研究了西医东传与西方其他文化东传的差异。常态接触传播,指的是西医在与中医共存互竞的状态下进行,在相对平静的氛围中实施,而非常态接触传播则是指依靠强势武力来推进。西方医学文化传入中国,正是凭借常态方式,而减少了敌意和排斥力,与中医文化从共存到逐渐融合,最后成为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医学文化。西医东传及中西医并存并荣,有力地证明了异质文化在共存互竞中,完全有可能形成良性互补的关系。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在每一种文化中,也有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异质核心文化相遇,共存与融合一般较为困难,而异质边缘文化相遇,共存与融合一般较为容易。医学文化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因其普遍的、大众的实践性、应用性,通常属于文化的边缘部分,这也是医学文化互相接触传播时,相对容易通过常态进行,也相对容易共存乃至融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