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辞赋的滑稽成分,有许多是基于具体源文本的转相祖述。扬雄的《逐贫赋》和韩愈的《送穷文》是将“贫”“穷”拟人化以自嘲的俳谐佳作,而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互文关系 [1]。宋人创作以二赋为本,或铺采摛文,踵事增华;或反其道而行,翻新出奇。赵湘的赋体文《迎富文》[2]顺二文之势,在送穷、逐贫之外,以迎富构思,同一机杼,各写两边,所趋相同。赋中铺排仁富、义富、信赋、孝富,意在说明若仁义信孝,即使贫穷,人格上也是富有的,人生也是充实的。读之令人会心一笑。王之望的《留穷文》基本上是对韩愈《送穷文》的模仿,其中描写个人际遇一段,完全脱胎于韩文,只是描写更为具体,语言更为整丽流畅。通过这种对原作毫不避讳的有意“冒犯”来与之争衡,是宋人惯常的做法,意在显示自己的才华不输前人。而且,这种模仿不是偷偷摸摸的,作者故意强调了作品与韩文的联系:“吾读韩子,久闻尔名,谓子有知,庶几神灵。子则不然,憎贫弃旧,我不尔驱,尔顾我咎。凡人之生,各有定分,贵贱穷达,造物所命。天生我穷,令与子俦,命实为之,汝安归尤?物极必反,否泰相缪,吾穷久矣,庶其有瘳。”[3]这是在说此作是受到韩文的启发,见识之高下留待读者评说。作者想在词章和义理方面和韩愈争雄。如果对韩文不了解,此赋的意蕴可能难以理解透彻。崔敦礼的《留穷文》则反扬雄、韩愈之义,铺写五穷,即仁穷、义穷、礼穷、智穷、信穷,暗扣赵湘《迎富文》主旨,意在强调人有此五德,何穷之有!将二文之义又转深一层。区仕衡的《送穷文》之于扬雄《逐贫赋》,与王之望《留穷文》之于韩愈《送穷文》一样,都是通过故意模仿来和古人比试高下。赋作对贫苦之状的模仿极其精彩,铺排更为具体深入,语势更为流畅自然,富于气势,节奏更为顿挫,内容上也更具生活感。如果是与作者境遇相仿、或者是同时代的人阅读此篇,较之韩文的感染力将更为强烈。与此相类的俞得邻的《斥穷赋》则是责问人世的不公道,这就使扬雄、韩愈二文讨论的问题转向人生困惑的角度。可见,宋赋的滑稽描写在转相祖述的过程中,源文本的语词、主题、结构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充实和发展,词章方面也不断得到提升,内蕴得到充分挖掘,宋人往往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对宋赋滑稽艺术的理解,若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很难理解其中之况味。 宋赋滑稽的互文性流变,是一个不断增饰、变形的过程,有时候其对源文本的扩大、升华,呈现出意义上的“增值”特点。苏轼的《后杞菊赋》仿陆龟蒙的《杞菊赋》,二赋均表现贫而餐菊的洒脱人生,苏轼将此境界表达得相当传神:“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几个问句咄咄逼人,引发读者对齐物达观的深入思考,暗示膏粱肥腴与糙粝藿食没有本质区别,然后以轻快的语调写出餐杞菊不仅可以果腹,而且可以助寿。其中流露的自解自嘲情绪令人发噱,这比源文本只是阐述杞菊助寿要深刻得多。如果再联系苏赋的上文,其调侃用意便豁然开朗:“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大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椽属之趋走。朝衙迭午,夕坐过酋。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身为太守而食藿充饥,未免太夸张了,其实,这是在拿新党执政减少官员薪俸的举措来调侃。作者想说的是,王安石是要让官员们都成餐菊延寿的世外高人!张耒的《杞菊赋》大肆美化苏轼的餐菊之举,借此彰显自己作为新法对立面的政治身份,作者在赋中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新法的反对者,都是像苏轼这样的君子,都具有像屈原那样的餐菊饮露的高洁品格。思想意蕴比苏轼更进一层。张栻的《后杞菊赋》则是借苏轼餐菊的形象来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超过前两篇,文章把苏轼的自解自嘲提升到一个哲理的高度,这只有在阅读前两篇的基础上才能够体会出来。应该说,滑稽的增值现象在宋赋中是相当普遍的,这正是其文学追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倾向在辞赋中的表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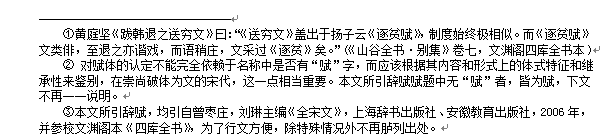 宋赋滑稽描写的互文性有时不仅立足于某一篇或几篇源文本,而是对于各种文学作品共同表现的某类意象的融会贯通与铺张排比。它的互文是针对某类内容或某类思想的。薛季宣的《七届》铺写七种人生追求,第一部分放笔铺排饮食和美女的诱惑性。这类描写在楚辞《招魂》中就已露端倪,继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后,女色的描写在舞蹈、音乐、神女等辞赋中逐渐泛滥,甚至像张衡的《南都赋》等都邑大赋也时或有之。对饮食的描写,枚乘《七发》较早涉足,以后在都邑赋和“七”等辞赋中几成俗套。枚乘的《七发》指出享乐生活是“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薛季宣的描写要比枚乘详细得多,他显然不是单单对《七发》的模仿,而是针对前代一系列关于饮食男女的作品的,在几成俗套的滑稽描写中,作者希望自己的文笔更具辞章方面的审美性,更具哲理的深度,更吸引人。赋中点题道:“瞽哉!燕安枕藉,吾知其斧斤酖毒也,不知其它。”这和《七发》的“伐性之斧”之说遥相呼应,但是它又不单单是绍续枚乘之说,女色伤身是古人共识,《庄子?达生》曰:“人之所畏者,袵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戒者,祸也。” [2](P117)汉严遵《座右铭》:“淫戏者,殚家之堑。”[3](P360)嵇康的《养生论》曰:“唯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4](P151)乃至于孟郊的《偶作》还说:“利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 利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 道险不在广,十步能摧轮。情爱不在多,一夕能伤神”。等等。显然,薛季宣的描写以及观点是对一系列作品和见解的总括。范成大的《问天医赋》对于这一系列的话语表述,其互文性的表达更具概括性:“人之多疾,自取自探。不一其凡,大略有三。其一者心根泄机,命门丧阻。明消精散,形弊神苦。掷温玉以畀火,奉甘餐而戏虎。阴惑阳而化蜮,风落山而成蛊。若是者得于晦淫,命曰伐性之斧。”[1]作者之所以没有详细阐述食色害人,是基于对前代类似文本的互文性概括,暗示读者去联想类似的前代作品。林半千的《遣惰文》沿着薛季宣的路子,融饮食与美色于一体,他将之概括为人的惰性,该赋模仿屈原《招魂》的结构,把灵魂的流荡往返置换为心志的懈怠低迷,内容上则是如薛季宣赋那样,立足于对饮食男女的描写。 宋赋滑稽艺术的互文性特征,建立在他们良好的学术修养和文学素养之上的,他们在对前人的模仿中同中求异、求变,力图檃栝前代作品而有所突破,有所变异,这和“抄袭”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实,文学的发展就是通过融汇前代成果并不断创新来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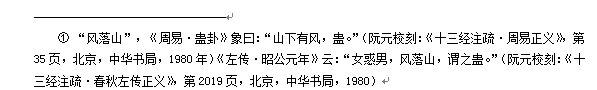 二、游走于雅俗之间的诙谐幽默 关于宋代文学的雅俗之辩,古今论述汗牛充栋,由于雅与俗是一对具有感性色彩的伸缩性很强的概念,要犁然分明,并非易事。宋代士大夫是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文化精英阶层,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具有高度自觉的认同意识。这种身份认同不仅表现在他们具有较之前代任何时期的文人更为强烈得政治抱负和使命感,更表现在他们对低俗、庸俗情调的警惕、抵制与排斥。他们希望通过超越性的思维和心境来理解人生,感受生活,拒绝平庸浅薄的趣味,他们追求不累于俗、不受制于外物束缚的精神愉悦和贯通历史与知识的远见卓识,以达观超然的态度和深刻的哲思来化解生活中的不快、不幸,在自嘲自讽中获得精神的升华。他们眼中的“俗”,不仅包括平庸的情调,也包括作为这种情调的载体、形式,以及庸常生活中不具有高雅气质的琐细微末之物态。他们对于无处不在、触目可及的“俗”,大多采取以俗为雅、化俗趋雅的“提升”的态度。滑稽艺术从一开始就与世俗有着亲缘关系,低俗、浅俗、媚俗甚至是滑稽的重要构成元素。对于滑稽的世俗特色,宋人在辞赋创作中同样以提升的态度来面对,而非拒斥。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的宋赋,在庄严与轻佻、高雅与平庸的巨大反差中凸显着滑稽艺术的幽默诙谐特色。 生活中的琐细之物、庸常之事,是咏物赋的表现内容之一,其潜在的滑稽因素颇为赋家看重。宋人用流畅优美的文辞来铺写这些俗物俗事,使其脱离那种鄙俚浅陋气息,以文雅写庸俗,同时,这类作品惯常的粗俗噱笑被提升为超越凡俗的高雅趣味和高妙道理,以雅趣化俗情,使其与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好尚想契合。蛙的可憎面目和其鸣叫的聒噪不已是它成为俳谐文学热衷表现的对象。张耒的《鸣蛙赋》紧扣悲和乐,组织一连串的比喻,描摹蛙鸣执着、持久、放肆、呕哑嘲哳的特点,作者在结尾加了这样的一段:“尔其困于泥潦,失其所处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处而乐也。”蛙絮聒不已的呼号,是缘于得时抑或失时呢,这就在蛙鸣与文人对人生的思考之间建立起若隐若现的联系,得势者的炫耀鸣唱不就像蛙鸣那样惹人讨嫌吗,困厄者的悲叹号呼不就像蛙鸣那样焦灼悲酸吗。顺着这个角度去体会,作者对蛙鸣的描写不仅仅是引人发噱,更有关注人生、默然心会的苦涩一笑。结句的一点,使具有世俗色彩的滑稽描写具有了一种符合士大夫雅趣的深远韵味。李新的《蛙赋》显然受到张耒的启发,赋以与蛙的对话结构全文,对于自己的呼号不已,作为居士的蛙是这样回答的:“兴《考槃》之歌,赋《衡门》之诗,引《泽畔》之吟,咏《北门》之薇。士不得志,故嗟叹之。鸟鸣常山,孤雉朝飞;杜宇亡国,秋猿号儿。物不得平,哀也无期。”蛙的鸣叫与有志不得伸的屈原等贤人同调,蛙鸣与贤人失志的高雅主题联系在了一起。南宋理学家杨简的《蛙乐赋》循着这一思路,以相当优美的比拟来描摹蛙鸣的悦耳动听,说蛙鸣如黄钟大吕振奋人心,那声音的特点是:“其莹然之鉴,澄然之渊。至动矣而静,至繁矣而不喧。是音也可闻而不可听,可以默识而不可口宣。”单调的聒噪居然有如此悠远的美韵,给人些许无厘头的感觉。作者解释道:“孔圣遇之而忘齐国之肉味,黄帝得之而大张于洞庭之原。胡为乎独不见省于横目之士,至憎而为烦?甚以为冤。冤矣乎,冤矣乎!”原来蛙鸣是天地之间天理或道统流传之一个环节[1],大乐与天地同和,只要人们进入仁者境界,难听的蛙鸣可以成为天下最动听的音乐。蛙鸣之为凡俗讨厌,与当时道学家的“鸣道”所遭受的世人非议极其相类,这种巧妙的构思和深邃的思致是非寻常人能够行之笔端的。刘克庄的一篇描写蛙鸣的“失题”之作可能是出于对杨简以蛙鸣写鸣道的不满,赋中对蛙鸣近乎谩骂式的宣泄,其背后隐含的士大夫文人思想争锋的意气用事,合而读之,令人发噱。可见,宋代的赋家缘于自己审美立场来感受、体会琐细之物,在俗之物象和雅之情趣之间,巧妙地建立起联系。李刚的《药杵赋》和刘子翚的《闻药杵赋》能把捣药的单调声响描绘得如音乐般动听,苏轼的《菜羮赋》、陈与义的《玉延赋》能把野菜、山药描写成天下致味,等等,都是通过俗物俗事来感发文人士大夫雅怀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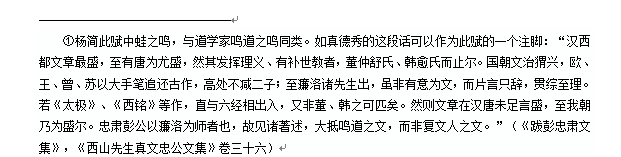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