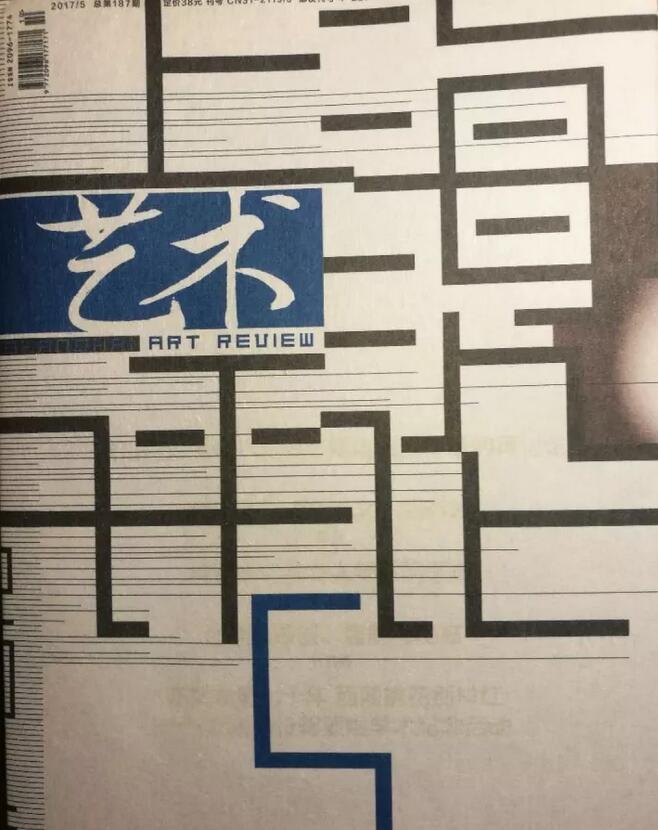 我们曾致力于区分神话与宗教,认为前者属于作为艺术一个门类的文学,后者是一种信仰体系。这是一种共时性的现状分析,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社会学上的处理方式,以及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所决定的区分。如果将之放在历史的维度之中考察,就会发现,两者并非完全不同、相互绝缘。希腊神话就是希腊人的宗教,只是在没有人信这种宗教时,它才变成神话。同样,在北欧,原来也有一套自己的从属于维京(Viking)人信仰体系,基督教到来之后,这些信仰体系崩溃了,就变成了神话。中国古代也有这种情况,许多神话都来自前朝的信仰。 由此,“神话”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不信”。当我认定你说的话和事是“神话”,我的意思就已经包含着,它与我的信仰体系不兼容。然而,“不信”不等于不喜欢。一些成为美的欣赏对象的事物,原本常常是作为崇拜的对象存在的。在作为崇拜对象之时,笼罩在它之上的,是一层神秘的面纱。当这层面纱被揭去之后,它就成了审美的对象。 从叙事的角度看,神话与宗教遵循着同样的逻辑。神话与宗教不同之处在于,当一种叙事不再依托信仰体系而存在,不再具有强制性之时,美就成了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在哲学中,“我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为什么“在”?笛卡儿说,是由于“我思”。仿照这个句式,人们造出了许多的句子:“我说故我在”,强调言说的重要性。“我作故我在”,强调动作性活动,以至人的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进而,有人造出“我感故我在”、“我爱故我在”、“我信仰故我在”、“我抗争故我在”一类的句子。随着市场和新媒体的发展,又有了“我消费故我在”,“我上网故我在”,等等。这个句式可以无限的扩张下去。这时,考察的重点,都在“我”。将世界化为“我”的感受与作为。 然而,世界是如何起源,又是如何存在的?当世界成为“我”的感知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问一个问题:别人的感知呢?当世界成为“我”的思考时,人们就会想:别人也在思考着。回到起源,这也许是一个解决途径,看看原始人怎么想的。 在几乎所有的神话中,都有关于起源的神话。无论在希腊神话,还是北欧神话之中,神都是从一种自然的力中生长出来的。在希腊神话中,从法那斯,经纽克斯、乌拉诺斯、克洛诺斯,到宙斯,是第五代。法那斯的意思是光,法那斯可被视为男性,或者雌雄同体,而代表夜的纽克斯是女性,她与法那斯密不可分,最终接替法那斯成为一代神王,下一个是乌兰诺斯,他是天空之神。接下去是时间之神克洛诺斯。经过这四代,终于到了第五代,即宙斯。在北欧神话中,从代表着不可名状的“力”奥尔劳格(Orlog),到从寒冷的霜冻中而生的冰巨人伊密尔(Ymir),再到冰逐渐消退时出现的祖神勃利(Buri),再到勃利之子勃尔(Borr),直到主神奥丁(Odin)的出现,经历了至少五代。这五代神王,与希腊神相仿,都暗示着神力与自然力最初同源,而神力又逐渐克服自然力。 中国有所谓盘古开天地的说法,颇为奇特:“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艺文类聚》)盘古是一,三皇是三,五帝是五,由此,遵循数的规律,天地人文得以起源发展。 在创世神话之后,有正邪相争的神话,大洪水神话,等等,不同的神话叙述不同。但是,各种神话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就是,造人的主题。 在希腊神话中,人是由一位不属于宙斯的奥林帕斯神谱系的普罗米修斯捏泥而造。在北欧神话中,则是诸神用树枝造人,而由奥丁给他们以生命和灵魂。在中国神话中,人是由一位女性的神女娲抟土造成。 与这些对“工匠精神”的强调相比,《圣经·创世纪》则简单得多。书中宣称,神在六天之内造出了世界,而所造的办法,就是“神说……”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如此等等,似乎在暗示,神说要有一切,就有了一切。 这些论述被赋予了哲学的解读,形成了一种“以言成事”的观点。这种说法很流行,但实际上是断章取义而已。“以言成事”有着不同的理解。不能理解成《圣经》中的神是动口不动手,有一种神力,能一说就成,不需要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性抗争,不需要奥丁的勇武战斗,也不需要女娲的辛苦劳作。 “言”固然能“成事”,但这里有一个如何“成”的问题。如果细读《创世纪》,还是能从字缝里看出意思来。神是在造物,这里的“说”,只是说出意愿而已。神是动嘴又动手,以至于六天造下来已经疲惫不堪,“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说明神忙得很累。作为进一步的佐证,《创世纪》中说造人时,特别描绘了过程:“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既造人的肉身,又赋予他灵魂。 神不是一位仅仅坐而论道者。他说要有什么,不代表没有伴随的行动。这种将伴随行动抹掉的做法,是哲学家们的偏见,他们将话语所表示的意愿与实现这些意愿的行动区分了开来,而只强调前者,舍弃掉了后者。 当然,在神话中,一切逻辑都有可能。但神话的逻辑,其实还是生活逻辑的折射。世界是行动的结果,不是思维的化身。经过千年的经院哲学的发展,世界变成了神的象征,这种思考是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其实,世界只是创造过程的结果。 说完这一切,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种种的神话传说,包含有三个含义:一、世界如何“在”要优先于“我在”;二、神最早是自然力的体现或象征;三、世界和人都是神的物质性劳作的产物,而话语只是劳作过程的伴生物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