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M.库切

《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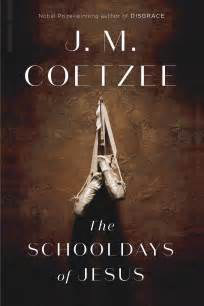
库切新作《耶稣的校园时光》
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致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
——本雅明评保罗·科利画作《新天使》
现代社会里,有公信力的文学奖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批评,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依据,也是文化消费市场中体制化的能动者。批评者从孤独的个体走向群体,评奖过程与颁奖仪式愈来愈从狭隘的文学圈子里“溢出”,变成公众话题。就文学社会学而言,文学奖提供了一个“权威阐释”的集体展示、一种主导性艺术意识形态对于“标准共识”的召唤与归纳,以及一个“新经典”作家/作品定性和时代文化资本等级的认证。凭借长篇小说这一文体,1983年、1999年,南非作家库切两获英国布克文学奖。借用世界文学为背书的亚非文学这一文学史范畴,在此或可以谈谈文学奖视界里的库切。
布克奖:“全球化”如何置换“帝国”?
布克奖于1969年横空出世。它起始的评奖准则是:“设置标准,传播小说,扩大读者群,增加销量,使小说这一形式受到重视,并使作家受益”。布克奖由出版商和伦敦文化圈共同操作,其管理委员会和评委是两套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管理委员会由赞助商和出版商主导,评委则主要是来自伦敦的文化精英。他们试图打破战后封闭、保守、自娱自乐,且受到美国文学严重威胁的本国严肃小说写作局面。
当时,作为19世纪日不落帝国遗产的一部分,英语文学仍然具有一种全球文学的潜力。布克奖管理委员会敏锐地抓住了此点,他们提出一个基本信条:英语文学的生产和消费皆为全球性的。这让它很快走出国境,在英联邦文学——这一在上世纪90年代被后殖民文学所正式取代的范畴内,寻找位于业已崩塌的帝国曾经的边疆地带的文学表达。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其评审原则最终精简为:选择本年度在英国出版的“最好看的英语长篇小说”,并在2014年吸纳被长期排斥在外的美国作家,于2016年将其颁给非裔美国讽刺作家保罗·比蒂。
作为一个公认的英语长篇小说的权威奖项,布克奖的成功在于它实现了国家文化身份建构、强势语言扩张和文化消费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它重视作品在风格、题材、主题上的陌生感以及叙事上的创造性,擅长于制造阅读热点,炒作各种话题、论辩、悬念,趋向于制造文学明星和挖掘无名作家,在相当多的年份都成了提携新人的舞台。1983年,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库切能凭借《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战胜当时如日中天的萨尔曼·拉什迪的《耻辱》,很难说与布克奖的“新人”倾向性无关。布克奖还和以BBC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有着密切的合作,颁奖典礼模仿奥斯卡,入围名单和最终获奖作品往往是圈内人、出版商和普通读者相“协商”的结果。同时,它还是影视剧改编和外文翻译的“孵化器”,获奖作品一般会销量激增,且可获得多个语种的翻译出版合同。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已有五分之一强的布克奖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不乏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英国病人》《奥斯卡与露辛达》这样的成功之作。
布克奖的评委需要大量阅读那些由出版社推荐的,甚至是从未耳闻的作家作品。在客观上没有市场销量和批评家意见作为参照的状态中,评委们的趣味、发现经典的能力以及小说的探索性和形式创新成为了重要指标。它更多依赖于对普通读者阅读期待的预判。那么,相对“曲高和寡”,同样“值得尊敬、道德上直言不讳、政治上发表异见”的《彼得堡的大师》《耶稣的童年》无法获奖,由西方提供话语,由本土提供饵料,立足探寻南非经验、讲述南非故事、揭露南非现实黑暗面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耻》能顺利获奖,自然在情理之中。2016年的布克奖评委们为了追新,甚至制造了将库切尚未正式出版的《耶稣的校园时光》列入长名单的“乌龙”。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南非作家的写作都被认为是采用“反抗的形式”的现实主义谴责文学,具有“明显的即时性的政治后果”。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一个大部分为文盲的国度里,库切作品最好的读者是负责“出版控制”的审查员和少量知识分子。而在“严肃小说根本没有市场”的南非,库切早期的实验性创作因其知音寥寥实际上是无需大改就直接上市的。就在攻打南非(甚或可以说整个非洲)的现实主义堡垒失败之后,在布克奖的烛照下,库切却在另外一个二战后的现实主义堡垒——英国——获得了成功。他遭遇的是帕慕克在《你为谁而写》里界定的——追求异国情调的一类读者:“他们渴望打开一本书,进入一个与世隔绝的异国他乡,他们渴望观察这个国家的内部纷争。”鲁迅早就观察到这类现象:“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外国所注意。”经由布克奖的大力推荐,读者将库切早期那些充斥着叙事诡辩术、冷峻身体暴力书写、尖锐知识分子批判的小说,视作缓解南非种族和政治紧张的一面破碎的镜子,尽管他们只能通过拼贴碎片打造映象。同时,一些文学理论家倒果为因的学术研究,也助推了这种想象。他们将库切的小说定位为自边缘回望中心,提出质询,拥抱颠覆,契合欧美英语阅读市场预期的逆写“帝国”的“对抗性”写作;某种建立在西方读者刻板印象基础上的,对于混乱、黑暗、充满创伤记忆的“前殖民地”境况的文学想象。库切的作品被解读成刻意追求后殖民批判效果的文本,而评论者没有充分意识到,正是库切的早期创作参与了这一研究范式背后概念、观念和解释体系的初始建构。最是强调意义及价值的不确定性的库切被认为需要对南非的政治状况负伦理责任。致力于解构历史叙述本身可靠性的库切的文本,甚至进入了旅游手册,最终成了英语世界了解南非的一个窗口,库切成了“米老鼠”般的后殖民主义作家。这和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红高粱》时,特意加入一个明显误读,带有宏大叙事色彩的副标题“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一样的荒诞,一样的刻奇(kitsch),一样的迎合市场。
“在世界的碎片和历史的废墟上思考”:
经验及其讲述方式
库切是典型的学院作家,走的是二战后美国作家所常见选择的道路:进入大学教书,既是小说作者也是精英读者,有时还会兼职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某些时刻,他的批评文章远比小说更显坦率,更有耐心,更为精彩。他的学术文字和小说家言构成了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本雅明、贝克特、布罗茨基等人的阅读体悟,会直接体现在他的虚构作品之中。在亚非文学的视野里,他的作品大多都是站在“第三世界”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上,越过“第二世界”,直接从“第一世界”寻找资源的结果。库切自由出入于欧美前辈大师搭建的世界之中,少见哈罗德·布鲁姆定义的“影响的焦虑”之流。他重写、改写、反写、拟写《鞑靼人沙漠》《群魔》《鲁滨逊漂流记》《神曲》《七武士》等经典之作,在解构/重构经典之作之余,施展他所意识到的“历史的狡黠手段”。
在库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建立在审慎的怀疑论基础上的知性的诚实。在他的笔下,即便是充满抚慰意味的乌托邦,也不过是历史乱流中那些隐秘的、碎片状、充满创伤记忆的边缘之地,制度野蛮性、语言多意性和能指多可能性的另类表达,直指哈耶克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作为一个出生在南非的阿非利勘人(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种族集团之一)、用英语写作的前殖民地作家,复杂的文化认同和流离失所的位移姿态,使得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与一个分裂的、论辩性的自我战斗的过程。竹内好在讨论鲁迅时,用一种启示录式的语言,非常准确地把握住了这种“两间余一卒”立场的内在痛苦,“与自身中产生的‘阿Q’”的永恒战斗:“他是论争者。他通过论争,与在他之外、被他自己外化的东西进行论辩。这种论辩的场合也就是他表现自己的场合”;“他不断地从生成自己的基础上涌现出来,而涌现出来的他常常就是他本身。”通过一种将包括自我在内的整个世界对象化的方式,库切对于“离散”状态既有一种切身的创伤感受,又对其有一种拉开距离的“隐喻式”的把握,虚无但不乡愿,后撤却从来不曾妥协。库切的小说在后现代主义面上追寻自由实则保守退缩的文化政治状态,与反殖民、反暴力、批判强权的激进立场之间,建构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二者相互冲突,不断交锋,同时又互为背书,互相寄生。
库切坚持探索和实验,很少自我重复,不断寻找叙事的可能与边界。他的每一部作品均有新的尝试,但又并非那种盲目的创新,只是在文本内部寻找与表达内容相配合的格式与语调。他的新著《耶稣的校园时光》“退缩到一个虚幻的世界里,他觉得只有在那儿他才能把握自己”,于平地起高楼,没有时代,没有实地,人物的记忆被删除,身份被篡改,用隐忍不发的、消除了一切华丽修饰和南非印记的语言,讲述一个一切激情均被压抑的反乌托邦故事,读来宛如进入了一个冰冷的、“无历史的”、叔本华所不懈探索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于沉郁顿挫的整体文风之外,库切总要写出隔绝在历史的幽暗之处、虽微弱但仍对整个世界释放善意的一抹亮色。严肃阴郁的写作中,偶有灵光一闪的诗意抒情。毕竟,在无信仰者的人群中,诗歌可以取代信仰。这些“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鲁迅语),使得他的作品没有滑向“存在即合理”的虚无泥淖,总有内容指向情感升华。《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中生机勃勃、杂色错综的结尾,将无比壮阔的非洲大地演化成了人的忧患、窘迫、压抑得以净化的福地,远遁宇宙洪荒未起之时,不再“纠结”,且听天籁,充满了“天道渺远、人如朝露”的清新气息。
“讲故事的人”:来自严肃作家的邀约
库切写的并非都是单纯反映“只阅读经典的那部分精英读者的兴趣和态度” (卡维尔蒂)的作品。为了照顾那些有想象力的懒散读者,他倾向于采用一种让简单的回归简单、让复杂的仍旧复杂的写作策略,作品写作与普通读者的阅读趣味之间保持着一种颇具匠心的弹性关系,既适合做深层阅读,也适合做表层阅读。在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的年代里,当严肃文学无法承担情节和意义完整性的重负时,库切“礼失求诸野”,孜孜于充满戏剧化的类型小说的情节设置。库切热衷于写暴力罪案过程及其审判。这也是为何有着贝克特随想曲风格的日记体小说《内陆深处》能被改编成电影《尘土》,以及充斥玄思冥想的《等待野蛮人》能被改编成歌剧商演的原因。
库切是英语散文大师。他文本中让人沉溺其中的、富有穿透力的语言,验证了苏珊·桑塔格的经典判断:“自福楼拜以来,散文总是在追求某种诗歌的密度、速度和词汇上的不可替代性。”他的文字有一种强烈的密度感,语言犀利准确,少见华词丽语,却有一种精雕细刻的美感。闲言碎语间充满思辨意味,很多段落甚至让人觉得讲述者写作的惟一目的就在于这种密度感,读来如临弱水,一切漂浮其上的终将沉沦。在描写一个戏剧性场景里人的心理流动的“节奏与句法”上,库切已臻化境。
尽管其作品整体上堪称“烧脑”,但库切几乎很少在传统小说所重视的故事张力、情节悬念与人物行迹上“动刀”。他的小说大多是“羊皮纸”写作,内部存在一个双重叙事运动。撇除掺杂其中的精深细微的哲学思考、伦理学阐释与政治学寓言等等模棱两可、“用隐形墨水写就的文字”,写给理想读者(或者说作者的读者)的内容,故事一样是可复述的,深具阅读兴味。同时,库切的数学、计算机、语言学以及荷兰语、德语的背景,也让他对于形式有着迥乎寻常的讨论和探索兴趣。库切“对叙述者及人物话语的巧妙安排,对作品形式素朴却别具匠心的把握”(段枫)使得其言辞隽永、简洁准确的作品成为可以多次重读、每次均有新发现的阅读盛宴。写作时,他并非一言而决的独裁者,相当多情况下,甚至会被“暴乱”的人物和情节逼到墙角,不知所措。库切还异常关注大历史笼罩下身处边缘地带的异己者、卑微者、无权者的内心世界,特别是那些人群中的孤独者,拥有无望的人生、坚韧的内心,与所谓文明反向而行的“畸零人”。由此,他的作品出现了不少经验作者不能让其发声的神秘“失语症”患者(星期五),或者是拥抱执念、不想说话、不愿进食的人物(迈克尔·K)。
布克奖是在英国国家转型或者说价值观急剧变动时刻出现的文学奖,它难免被赋予了参与重塑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重任。在这一背景下,库切的获奖(以及无法获奖)在文学史和文化研究的视野里都意味深长。库切两度获奖,不仅是对其作品艺术价值的肯定,还带上了打造全球英语文学版图的历史动机,通过一种“在经济学上,把敌人转换成竞争对手;在知识论上,把敌人转换成争论对手”(施密特语)的方式,布克奖与库切之间成功实现了“双赢”。昨日“拒绝阐释”的激进探索,变成了今日拓展英语“世界文学”写作版图的文学常识。在库切充满寓言气息的长篇小说中,我们可以发见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和身份焦虑。在所谓后殖民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幻觉中被消解成为跨国资本主义文化消费的对象,“流民”、“放逐”和“边缘性”因之不再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年代里,库切艰难的形式探索和真诚的写作实践,更显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