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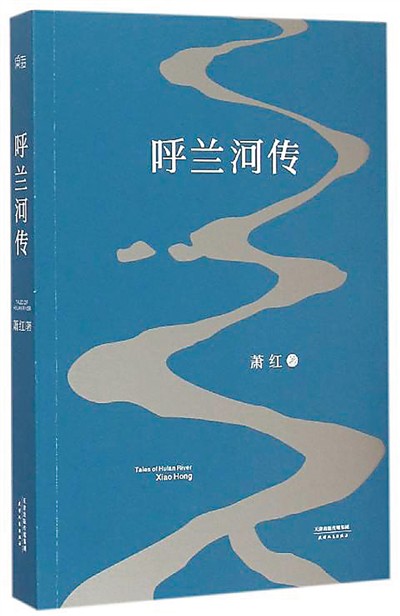

多年前读过《呼兰河传》,那时年轻,留下的只是一个浅浅的影子。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历许多风霜,愈益为思乡的情结所苦,重读得到的是深深的幸福与感动。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之一,亦是现代文学“最美的收获”之一。萧红构思于1937年的武汉,因时世动乱不安,转徙流离,直至1940年12月才在香港完成。这部倾注萧红巨大心力的作品1940年9月1日至12月27日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翌年5月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单行本,此时距离她的英年早逝,不过8个月的时间。
萧红自20岁离家,备尝饥饿、寒冷等人世艰辛,不和谐的感情生活又使她屡屡怀着一种忧虑的心境,以致她经常感受着深入骨子里的孤独和寂寞。好在有一支笔不离不弃。她用它恣意表达性灵的受难与飞翔,描绘人民、民族的苦难,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萧红拥有两套笔墨,两种才情。一方面关心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一方面又专注自己孤寂的情绪,对爱和温暖的追求与向往。前一种使她与文坛主流保持了步调上的一致,而后一种,又使她处于主流之外。
后期萧红的写作逐渐远离了抗日主题,她运用一种更加长远的目光,将对国家民族的关心转移到另一个焦点上:批判国民性的痼疾。因为这些痼疾是中国积贫积弱及受列强欺侮的根源,而扫除这些痼疾,则是中国再造的基础。萧红曾经说:“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她的这一追求直接受到鲁迅“改造人的灵魂”的写作导向的影响。
她在经历了更多的流离、孤独、无助,甚至屈辱之后,对人生的悲苦有了更深的感触。写作成为她自我疗救的重要方面。对故乡和祖父的怀恋给了她温暖、慰藉和安全感。之于她,故乡虽意味着无法抹去的伤,但一直潜藏在心灵深处。1936年,萧红感情受挫,东渡日本,实际上不仅心情没有转好,反而更孤独,更寂寞,加之随后鲁迅先生的死,以及日寇的侵略,故乡的沦陷,她那种怀乡的情绪更重更浓了。以至于一直到死,她都梦想着回到呼兰河。
这一切,促成了《呼兰河传》的写作。它是回顾故乡时检讨和爱恋等复杂态度的嫁接物。
《呼兰河传》共分七章,每章都可单独成篇,但合在一起,又相契无间,缺一不可。因为本书的主角不是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整个呼兰河城,这城的善、恶、美、丑,堕落及坚强。这是有着自觉启蒙意识和人道情怀的知识分子萧红和具有思乡情怀的游子萧红之间的一次巧妙遇合。结构的“杂糅”契合了她那种对呼兰河既爱且恨的态度,那种在回溯时总结的意图:既要批判,又有温馨,又有憧憬。这三者在书中达至了巧妙的平衡。
如果我们运用一个足够大的放大镜或比例尺,便会看到,呼兰河城其实也即老大中国的一个代表。萧红其实是欲借呼兰河城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单调停滞、因袭重担的“老中国”本身。这批判又以深沉真挚的热爱为前提。她希望中国新生,希望中国跃变为真正尊重人的尊严、充满理性、健康向上的社会,她希望中国人民坚强地走下去。
《呼兰河传》在写法与风格上颇具独异之处。它不充分具备经典小说定义中所说的“三要素”: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它没有中心人物,没有扣人心弦的向前推进的情节,而环境的描写也不是为了塑造人物、渲染情节。小说重视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及场景的描述,对于某种氛围的渲染;写人也往往不求全,而重在描画人的精神。在《呼兰河传》的写作中,萧红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介于小说、散文与诗之间的体式。这种体式虽然她一直在运用,但直到《呼兰河传》,才形成了美国学者葛浩文所说的“巅峰”。
萧红善用“大白话”,又喜一种可称为“稚拙体”的语感,有时竟让人觉得是小学生在写作文,而多处写得竟像是“废话”。萧红具有那种化平淡为神奇的能力。这些“大白话”一经她的点染,便具有了“成金”的效果。语言虽朴拙,但诗意的情调、氛围、意境却突出了。赵园认为萧红深得古典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不落言筌”“得意而忘言”的神髓,意在创造一种蕴蓄着的情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味”的文学世界。这种“味”其实更像一种氛围,伤感的,抑或明快的氛围,它必须靠精细的感觉、体会才能获得。获得之后便很难去除掉,它甚至进入你的身体、灵魂,你一回头,一探身,便可看到它。有时,你满眼浮现的竟全是它。
她的笔触中也有幽默和讽刺,不时使人忍俊不禁,但多半是“含泪的微笑”,因为它有一个“荒凉”的感触、一种对于民族痼疾的忧痛做底子。当然,明朗时又非常明朗。
书中的很大部分采用儿童视角来叙述。许多章节颇有儿童文学色彩。作者通过儿童视角的运用,复苏了童年的记忆,也给了读者回望童年的杠杆和凭借。或可体验诗情,或可得到教益,也大可见仁见智。
这些均是属于萧红的独有的才华,是她真挚心灵的一种温婉的外化。无技巧,是大技巧。
可以说,《呼兰河传》是一部意蕴丰厚、技巧精湛的成熟之作。它证实了一个公认的结论:好的作品必然是多向度、能引起人们的不同理解与阐释的。你尽可好好理解作品美妙的浑然一体性,但也可抓住一点,而忘情流连,深入思考。当然也可以从更终极、更具哲思性的意义上思考人类生存的困境,以及更普遍的人性。或者仅仅陶醉于那美的文字,以及氤氲其中的迷人的味道、意境及神韵。正因为如此,茅盾称它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