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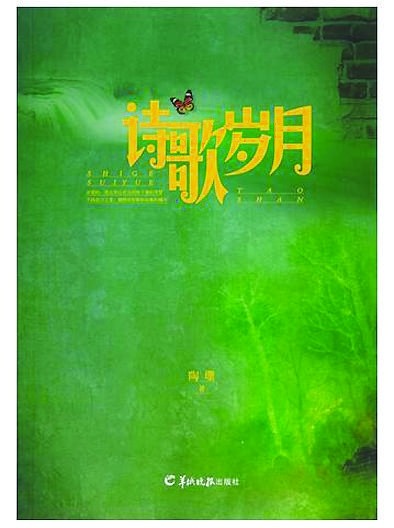
在时间的不见头尾的长绳上,破碎的生活总在不停地上演一幕幕悲喜剧。其中的场景似曾相识,但大概都是在别人的生命剧场里,看到曾经、眼下甚或未来的自己。对于作为个体的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一次次看似“理性的选择”在事后看来常常是盲目的。重来从来都是奢谈。选择没有是与非,对缺乏经验的个体生命而言,通常意味着两难。逃不脱的俗世常常规定了我们生活的形态,秩序井然,壁垒森严,将人类所谓的理性消解于无形,经不起追问。
陶珊长篇小说《诗歌岁月》讲述的是一位诗人的诗歌之路。俗世给小说里的主人公苑香妮规定了一个尴尬的身份:城市中的农民。由于是农村户口,在改革尚不彻底的年代,她“只能背负着农民的身份,尴尬而卑微地生活在城市的缝隙中”。但这并没有影响主人公对于诗歌的热爱,一开始“苑香妮对诗歌的热爱有些模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写诗。可是如果不写下那些在她内心深处游弋的跳跃,似乎带着呼吸的词语,它们就会转化成种种愁绪,使她变得惆怅、低落、压抑或者岑寂。而她写出来的时候,她就会感觉舒朗、开阔和丰盈”。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她出发了。
有了开端,后面的路途仿佛自然生成,走到哪里,路途就延伸到哪里。然而“生命严格如阶梯”,俗世并不吝啬各种错乱,各种“不谐”,它们会接踵而来,让你应接不暇。随着时间的流转,主人公身边的诗友一个一个深陷俗世的泥淖中。在俗世的围场中,有猎取官位权势者,有仅为生计稻粱谋者,亦有以诗猎文名以为进阶之梯,用完即丢弃者。生命总是殊途同归,生命的火焰却可以轻易分出明与暗。主人公略显孤独,当然并不完全孤独。知音难觅,虽不多,但还有。诗歌本就不是一件热闹的事。
诗歌不是热闹的事,但不妨碍它在特定的时空热闹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而众多的诗社即是其表现之一。后来,诗社中的诗友各奔前程,则又让诗歌回归自身。
小说就是以主人公苑香妮参加诗社开场。细读其中诗作,都是诗人对诗的不离不弃和不断吸取养分的提升自我之后的心血之作。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诗人生命中各个段落,它们就是诗人一个个人生段落的标记。如果把主人公苑香妮写下的一首首诗作比作其生命中的欢乐与忧伤燃烧后的火焰,我们足以借助它们的光亮来照进诗人行走的路径,照见其中独特的景象。这些悲欣交集后升腾起的生命之火,汇集而成为诗人的“独一之诗”——温柔的火焰。
上面说的都是诗,仿佛忘了作品是小说,忘了它本质上的虚构其事。
作为一篇小说的作者,在以“诗”作为素材时在取舍上则需要再谨慎克制些。“对症下药”并且把控“剂量”才能真正使作为素材的“诗”(包括诗作、诗人、诗论)与小说的内部构造相得益彰。文中过多的引用一些诗论,不仅打乱了行文的节奏,也有堆砌之嫌。隐约间,作品中的叙事似乎只是为诗歌作注脚。小说字里行间充满诗意的言词,这当然有益于提升小说的诗意。但小说的诗意并不仅仅是行文中散发着诗意,就能成其为诗意小说,它更着重的应该是从文本里生长出来的诗意。另外小说中几乎没有留白,一件件一桩桩娓娓道来,这在让小说变得易读的同时也取消了读者想象力的参与。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小说诗意空间的建构。在叙事的策略和作品诗意空间建构上,作者的野心显得过于“温柔”,这把火不妨热烈些,需要作者更为用心的经营。诗歌和小说的左右互搏,作者在行文中诗歌的惯性过于强大,终局就是小说中尽管“满屏皆诗”却独缺诗意。
(《诗歌岁月》陶珊/著,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年9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