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年是中国新诗诞生一百周年,这个时间确定,是从1917年胡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开始发表新诗算起。因此,今年的上海书展,借机设立了首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同时就中国新诗百年举办了“世界诗歌论坛”。而此前,全国各地也已陆续举办过各种纪念新诗诞生百年的研讨会、论坛及诗歌活动。“百年新诗”无可争议地成为2016年最火的热词之一。

失望与希望
百年新诗,客观地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意见纷纭。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鲁迅就对当时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甚至有些尖锐地说:“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而鲁迅在留日时期写过《摩罗诗力说》,对诗曾寄予很高的期许:“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 甚至以写新诗而著名的流沙河,也认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实验。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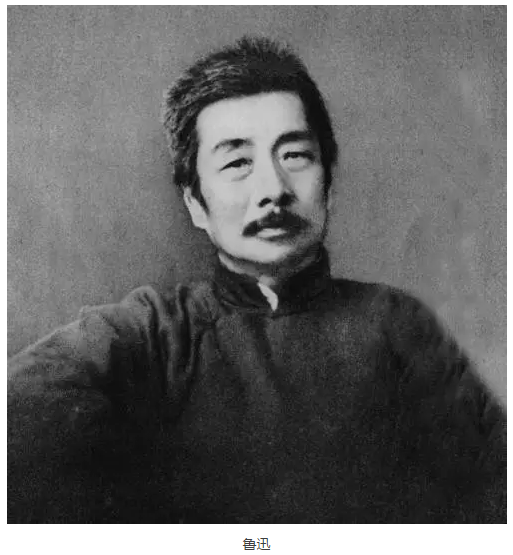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觉得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著名的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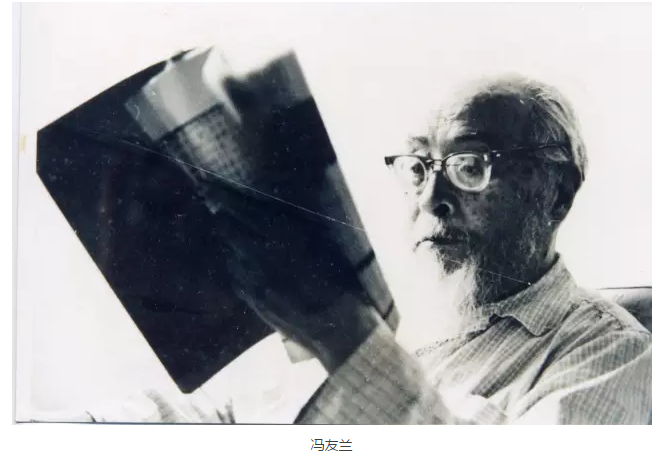
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谈起。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诗”是“言”的基础,就是说诗歌是中国文化一个基础。诗歌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儒家的经典中,《诗经》总是排在第一。可以说,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古代最基本的教育方式是“诗教”,《礼记》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次, “诗教”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教养和修养,孔子在《论语》里面经常夸一个人时就说:“可与言诗也”。最重要的,“诗教”还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林语堂曾说:“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他认为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钱穆等也有类似观点。
旧体诗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和核心,那么,对传统采取全盘激烈否定的态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要从新诗革命开始。新诗,充当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率先带头创作白话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倡导文学革命,声称要用“活文学”取代“死文学”。认为只有白话诗才是自由的,可以注入新内容、新思想、新精神,他声称:“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开始了以白话诗为主体的“诗体大解放”,打破格律等一切束缚,宣扬“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因此,新诗也被称为自由诗。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称欧洲之先进发达源于不断革命,“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固革命而新兴而进化。”

检讨与赞美
这些年,关于“五四”的争论也很多,正面的认为其代表时代进步思潮,值得肯定;负面的认为其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开了激进主义思潮,导致伦理丧失道德崩溃虚无主义泛滥,关于“五四”,学者张旭东的观点比较公允,他指出在“五四”之前,人们常常把中国经验等同于落后的经验,而将西方经验目之为进步的象征,由此就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立了一种对立关系,陷入了“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五四”将“中西对立”转换为“古今对立”,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困境,“五四”成为“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从此可以“既中国又现代”。既然古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诗歌,所以,五四新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新诗作为突破口是有道理的。
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表达过其相当深刻的理解。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

确实,在郭沫若、冰心、胡适、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此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诗艺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但后来这一方向遇到文革阻断。直到1970年代末,诗歌界才又重新开始新诗的现代探索之路。
我觉得,也许是新诗过于激烈的对抗性姿态让人们难以完全接受,也使自身的建设处于一个断崖式塌陷状态。新诗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底否定性的革命姿态,指责旧体诗是腐朽僵死的产物,主张通过新诗歌来新文化乃至新中国。但往往欲速则不达。而且,这种动辄断裂的行为自身面临挑战,郭沫若式的狂飙激进,北岛等人的对抗批判,一代又一代年轻诗人不时喊出“打倒”“pass”的口号,都使对立达到一个高潮。新诗百年,多情绪发泄与激进观念,少借鉴积累与文本创造;多宣言主张,少扎实建设。缺乏传承、融合的平和渐进演变,导致新诗的非正常跳跃式发展;低门槛无标准,导致创作者的混乱和接受者的抵触抗拒,因而也始终无法被人们广泛接受。相比旧体诗,新诗在语言和思想的大浩劫之后,也许还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自我修复愈合,回复平静,被人们逐渐认识和喜爱。
(李少君,曾任《天涯》杂志主编,现为《诗刊》副主编,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