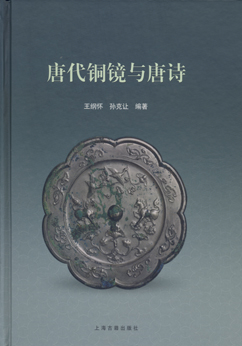 四十余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研习隋唐考古,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主要承担中国通史陈列——隋唐五代部分的内容设计。其间曾“通读”唐诗,摘抄与良手工业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诗句,如纺织、服饰、妆饰、金银器和铜镜等。事有凑巧,从大学毕业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领域。因此当看到《唐代铜镜与唐诗》书稿时,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敬而亲切的感觉,这不是涉及过,但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一个课题吗? 四十余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研习隋唐考古,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主要承担中国通史陈列——隋唐五代部分的内容设计。其间曾“通读”唐诗,摘抄与良手工业和社会生活有关的诗句,如纺织、服饰、妆饰、金银器和铜镜等。事有凑巧,从大学毕业直到今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领域。因此当看到《唐代铜镜与唐诗》书稿时,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崇敬而亲切的感觉,这不是涉及过,但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一个课题吗?回想自己从唐诗寻觅唐镜,当“读”诗仅成为一项工作时,其结果只能是无法回味;反过来,从唐镜中引申唐诗,当“写”镜变成为一个任务时,其结果也只能是缺少欣赏。没有欣赏、回味、没有激情、深情,是绝不可能做好这一课题的。因此,研究中国古代铜镜,特别是唐镜时,如何将科学性、知识性和艺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本书作者思路开阔,选题新颖。根据铜镜正面能映像,背面具纹饰、铭文的“两面”特点,巧以“赏镜读诗”、“吟诗识镜”两部分内容,将唐镜与唐诗融会在一起,“期盼通过唐镜来释读唐诗,试图借取唐诗来认识唐镜”,其定位是适当的。“将唐诗和唐镜这两种精品文化,加以联系结合,力求从‘边缘学科'这样一个角度,去探索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其想法是可取的。 本书引证资料丰富,架构合理。近几年,一些学者都在呼吁加强对“铜镜文化”的研究,提倡从中国美学史或中国艺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铜镜,这类注意相关领域学术发展方向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我必须严肃地指出,进行这类研究,如果不首先或不下功夫去了解铜镜的年代学、类型学和中国古代铜镜发展的历史及时代特点,不去作些最基础的资料工作,仅仅将一些不具典型性或代表性的铜镜作为载体,论述的范围虽广,提出的观点虽多,拟定的题目虽大,但缺少资料,缺少论据,最终只能停留大粗浅的层面上而难以深入。《唐代铜镜与唐诗》一书在与唐镜有关的唐诗资料和唐镜实物资料的收集、对比和研究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些资料不仅具有系统性,特别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经过作者的精心整理和排比,重点突出,分类合理,较深刻地挖掘出这些素材所包含的时代特点。这些资料将人们一般都知道的唐诗和人们一般并不熟悉的唐镜,通过了一次完美的结合,经历了一次审美的融汇。在我看来,这两者的结合、融汇,其实是通过唐诗来提升唐镜的历史学术地位,丰富唐镜的文化艺术内涵,关注唐镜的口味和情趣,进而提升人们对中国古代铜镜及铜镜文化的认识。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知识性、学术性较高的著作,也是一部趣味性较强的著作。 本书是唐镜专题研究的成功探索。近几年,我一直不同意一些人认为对铜镜本身的论述已经不少了的看法,强调对中国古代铜镜要进行深层次的探讨,不论是综合性的或是专题 性的,都需要深入,特别是后者。仅就战国镜、两汉镜和隋唐镜而言,它们被誉为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的三个重要标示,将三者的研究情况加以比较,不难发现,隋唐镜除个别类型如海兽葡萄镜的研究成果较多外,总的评价并不理想。究其原因,隋唐镜许多是花鸟、花卉纹题材,虽艺术性很强,然像汉镜那样,即有政治思想性的铭文内容,又有精美艺术性的纹饰图案,可供著书立说的范围广泛。因此如何进一步对隋唐镜加以研究,已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总量。本书既不是对唐镜的全面研究,也不是对唐镜的全面评述,只是在传统文化被 不断重构、整合的今天,从某一侧面将唐镜这个“物”与其相关联的唐诗这个“文”结合在一起,进行理性的判断和情感的发挥,从而体现了本书的价值,应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 孔祥星 2006年8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