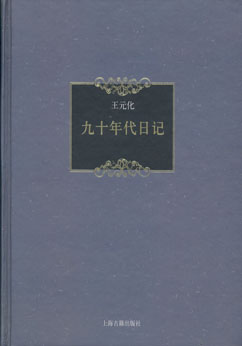 王元化先生(1920.11-2008.5)一生著述宏富,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均有专著和专论问世,建树颇多,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在他众多的著作中,他自己情有所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以修订出版一事嘱托的,却是一部既非专著又非专论汇编的《九十年代日记》。 王元化先生(1920.11-2008.5)一生著述宏富,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均有专著和专论问世,建树颇多,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在他众多的著作中,他自己情有所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以修订出版一事嘱托的,却是一部既非专著又非专论汇编的《九十年代日记》。元化先生早年投身革命运动,并开始其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生涯;建国后经历坎坷,曾因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牵连而遭隔离审查,“文革”期间也受迫害,平反后一度出任宣传部门的领导要职;晚年以教书著述为业,在文坛和学界有重要的影响。特殊的经历,使他在自己的一生中不断进行反思。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的思想真正进入了一个自由成熟的阶段,他也由一个成就卓著的学者进而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九十年代对他来说,是颇为重要的十年。 他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这也是他在这十年坚持记日记的原因。他认为:“倘要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和自己思想的演变全都记录下来,恐怕再没有比记日记更简便的方法了。”因此,元化先生非常重视这部日记,并将之出版。 为了出版这部日记,使之以“为自己的”转变为“给别人看的”,元化先生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或对某些个人隐私和目前为不宜公开的事件作了删削,或对原来没有记述下来的事件背景增补必要的说明,并特地写了“一九九一年回忆录”,以弥补因赴港、出国等导致的日记空白,于2001年7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元化先生还把日记中的一些内容或辑录,或抽出单独成文,编入他的《清园自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人物·书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书中。元化先生把这部日记视为他在九十年代重要论文结集的《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一书的姐妹篇,认为从这部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在这十年中的一些新的认识和思想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一步步形成的,发现它们的发展演变之迹。 元化先生的这部日记记录了他九十年代的学术活动,和那些重要论文如《“子见南子”与前人注疏》、《“达巷党人”与海外评注》、《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对“五四”的思考》、《关于京剧与文化传统答问》、《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等的写作经过。这段时间,元化先生读了大量的书籍,从先秦诸子到晚清陈澧、朱一新、崔东壁等的著作,从王国维、杜亚泉到“五四”人物的著作,以及熊十力、陈寅恪和当代学者的著作。他读书,不是泛泛而读,而是带着问题,反复研读。这段时间,元化先生还主编了《学术集林》文丛和丛书,主持了《古文字诂林》等著作的编纂,整理出版了自己的许多重要著作。他晚年还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多位如今在学术界卓有成就的学生,同时还参加了不少博士生论文的答辩。他对学生充满关切之情,日记中多有他与学生一起讨论、活动的记录。他审读论文相当认真。如他曾主持复旦大学朱学勤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朱的论文研究法国大革命,涉及了契约论问题,论证了为元化先生陌生的一些观点,与元化先生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既定看法发生了剧烈冲撞。元化先生为此认真研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卢梭的国家学说、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去寻找极左思潮的根源,纠正了原来对于激进主义思潮的看法。元化先生认为,他的反思虽然一进入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到了这时候才真正进入了角色。主持朱学勤的学位答辩这件事,是导致他在九十年代进行反思的重要诱因。他对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思考几乎贯穿了九十年代,直到1999年他以通信形式写了长篇论文《与友人谈社约论书》作为小结。他认为要认真对待杜亚泉等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并分析了五四时期流行的庸俗进化观点、激进主义、功利主义、意图伦理四种观点,认为激进主义是极左思潮的根源。这些观点相当深刻,是他九十年代反思的主要成果,也是他提倡“有思想的学术”的具体体现,在当代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元化先生为人正直,敢说真话,容易激动,情见乎辞,对人的好恶褒贬也见于日记。他对自己的师友充满敬重,日记中常常提到汪公岩夫子、熊十力、郭绍虞先生等前辈对他的影响。他与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和日本学者冈村繁等相互敬重,保持了终身的友谊,在日记中也有充分的表达。他对家庭的感情更为深厚,对家庭温情十分渴求,盼望过安静、和谐的生活。晚年夫人中风,唯一的儿子又不在身边。1995年春节,儿子未回来与二老团聚,又未及时来电,元化先生在除夕和初二的日记中一再表达思念、牵挂乃至担心之情,有“昨夜连得噩梦,不知是否心绪不宁所致”之语,直到初五接到子、媳自加拿大打来的电话,方才释然。元化先生和夫人张可的感情早为人所羡称。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