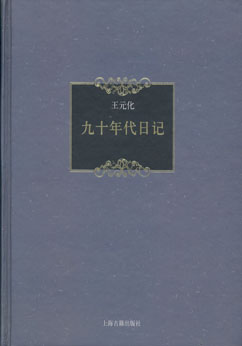 1990年王元化去参加某委员会的会议,工作人员拿出评博导的初审名单,王元化说名单或可再议一议,工作人员说不能动了。王元化不想当只画圈的工具,就说:“我们可有可无,那还不如根本撤销掉。”工作人员安排大家去跟领导合影,王元化明说不喜欢“排好了还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候好久”,就以腰病为由请假,引得大家也纷纷请假。1991年香港海关的女关员对他例行公事说:“你不可以在香港久住——”王元化听来十分无礼,便不客气地回敬她:“你怎么知道我不回去?我并不喜欢香港,没有事我是不会来的。”科塞(Lewis Coser,1913—)说过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理念人》)。那些年王元化七十多岁了,人书俱老,可是心却依然像孩童一般地按捺不住。 1990年王元化去参加某委员会的会议,工作人员拿出评博导的初审名单,王元化说名单或可再议一议,工作人员说不能动了。王元化不想当只画圈的工具,就说:“我们可有可无,那还不如根本撤销掉。”工作人员安排大家去跟领导合影,王元化明说不喜欢“排好了还要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候好久”,就以腰病为由请假,引得大家也纷纷请假。1991年香港海关的女关员对他例行公事说:“你不可以在香港久住——”王元化听来十分无礼,便不客气地回敬她:“你怎么知道我不回去?我并不喜欢香港,没有事我是不会来的。”科塞(Lewis Coser,1913—)说过知识分子“对于他们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经常详加审查”,“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理念人》)。那些年王元化七十多岁了,人书俱老,可是心却依然像孩童一般地按捺不住。这本《九十年代日记》,就好在真实记录了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面貌。随着“日记”的“镜头”,我们的眼光进入王元化老人的客厅、书房、一灯荧然的沉思之夜、座无虚席的演讲大厅、争执、辩论、夏威夷的夏夜、斯德哥尔摩的雪天、北京的王国维碑、台湾的胡适墓、万里晴云的南国乡间和荆州的古城,以及他的种种生气、不安。好像近些年还没有哪本出版物像这样细致切近地实录了一代思想人物的日常生活与晚年心境。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可贵的历史资料———首先是具有高浓度的知识社会学含量的资料,其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思想文化史的脚注/野史,以及今典和互文。 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不仅适合于书斋,而且适合于沙龙、咖啡馆的气氛。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却并不自命为“战士”、“精神界领袖”或先知。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份留恋。他们对文化、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也缺乏能力。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所以,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从他们的知识性格来说,他们往往做不来一些过于技术化的智力活动,也做不来一些太富于游戏意味的美学活动;对于前一项活动,他们觉得不够美,因而喜欢在一些较能显示出功夫、修养、趣味、风格、意境的人文活动(如京戏)中得到美感愉悦;对于后一项活动,他们又觉得不够真,这时他们显得过于执着、甚至钻牛角尖,然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不游戏,不苟且,才显出了这一类型的知识人的可敬亦复可爱。 谈到元化老人对自家生命的晚年反思,也恰是这部日记的当代思想史意义之所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被称为“反思的时代”,不仅仅是从情绪上,而且更是从理性、从历史纵观,对过去的东西的清理、重新认识与重新评估。王元化是这一思潮的开风气者。《日记》后记中说到:“九十年代是我的反思时代,直到这时我才对于自己长期积累的思想观念,作了比较彻底的全面检讨”,“所以我把九十年代视为自己思想开始成熟的时代”。字里行间,差不多看成是一种新生命的再生。王元化友人林同奇有一封信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心路,外国学界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轨迹,实际上是心路轨迹的某种投射,是一种生命形态,绝不同于‘职业思想家’的纯学术探索。”(《日记》第336页)这是知者之言。 依我个人之见,他的反思文字的思想史意义在于:首先,不以外来五光十色的思想学说为根据,不被西方思想家牵着走。其次,以“极左”为敌,不游戏、不回避、不滑头,活得真诚执着。第三,标举知识高贵、人文崇尚的传统,——这是尘埃落定之后,王元化终于觅得的一片归宿之地。记得托纳多雷(Giuseppe Tornatore)的电影《1900的传奇》(The legendof 1900)中,有一个在船上呆久了的人说:“上了岸小便都撒不准了!”王元化终于划开了一块文化、学统的蓝天白云的彼岸,在其中舒展自己的生命……想一想世纪老人给我们的这一份特具生命形态的反思财富,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