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宴》的开头,无力支付房租的顾葳葳向房东高伟同讨好地撒娇:“我命中老是爱上同性恋的美男子。”这大概也是我看到《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时内心最多的OS了。毕竟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每人的心中又都装着一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没看过原著,但相较其他的同志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算不上一段太挣扎的爱恋。没有五雷轰顶的父母和纠缠不休的前任,也不曾沿路遭遇冷漠眼光。24岁青年和17岁少年在意大利小镇的花果香中自然相爱,又自然别离,像是张国荣唱过的夏天:“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烧得肌肤如情痕极又痒,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柜里柜外,都是天堂。
在非异性恋的文学世界里,越是光明的指引,便越是特立独行。1952年,为了能顺利通过美国的书刊审查制度,玛丽珍·米克必须保证自己笔下的同志爱人得不到祝福。于是《Spring Fire》的最后,一方重新发现她的异性恋倾向被男人拯救,一方遭遇车祸神经损伤。
彼时,比她年长的帕特里夏·海史密斯是女同酒吧的集体偶像。虽然海史密斯已凭借《天才雷普利》获得过法国格兰匹治警察文学奖,但她们更乐意热烈讨论的是另一本:《盐的代价》,也就是《卡罗尔》,1952年首次出版,2015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卡罗尔》
连续好几个月的时间,海史密斯都会收到塞满读者反馈的大信封,重申着相同的珍视:“您的书是这种主题的作品里面,第一个有快乐结局的!我们这种人,并不是一定得自杀不可,我们有很多人都过得很好。”
他们是哪种人呢?同性恋酒吧是曼哈顿的某处暗门,警察会突击搜查,盘问男性化打扮的女性,同志被认为是精神病,坐地铁去得提前或滞后一站下车,以免被坐实身份。他们兴致勃勃寄给海史密斯的信,收件人处赫然标注的是“克莱尔·摩根”。这在当时没什么奇怪,没人甘愿被轻易看破。米克就有众多的笔名,她同时也是安·奥尔德里奇,《We Walk Alone》的作者,相信同性恋是种心理缺陷,并且精神分析学家可以治愈。
虽然海史密斯一度为《卡罗尔》的成功惴惴不安,小心翼翼撇清其间的关系,多少让这本书的先锋性打了折扣。但在“不敢有风,不敢有声,这爱情无人证”的处境中,卡罗尔的自主还是难以忽略地耀眼。
圣诞采购的人群里,中年主妇卡罗尔和售货小姐特芮丝不过彼此多看了一眼,便深深被对方吸引。卡罗尔正着手摆脱多年前因“大家都这样”才缔结的婚姻,特芮丝发现自己始终无法爱上现任男友。两人都渴望一个新的开始,对方又出现得刚刚好。她们在书信、电报中纸短情长,相约一起去西部旅行。
同时,她们被哈吉雇佣的私家侦探跟踪、窃听,哈吉是卡罗尔的丈夫,疯狂地希望妻子在离婚诉讼中一无所有。特芮丝的弯路走得少,她很早明确了自己的性取向,选择男友理查德是因为他把她“当做一个人来尊重”,遇到卡罗尔之前,她做的只是等待。卡罗尔则在踏过婚姻的泥沼后才开始觉醒,并绝不回头。
原著的最后一章,海史密斯没有详说卡罗尔如何在女儿的监护权上选择放手。大部分读者欣欣然大团圆的结局,赞赏她经历过艰难的日子,仍然保持了令人羡慕的理智。倒是电影为卡罗尔安排了向公众正名的出口。听证会上,卡罗尔出乎意料地主动让步,她努力使自己停止颤抖,起身准备离开:“要是以前,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只要能把琳蒂留在身边,哪怕是要与世隔绝。但是压抑我自己的天性,于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呢?”她缓缓穿上大衣,毫不畏惧地盯着哈吉:“我不会再让步了,没有还价的余地。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法庭见。一旦闹上法庭,只有撕破脸了。”她情绪崩落,转过脸去又回过来,带着克制的哭音:“而我们并不是丑陋的人啊!哈吉。”
这样的自白应该会符合海史密斯的心意。她曾提及小说名来源于《圣经》,又熟悉安德烈·纪德的作品,后者常以宗教和性为主题。人们在他的《伪钞制造者》中找到蛛丝马迹:“盐若失了味,如何才能再咸呢?——这是我忧心的悲剧。”
前任哈吉、理查德和追慕者丹尼分别代表了当时男人中的大多数和极少数。卡罗尔和特芮丝是前任们眼中迷途的羔羊,他们有权进行拯救和惩罚。“你也别以为我和理查德一样,我认为人们都自有其生活的方式。”丹尼爱着特芮丝,对她无法回应的理由也出奇平静,鼓励她直面内心的悸动。丹尼的选择,看不到强迫的异性恋,这或许也是读者们特别向往的一部分,但向往和乐观,是两码事。
从异性恋反思同性恋,是从弗吉利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开始的表达。昨日的克拉丽莎小姐,今日的达洛维夫人,在自己操办的聚会上与前任彼得·沃尔什相逢,汹涌的回忆带来愤怒和挫折。当年她不选择彼得,是因为无法交换金钱和地位;她也没和知心女友萨利走到一起,因为这种恋情是“违背自然的犯罪”,何况她们又都很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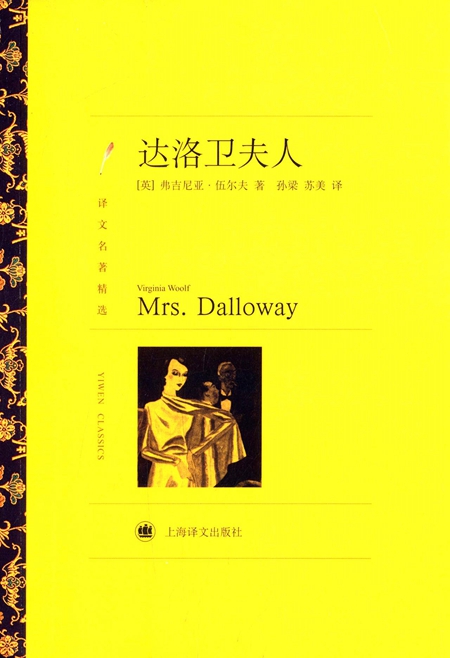
《达洛卫夫人》
她如愿以偿成了议员夫人,也过上了修女般的生活。一般来说,无论哪个时期的阔太,处境都差不多,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穿上‘雨衣肩胛’的春大衣,手挽玻璃皮包,粉白脂红地笑着,替丈夫吹嘘,替娘家撑场面,替不及格的小孩子遮盖”。唯一的区别在于,达洛维夫人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人得依靠婚姻谋生。天真烂漫的萨利不是也嫁了一个谢顶、愿意听她唠叨的有钱男人吗,生了五个儿子,衣食无忧。活得像橱窗又如何,阔太总要撑过去的,她们有这样的觉悟。
伊丽莎白是达洛维夫人无法省心的独女,倾心家庭女教师兼恋人基尔曼(Kilman)的独立和自强,她总想着“要有一个职业。她要成为一个农民,必要的话,也可能去当议员”。伍尔夫虽然这样写,却没预备让她成功。达洛维夫人的内心自然慌张,她能够理解但绝不支持,她能料想伊丽莎白的最好结局,便是点缀其他男人的生命。
虽然说真实世界中,付出了加倍的努力,思想里的桎梏只得到微小的改善也属正常。在当时的大多数人还对同性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圈子对此却进行着越来越广泛的讨论。西蒙娜·德·波伏娃直言应当“给予女人与男人一样的自由和相同的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金赛性学报告》首次用大量的访谈和图表,描摹了男性性行为与女性性行为的实况。总之,相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达洛维夫人,1952年的卡罗尔可以离婚,也可以养活自己。
那么,波伏娃距今都诞辰110周年了,那些曾在历史上被孤立过的爱情,真的有继续变好吗?以《达洛维夫人》为灵感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也许能回答这个问题。妮可·基德曼、朱丽安·摩尔和梅丽尔·斯特里普分别扮演不同时空的女人,她们因为《达洛维夫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时代在进步,也各有各的抗争。这些抗争,有些新一点,有些旧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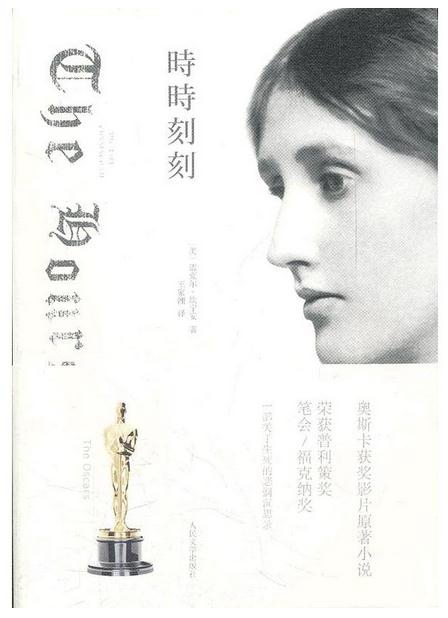
《时时刻刻》
不可否认的是,同性恋文化已经获得了公开表达的权利。仍以女同文学而言,人们比过去更加频繁地讨论到它。BBC一连对萨拉·沃特斯的两部小说《轻舔丝绒》和《指匠》做了忠诚的改编。她的作品洋溢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调,和哥特式的风采。烛照过往相同题材的小说就明了,萨拉笔下的主人公对性倾向相当自信,没人在自我认同上饱受折磨。

《轻舔丝绒》
萨拉追求盘根错节的情节感,例如《指匠》(又名《荆棘之城》)是一个相互欺骗,也互相深爱的故事。千金小姐莫德每天都得为舅舅的情色藏书制作目录,从未去过远方。苏有着精明的头脑,不过是伦敦街头的小扒手。而她俩逃离禁锢和贫穷的方式,竟要依靠把对方送进疯人院来实现。莫德和苏都以为只有自己是操盘手,这又得牵涉两人身世之谜了。故事的结尾当然是互相原谅,她们有房、有英镑,还继承了一大屋子的情色书。

《指匠》
还可以分享的番外是,《指匠》在被BBC改编为《指匠情挑》之后,还被韩国导演朴赞郁作为电影蓝本,拍摄成《小姐》,影射了韩国与日本的历史。《唐顿庄园》的大表姐曾在《指匠情挑》中贡献了疯人院女病人的角色。萨拉·沃特斯穿上了鲸鱼骨裙,客串了《南茜的情史》(《轻舔丝绒》的BBC版)中的路人甲。
珍妮特·温特森的作品也频频被改编为热门剧集,她像手上提着一只水果篮子,一会儿拿出一只橘子,一会儿扔出一个苹果,最后掏出一把樱桃。你不会知道篮子里还有多少水果。
她是对萨拉·沃特斯很有影响的作家,萨拉毫不讳言:“在同性恋写作方面,她是个很优秀的楷模。她不会装腔作势,只愿坦诚地书写她的想法。”她的半自传体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有种单从题名就可以领略到的坦诚,橘子不像母亲所言是唯一的水果,婚姻不是女人唯一的归宿,异性恋也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

《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
电影镜头可以丰满我们的想象,但原著中总有一些还要好看的文字,你能感受到历史、悬疑,还有爱。优雅的卡罗尔,枯萎的达洛维夫人,深不可测的莫德……你发现无论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都和她们的性取向无关。她们的喜怒哀乐,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让蔡康永泪崩的那集《奇葩说》,讨论了非异性恋该不该向父母坦白的主题,姜思达说:“平等永远不是当我说我出柜的时候,你们在那里为我摇旗呐喊,反而是因为你们在摇旗呐喊的过程中,把这种不平等显得格外昭彰。”
连岳曾公开一封读者的来信:“我选择大条条地告诉别人我喜欢他,我选择放弃我认为是屁事的其他事情和情人约会,我选择出柜,我选择让周围的朋友知道我是同志,我选择一个人千里迢迢来美国泡洋帅哥。每一次都是我自己的选择。但困扰我的是,我选择这么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生活,但怎么还是孤零零一个人。”
去年的5月24日,台湾宣布成为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区。社会条件总有一天会具备,问题是非异性恋的权利不但要赢在制度上,还要赢在人心里。而这个热闹的尘世向来都是,在互相理解疼痛之后才变得更好。
传说,遥远的山里有一个黝黑的山洞,人们以为太阳要过很久才能照到它。事实却是,阳光照亮它,只要一瞬间。如果上面那些书曾经照亮过你,不妨再把自己当做太阳,照亮别人,也只需要一瞬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