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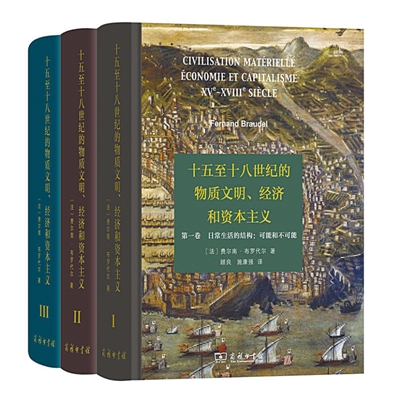
日前,商务印书馆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物质文明》)十套样书送到我家。书籍的封面、版式、插图等设计极其精美,令人爱不释手。编辑希望我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大家译书的经过及其中的艰辛。盛情难却,我想,不妨讲述一下自己成为布罗代尔中文译者的前因后果。
我退休前在中央编译局,本职工作是把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及两会文件翻译成法文,按说很难与外国史学名家发生任何交集。然而,太多的机缘巧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
事情要从1978年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待法国的一个学者代表团,邀我充当陪同翻译。以布罗代尔为首的年鉴派史学是法国学界的骄傲,代表团自然津津乐道地详加介绍。在他们所做的学术报告里,我第一次听到布罗代尔的大名,并得知“文明史”“长时段”“跨学科研究”等新概念。为了把报告中那些陌生的东西翻译清楚,我不得不请报告人在每场报告前专门为我开点小灶。这点“特殊待遇”,让我打开了新视野。但在当时,这些知识与我的本职工作毕竟相距甚远,我并没有作进一步探究的意图和动力。
出人意料的是,代表团副团长雅克·勒高夫对我产生了兴趣,主动邀请我去由他担任院长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作访问学者。就这样,经编译局同意,我于1982年11月至1983年7月在巴黎进修了9个月。
法方的邀请意图与我的个人愿望有一定的错位。他们可能希望我在高等研究院能与法国学者有更多交流,加深对年鉴派史学的了解。而我当时却一心想提高法语写作能力,以期回国后做好本职工作。
此外,赴法前我已出版了两本译著:布朗基的《祖国在危急中》和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有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资料、研究动态自然也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因此,9个月中,我对年鉴派史学只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认真攻读过的两本书至今记忆犹新:勒高夫的《新史学》和孚雷的《史学作坊》。两位作者都是布罗代尔最具影响力的门生,我有幸受到他们的多次宴请。然而说来惭愧,布罗代尔本人的大作,我一本也没有读过。
与布罗代尔唯一的一次见面,要归功于《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地区》(以下简称《地中海》)的译者唐家龙先生。一天在巴黎街头偶遇,他正寻找门路,想向作者当面请教几个问题。我便利用自己访问学者的身份,预约了与布罗代尔的会见。可是,我为老唐作了引见后便匆匆告别,并没有参与谈话。领略大师风采的一次极好机会不经意间被我错过,今天回想起来,真是追悔莫及。
与布罗代尔真正结缘,要等到他去世之后的1986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决定出版《物质文明》中译本,邀约施康强和我承担翻译工作。我们感到相当突然,甚至有点胆怯,因为早听说过布罗代尔作品的广征博引和艰涩难懂,深怕三大本巨著落在我们手里成了烫手山芋。可是,在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的巧言游说下,又禁不住书中精美插图的诱惑,我们居然皱着眉头领受了任务。
而法国人文科学之家为促进其创始人布罗代尔的著作在国外传播,可谓不遗余力。这家学术基金会特拨经费,邀请施康强、我和夫人张慧君在巴黎逗留半年,以便我们能就近查阅资料和答疑解惑。基金会主任给我们签发了通用借书证,可以在巴黎所有图书馆和博物馆畅行无阻。
布罗代尔的夫人保尔·布罗代尔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她的帮助也最直接、最宝贵。她把丈夫生前的工作室腾出来,供我和张慧君居住。除了耐心解答问题外,还经常讲些她先生学术生涯中的趣闻逸事。更加难得的是,我可以随时查阅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公学讲课的教案。为了讲课需要,他在教案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正式出版物中让人费解的语句和段落讲得一清二楚。
通过翻译布罗代尔著作的磨练,我的中译法水平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在1990年把《物质文明》译稿交齐后,我没有停下脚步。1991年,应商务印书馆邀请为《地中海》第一卷译稿作通读校订;1992—1994年,与张泽乾合作翻译《法兰西的特性》1—3卷;1995—1996年,和张慧君一起编译史学文集《资本主义论丛》。
就这样,十年时间里,我把这位史学大师的主要著作几乎摸了个遍,用布罗代尔夫人的话来说,我可以“当之无愧”地自称是“布罗代尔的中文译者”。这十年的日日夜夜是我翻译人生中最辛苦、最充实和最富成果的金色岁月。今天回顾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看到布罗代尔的著作因获得中国读者的欢迎而再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