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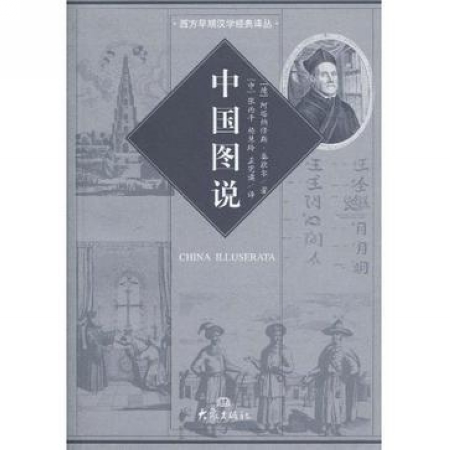
《中国图说》
[德]阿塔纳修斯·基歇尔著
张西平 杨慧玲 孟宪谟译
大象出版社
2010年3月第一版
526页,39.00元
阅读《中国图说》的体验,似乎帮助我印证了长久以来存于心中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时间的流逝和文明的隔阂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它们都拉开了我们和我们所要认识事物之间的距离。跟随基歇尔笔下那些耶稣会士的记述,中文读者仿佛也踏上了向着东方远征的旅程,搜罗奇闻异事,找寻奇兽珍禽,探索未知的异文明,尽管我们还需要不断地清醒,那个“异文明”正是几百年前的自己。
当然,如果去掉诗意的想象而回到最实然的学术立场,这种“距离”并不难理解,因为我们通过基歇尔所掌握的,不是中国本身,而是由文字和图像组合起来的一种“形象”。阅读基歇尔的书让我想到的,是顾彬教授曾用过的一本书名——“你的眼中的我的形象”(Mein Bild in deinem Auge)。当然,不仅在德国,就在中文学界,尤其在比较文学领域,形象学研究也早不是新鲜事物,甚至毋宁说已经熟透。“形象”一词并不是稀奇少见,而是已被用得太多,以至于其自身涵义也变得模糊难解。或许,“形象”中蕴藏的漂浮暧昧的成分,能让我们免于本质主义的滞重。人们总是好奇,借助别人的眼,看到的是另一个不同的自己。

中国的诸神
无论如何,初版于1667年的《中国图说》对研究近代早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而言,其意义确实不容低估。自十六世纪耶稣会士东来,乍然面对中国这样一个陌生而庞大的文明,燃发写作欲望并最终成书的不在少数,其中更有利玛窦和卫匡国这样心思细密记忆力超群的人物。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国新图》抑或《大中国志》,其影响都不及从未踏足中国的集大成者基歇尔编写的《中国图说》。后者汇集了早期耶稣会士的著述见闻,因其叙事之生动、绘图之精美而更具通俗性,从而跨出教会领域,成为《马可波罗行纪》之后又一塑造西方人中国认知的代表著作。
基歇尔是耶稣会士,也是近代博物学家的先驱,但与游历四方的后辈不同,他坐在欧洲的书斋里,频繁地和传教士、旅行家们见面通信,了解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并将它们编纂成书。由此,他也容易犯书斋人物常见的问题,因为缺乏亲身之经验,他只好选择依赖其信息来源,在《中国图说》里,某些时候他显然过于信任了他的耶稣会士同行们。从辽东的“凤凰”到南海的“鲲鹏”(基氏称作“黄色的鱼”,夏季为鸟冬季变鱼),这些本是传教士记录中国的固有传说,而非亲眼见证。另有一些怪诞事物,更没法确证其有无,此等却都被基歇尔当作实存事物一一记入书中。基氏此举,固然是为了满足当时欧洲读者对瑰异东方的猎奇心理,但也源于耶稣会士旺盛的“博物求知”欲望。盖世间万事万物,皆出于天主之伟大创造,对常人而言匪夷所思之处,亦为天主之绝妙手笔,一待闻见,自是虔敬多于怀疑。
形象在主体之间迁移,诞生出“陌生之自我”,但形象本身仍有真实性,它反映的是形象创造者的理解方式。从另一角度看,甚至形象的真实才是唯一的真实,因为“自我”本身的真实更难捉摸。如果按照拉康式的对自我主体的消解,那么“中国”只是一个符号,它充当了一条纽带,联系起今天的我和几百年前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的人们,它平等地对待每一个观察者。无论是十七世纪饱含传教热情的耶稣会士,还是十九世纪带着现代文明优越感的英国外交官,甚至是二十一世纪深入乡村的本土社会学家,都在重复一个恒久的疑问——如何理解中国?然而,这个疑问更精确的表述方式或许是,如何使“中国”变得可以理解?如何将散乱而纷繁的经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形式化,使其聚拢到“中国”这个符号之下?这样,这个问题便可以更多地避开本质性的方法论追问,而以历史性的方式展现自身。
即缘于此,任何“形象”的产生,都离不开创造者的自身经验。基歇尔和耶稣会士们也不例外。阅读《中国图说》,除了那些对物质世界的描述之外,读者还能清楚地发现一条精神传播的轨迹,而中国则处于其末端。在基歇尔的眼中,中国的文字来源于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人的诸神是对古希腊诸神的模仿,观音菩萨是埃及伊西斯(Isis)神的变体,而佛家的轮回转世说则来自毕达哥拉斯。整部《图说》里所描绘的中国,其文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埃及、希腊等中近东文明的延伸。这种在今天可能会反激出许多民族主义情绪的判断,却反映了基歇尔在写作《图说》时的既有经验,或者说“理解前结构”。基歇尔一生撰写了四十多部著作,其观察对象远不止中国一个,对埃及文字和文明则尤为熟悉。这赋予他极为广博的知识,并采用简单的类比手段,调动研究其他文明的经验来理解中国。

1667年版《中国图说》封面:利玛窦与汤若望
张西平先生在2003年的论文里,曾谈到过耶稣会士“中国形象”塑造中的“社会集体想象”,这种想象由两个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一是以自我的观念去塑造异国,二是强调其相异性而作“乌托邦”的想象。表面看来,基歇尔描绘的中国强大而富足,物产丰饶,社会秩序井然,很具“乌托邦”的色彩,但是,基歇尔做这种描述,并不意在批判和逃离现居的天主教世界。和后来的启蒙哲人比如伏尔泰不同,基歇尔对他笔下这个看似美好的东方帝国,并没有流露出多少憧憬和向往。相应的,他在书的第一部分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长篇抄录和梳解,倒鲜明地体现了他对基督宗教在中国传教的看重。
有趣的是,基歇尔撰写《中国图说》,正当清初“中国礼仪之争”愈演愈烈之时,但基歇尔的书中对这场风波的核心问题——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和“天主”的译名问题,却很少谈及。不仅如此,基歇尔对整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基督教以外的部分)都着墨不多,仅是出于对偶像崇拜的批判,泛泛地谈了“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对孔子和孔学更是一笔带过,其中还包含了许多肤浅的误解。这种情况的产生,显然不能归因于他信息来源的缺乏,因为他接触到的那些耶稣会士们都曾写有许多文字来对此进行解释,可以想象,如果他愿意了解,将会获得充足的资料。但是,他没有这么做,而且他对中国宗教和偶像崇拜的意见,仍然停留在一个相当保守的立场之上。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里曾经评论道,《图说》中列出的许多材料,应该不会让他所属的修会(耶稣会)满意,甚至可以认为能被他们在“礼仪之争”中的论敌拿来作为反对他们的论据。
为何如此?是因为基歇尔还不知道“礼仪之争”的重要性,还是因为他对这个论题缺乏兴趣而有意作出的选择,似乎后者可能性更大。今日看《中国图说》的读者,很难感觉不到该书写作中的这种选择性。基歇尔愿意花大量的篇幅描绘从欧洲到中国旅程上所见各色人物的穿戴打扮,甚至旁征博引各大洲所见的生物,只为了证明夏季为鸟冬季变鱼的“鲲鹏”之存在,与这种强烈的对“物”的好奇心相比,他对基督教中国传教的最大障碍——本土既有的精神世界却兴趣寥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耶稣会士博物学家特殊的眼光。
或许我们应承认,基歇尔对世界的认知,仍然离不开“基督教世界”和“异教世界”的二元分化观念,而中国只是这个“异教世界”中离欧洲较远的一个部分,正像《中国图说》只是基歇尔众多博物著作中的一本而已。他在《图说》中,将中国文明的诸多要素都溯源到古代埃及和希腊,除了显示其对近东文明的熟悉之外,更表现出将整个异教世界作同质化理解的倾向。然而,正如李天纲先生曾提到的,相比于十九世纪传教士,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士有着更强的“普世主义”的包容,基歇尔以如此饱满的笔墨尽情描绘一个美好的异教国度,表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普世情怀,多少也传递给了他的读者。
按照艾田蒲所说,基歇尔的著作并没有直接催生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著作,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绘画和引起人们对中国的兴趣上。而这两点都离不开《中国图说》中附有的大量插图。无论出于卜弥格、白乃心(Jean Grueber)或者其他人之手,他们都以比我们想象当中更重要的方式参与到了近代西方人“中国形象”的构建之中。
在十八世纪末英国使团访问清廷之前,很少有著作像《中国图说》这样,提供了数量如此巨大的关于中国的图像,为欧洲人认识中国提供最直观的材料。版画技术的发达,使得这些画在细节的表现上亦能完美。对于当时的洛可可艺术和英国庭院建筑等表现出的“东方迷情”,《图说》的贡献不可低估。张西平先生在“译后记”中说,他2006年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Herzog-August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中国图说》的1667年拉丁文版和1670年法文本,对其印制之精美叹为观止。我也去过该图书馆,有幸一观。可惜的是,今年出的中文译本,大概因为开本和印刷的关系,相比原本(甚至相比英译本)中的绘图,其精致程度要折损不少,不免遗憾。尽管如此,《中国图说》中译本的出版,能带动出更多对中西之间图像传播的研究,这是不难预期的。
责任编辑:宝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