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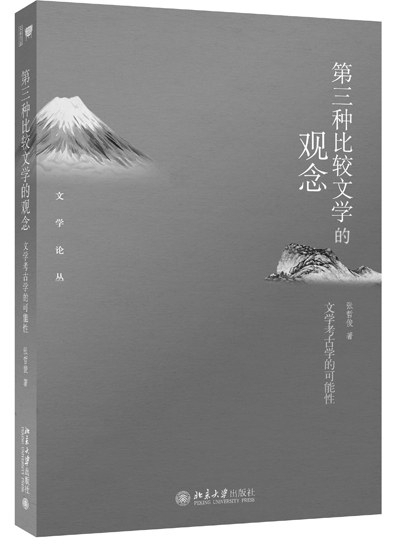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张哲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张哲俊教授宏论比较文学“第三关系”的著作《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终于问世,这对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是殊为可贺之事。当2011年《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一书出版的时候,书中间或提到的比较文学“第三关系”,已让学界同仁产生浓厚兴趣,都希望看到更加系统的阐述。时隔数年,比较文学“第三关系”论终于一览无遗。
仔细品味两本书的后记,还知道自《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至《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其中还有一段佳话。梁任公给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洋洋洒洒五万言。梁任公感慨说“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只能重做一篇序。那篇长长的序则单独出版,便是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张哲俊教授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杨柳的形象》正文六十余万字,原先的导论篇幅竟有二十余万字!当时他只好重做一篇导论。那篇长长的导论在续作充实以后,就是眼前这本将近四十万字的新著《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
张教授的研究兴趣是东亚文学,或谓东亚文学“圈”。东亚文学之为“圈”,严格说来是在一个往昔的时代。今天的东亚文学,情形已大不同。就算勉强地说成是一个“圈”,恐怕也只是一个松散的,没有圆心的圈。但在往昔,中国文学是“圈”的圆心,东亚邻国(如朝鲜、日本)是圆周。张教授论述比较文学“第三关系”,便是在东亚文学曾有过的“圈”的框架里来谈。书中所举,基本上都是中日古代文学方面的例证。或可选取书中提到的《都门柳色》——“五山”时期作家景徐周麟(1440-1519)的汉诗,以管窥比较文学“第三关系”论之一斑。
《都门柳色》一共三首,其一“绾柳河边惜别离,官桥烟瞑雨微时。一条界破都门色,勾引春愁上鬓丝”,其二“柳色青青绕禁城,都门细雨送君行。黄鹂在上解人意,唱起阳关第四声”,其三“柳色朝来带雨新,东人今日送西人。却将客舍青青地,变作故园桃李春”。“柳色青青”、“客舍青青”等,都鲜明地指向王维的《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对比较文学而言,《都门柳色》显然是一个相当标准的影响研究“素材”。诚然,给《都门柳色》造成影响的,到底是《渭城曲》本身,还是由《渭城曲》衍变而来的各种《阳关三叠》琴歌,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只是这并不影响“影响研究”本身,毋宁说是把影响研究推向深处。
张哲俊还在思考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都门柳色》的作者吟唱柳色,送别友人,究竟是都门处并没有柳色,不过是诗人凭着才情,摹仿《渭城曲》的情境,还是京都的都门真的有柳色,使景徐周麟联想到了《渭城曲》的送别情境,从而吟出这一组汉诗。经过仔细的研究,张哲俊指出日本京都确实有“都门柳”(且都门是城门而非宫门)。其他的五山诗僧,如义堂周信(1325-1388)、惟忠通恕(1349-1429)等,也写到过都门柳色。他甚至找到古地图,根据上杉本《洛中洛外图》的“粟田口”部分,指出了都门柳的位置。也就是说,景徐周麟的《都门柳色》像王维《渭城曲》一样,都是触景生情之作,依依惜别之情都凝结在青青柳色里。《渭城曲》之对《都门柳色》有影响,乃至《都门柳色》的形成,都结缘于这一点。通过对“影响”得以发生的契机进行还原,便把“影响研究”沿着这个方向推向深处。然而,张哲俊做这样一种还原的工作,其意并不在于影响研究,而在影响研究之外。
日本的都门柳承传自中国,中国的物质文化影响了日本,使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物质文化。中国的物质文化(就都门柳而言)赋予王维以灵感,使其创作出美妙的《渭城曲》。受中国影响而产生的类似的日本物质文化,赋予景徐周麟以灵感,使他想到《渭城曲》而创作出《都门柳色》。张哲俊很正确地指出,这里存在着两个值得注意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传输进来的物质使景徐周麟有了同样的灵感,第二个环节是景徐周麟想到了《渭城曲》。从影响研究的角度来看待、理解《都门柳色》,实际只捉住了其中的第二个环节。至于更加隐蔽,也更加重要的第一个环节,却被淡忘了。笼罩在第二个环节的光环下,第一个环节是幽暗的。然而幽暗的它,却是第二个环节的基础!没有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无从发生。比较文学“第三关系”论的敏锐之处,就在于紧捉住第一个环节,使其意义得获宣明。
完全有理由想到,第一个环节的产生,很有可能并不伴随着第二个环节,又或者就算伴随着第二个环节,却实在不能够对“影响”的源泉进行确认,而这意味着没有办法在影响研究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日本的关柳,也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关柳引发愁绪,在中国、在日本都经常发生。比如唐朝钱起(722-780)《送杨著作归东海》写道,“杨柳出关色,东行千里期。酒酣暂轻别,路远始相思。欲识离心尽,斜阳到海时”。平安朝藤原冬嗣(775-826)《故关柳》写道,“故关柝罢人烟稀,古堞荒凉余杨柳。春到尚开旧时色,看过行客几回久”。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表明,钱起又或者其它中国诗人的关柳诗,对藤原冬嗣的关柳诗造成影响。这里能够确认的,只有第一个环节。我们所看到的,只能是传输进来的物质造就了同样的灵感。
关于那并不伴随着第二个环节的第一个环节,更具体地说,关于传输进来的物质造就同样的灵感,现有的比较文学研究并未论及。多少与之较为接近的,恐怕要属类型学研究,尤其是历史类型学比较研究。比较文学的“类型”,是指“时空不一的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类似”。日尔蒙斯基所说的历史类型学研究,更加强调历史进程中的相似社会文化因素对相似文学现象之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似文学现象的出现,影响的因素有时候也是在起作用的。日尔蒙斯基敏锐地指出,影响的因素之所以起作用,影响的因素之所以成其为一种“外部的推动力”,也是由于那相似的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在起作用。更何况,相似文学现象的出现,很多时候影响的因素并没有在起作用,又或者很难确切地说清楚影响的因素怎样在起着作用。然而,日尔蒙斯基所关注的是“相似的社会文化造就同样的灵感”——哪怕有可能是“相似的物质文化造就同样的灵感”,却并非“传输进来的物质造就同样的灵感”。
类型学研究,甚或历史类型学比较研究,如果可以抽象地说(脱开“平行研究”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状况,脱开“历史类型学”、甚至“历史诗学”概念产生的具体历史状况),其实是一种更加高级的平行研究。原来所说的平行研究,是指把那些相似、类似,具有可比性,但相互间没有直接关系、并不存在事实联系,从属于两个不同民族(国家、语言)的作家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其同异,并导出有益的结论。平行研究的前提,是“尚未发现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平行研究所关注的只是“同样的灵感”,远非“传输进来的物质造就同样的灵感”。以钱起、藤原冬嗣为例,他们的关柳诗确实属于“尚未发现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事实联系的情况。但他们的关柳诗并非完全没有联系,关柳诗所依托的“关柳”之为物质现实,明显是一种从中国移植到日本的事物。径直采取平行研究,总有一种未尽之感,没有完全切中对象。
换而言之,比较文学领域内便有一种关系,介乎平行关系与影响关系之间。输入进来的物质,激发起相近的文学情感。这种相近性,其之为关系,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平行关系,并不完全是平行不相交,也非严格意义上的影响关系,影响、(更确切地说)传输进来的物质在这里只是中介。这种相近性所体现的关系,便是张哲俊所说的比较文学“第三关系”。这显然是比较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发现,作者是从平行关系、影响关系的缝隙里找见“第三关系”的。
传输进来的物质,时常也是特定的观念知识的载体。特定的观念知识,随物质一同输入。柳树在中国古代文学、日本古代文学里,原先都是生命信仰的载体,佑护生命与健康,能够驱鬼镇邪,可以说是一个例证。在日本后来的江户文学里,柳树不再是神力之树,而是妖力之木,成其为妖怪幽灵的象征。但这种变异,是有踪迹可寻的。日本的墓树风俗输自中国,且多以垂柳为墓树。既与墓地为邻,垂柳便逐渐成了妖怪幽灵出入的见证。
更进一步地,甚至传输进来的纯粹观念知识,也同样可以成为“第三关系”的基础。张哲俊指出,日本原先并没有虎,虎的形象却鲜活地存在于日本古人的观念里,也出现在日本古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文化当中,许多与虎有关的内容,大至文化思想,小至成语俗谚,传播到了日本。柿本人麻吕(660-720)的和歌,“跃身骑猛虎,飞越过旧宅。青渊战鲛龙,唯愿大刀在”,描写英雄骑虎战鲛龙。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龙虎斗则是很常见的观念。柿本人麻吕的想象,必然是以辗转自中国传输而来的“龙虎斗”观念为基础。
不难看出,“第三关系”的内容是相当广阔的,可以是物质,可以是物质所承载的观念知识,也可以是无需物质为载体的观念知识。《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一书都作了详细论述,而其中最为张哲俊关注的,恐怕还是要数物质的输入所带动的那种“第三关系”,他在这方面也有相当深厚的研究心得。
中日两国自古至今都在玩一种类似于“飞行棋”的游戏,扔出骰子,根据点数把棋往前挪步,挪到指定的位置上,根据位置的特定属性有时候还可以向前飞行数步,甚至直达终点,有时候则会后退数步。中国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类游戏是彩选、升官图、选佛图等,日本古代则是绘双六。日本学者增川宏一认为,中日两国这类游戏相互间没有影响和交流关系。张哲俊基于比较文学“第三关系”的立场和动因,则很自然地持谨慎的保留态度。
日本学者之所以认定没有影响和交流关系,最重要的文献证据是日本江户初期(17世纪)文献就提到了绘双六的最早形式“佛法双六”,而中国明代后期的文献里才有《选佛图》。但张哲俊通过翔实的材料指出,中国至晚在宋代就已有《选佛图》。北宋元丰进士黄裳(1044-1130)写过一篇《选佛图序》,这很清楚地表明当时已经有了《选佛图》。该文又清楚地提到了“世之为《选官图》者,使人有名利之意,为《选仙图》者,使人有生生之意”,足可知《选佛图》之前中国已有《选官图》《选仙图》。与此同时,《选佛图》之以《选官图》又或者《选仙图》为基础,也并非没有可能。佛法双六的图纸上每一步都是佛教世界观里的神鬼之位,选佛图大抵相近。有鉴于中国的《选佛图》时间远早于佛法双六,则在中日交流的总体背景下,在中国文化和思想东传的总体背景下,有理由假设佛法双六是《选佛图》在日本的“受容”或曰“变异”。佛法双六带给日本普通百姓的那份愉悦,与《选佛图》带给黄裳的“燕闲之中,资以为乐”之间的呼应,便是比较文学“第三关系”可以覆盖的内容。
还可再举一例,领略一下张哲俊对中日诗歌当中出现的佛寺松门所作的研讨。日本平安朝时期诗歌中经常出现佛寺松门,如藤原明衡《春日游云林院西洞》“松户荫花春雪〇,茶园藩柳暮烟回”,三宫《冬日游圆融寺》“松门故路半超谷,蓬鬓余生足望山”等。中国唐朝诗人如孟浩然、李白等,在诗歌里也明确地写到了佛寺松门,比如孟浩然《夜泊庐江闻故人在东林寺以诗寄之》起首两句“江路经庐阜,松门入虎溪”,李白《与从侄杭州刺史良游天竺寺》所写“天竺森在眼,松门飒惊秋”。如果这些诗里所写的佛寺松门,的确就是真切的佛寺门前的真切的松门,则可知日本的佛寺松门传自中国,这便又是一个典型的比较文学“第三关系”案例。
历史长河雍雍然流动,真切地存在过的事物并不都能留下踪迹。张哲俊教授探讨都门柳,的确找到了当时的地图,这就表明当时真切地有都门柳,诗中所写都门柳色并非诗人的诗性玄想。然而,云林院、圆融寺的松门,又或者庐山东林寺、杭州天竺寺的松门,则不能够同样幸运地找到地图又或者别的文献材料可以表明这些寺的门前真切地有松门。自此处前往比较文学“第三关系”,便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需要处理。确切地说,必须容设这些诗歌是“写实”的,如此方可说日本的确有佛寺松门且传自中国,而中国也的确有佛寺松门。
经历20世纪又或者21世纪各种文学理论思潮的冲刷,“写实”可以说既失去了地位,也失去了真切的内涵。只要是“写”——哪怕是“写实”,则难免都是“虚”写,带有主观灵动的底色。但张哲俊是从“写生”的意味上来理解写实的,他强调说中国古代诗歌(以及深受中国诗歌影响的日本诗歌)的基本传统就是如此意味的写实。在他看来,中国的“写实”的诗学传统与“六经皆史”的总体文化框架也是高度契合。六经皆史,诗亦是史。以“诗即史”为基点,他开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复古”之战。
现代文学的创作大概真的就像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所指导又或者总结的那样,多半都有主观创作的成份在其中,自虚构中挣脱现实并获得愉悦,然而古代文学的创作——如果仍然还需要使用“创作”这个词的话,则大相径庭。现代文学当然也有偏“非虚构”类的作品,古代文学也并非没有神游天外之作,但张哲俊所谈的主要是主宰现代与古代的诗学“基本精神”。而他之所以要“复古”,并非真的像这个词在贬义的意味上所表明的那样去“复古”,而是想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这些太久地浸润在现代文学理论的汪洋里的人,断不可一味地用现代文学理论套取古代文学作品——那将是一种本应该避免的“时代错误”的做法。面对古代文学作品,应该像尼采所说的那样,若要是真正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则应该“慢慢阅读”(《朝霞·前言》),仔细地体会古代文学作品自身的诗学“基本精神”。
回到现代文学,偏“非虚构”类的作品,又或者“虚构”类作品当中那些隐隐约约的写实的痕迹,我们同样也可以遵循“诗即史”的思路进行关注。郁达夫《毁家诗纪》所写的,固然是郁达夫所理解的家毁,但终究有家之被毁的真切的情形在其中。鲁迅的小说《长明灯》,也是以乡村里的长明灯为依托的。这种思路当然不是张哲俊的发明,然而他的创造性在于,重新申述“诗史”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并将之运用到比较文学研究当中,尤其是运用到比较文学“第三关系”的探讨里。
爬梳浩瀚的文献,务必要穷尽到真切事实之不能再穷尽处,才能做出一个又一个比较文学“第三关系”案例。这种“诗即史”的研究俨然是在比较文学的领域里从事考古的工作,张哲俊把“第三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称作“文学考古学”,可以说是一种相当中肯而精确的概括。这个提法有可能受到了福柯“知识考古学”概念的启发,但旨趣与之差别甚大。福柯所要探索的,是知识的控制问题,是权力对话语的组织问题。张哲俊所要确立的,则是比较文学领域的研究对象问题。在平行关系与影响关系之间,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个可以被作“第三关系”的领域。
概而言之,比较文学“第三关系”论可以说是比较文学领域的重要创新。它在平行关系与影响关系之间找到了一个乍看起来很不起眼,仔细品味却自有其奥秘的独特空间。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写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用这番话来说明张哲俊的比较文学“第三关系”研究,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从“第三关系”研究里总结出来的“文学考古学”方法论,基本上是从东亚文学圈里提炼出来的,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期盼并且乐见它将给别的文学“圈”的研究带来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