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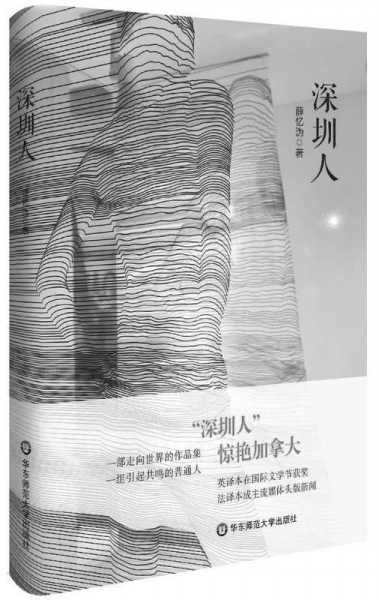
《深圳人》,薛忆沩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38.00元
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且获得跨国界的成功,除了叙述的精致和语言的精准等技术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立足于文学悲天悯人的本性,就是它“面对卑微的生命”。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这种“面对”的沉淀。
1977年,13岁的薛忆沩在自己就读的长沙市第21中学的门口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戴瓜皮帽的小贩。紧接着,那一伙差生羞辱小贩的细节更是震撼了薛忆沩敏感的内心,成为他将携带一生的创伤性记忆。33年后,已经移居蒙特利尔8年的薛忆沩完成了题为《小贩》的短篇小说。这篇幅很小而景深却很大的作品将整个“深圳人”系列小说发源的时间提前了整整20年。
2013年,名为《出租车司机》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在国内出版,并且立刻引起了读者和媒体的关注,入选当年的“中国影响力图书”。三年之后,由其中九篇作品构成的英译本以Shenzheners为名在加拿大出版,“隐藏在皇家山下的中国文学秘密”终于被当地的主流媒体发现,薛忆沩和他笔下的“深圳人”一起正式进入了异域的文学版图。2017年,也就是距离第一次遭遇“小贩”整整40年之后,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集改以《深圳人》为名重新出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
2002年初移居蒙特利尔的前夕,薛忆沩在深圳完成了他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访谈。访谈后来以《面对卑微的生命》为题在《深圳周刊》上发表。当时看来,这次访谈明显是受访者向“过去”的郑重告别,而现在看来,这次访谈却实际上是受访者对“未来”的积极示意。《面对卑微的生命》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题目,它对薛忆沩当时已经发表和随后将会完成的作品都做出了精准的概括。
由12篇短篇小说构成的《深圳人》就是一部“面对卑微的生命”的作品。跟随作者清澈又诗意的叙述,读者将会看到暗恋着陌生男人的“母亲”、挣扎在生活边缘的“小贩”、被诗意的学生激起爱欲的“物理老师”、因失去妻女而顿悟生活意义的“出租车司机”、由幻想走向幻灭的“女秘书”、从再现荒诞到经受荒诞的“剧作家”、被背叛摧残和摧毁的“两姐妹”、因孤独走近又因孤独分开的“同居者”、在生活的迷宫里不辩方向的“文盲”、被成人的世界吞噬的“神童”、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神魂颠倒的“村姑”以及被负疚感折磨终生的“父亲”……这一个个“卑微的生命”在经历了无法理喻的“失去”之后都选择了逃离:对现状的逃离,对浮躁的逃离,对虚无的逃离。他们的结局都好像是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生存状况的隐喻。在这个剧变的时代,“失去”是“卑微的生命”根本的处境,而“逃离”是“卑微的生命”勉强的抗争或者无奈的挣扎。
根据薛忆沩自己的介绍,“深圳人”系列小说中只有《出租车司机》一篇完成于深圳,其他的篇目则都完成于位于地球另一侧的蒙特利尔。但是,薛忆沩又反复强调,这个系列中的全部作品都根源于他本人九十年代的“深圳经验”。那显然是一种极具个性的特殊经验。它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并且获得跨国界的成功,除了叙述的精致和语言的精准等技术因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立足于文学悲天悯人的本性,就是它“面对卑微的生命”。小说集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是这种“面对”的沉淀,小说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这种“面对”的发现。走进“深圳人”系列小说,读者立刻会感受到这“面对”之中浓烈的哲学特质。这就是薛忆沩极具个性的深圳经验的特质。通过这种“面对”,悲天悯人的文学终于拨开了陈词滥调的迷雾,让“卑微的生命”诗意地显露,美学地定格:一座传奇的城市就这样升华成了一种文学的传奇。
现在,“深圳人”以《深圳人》的名义回到了深圳,回到了中国。或者借用薛忆沩自己新版序言的题目,“深圳人”现在以《深圳人》的名义回归了自己的“母语”。这不仅是薛忆沩本人奇特的文学道路的一次伸延,这也是为“深圳人”的母语读者奉献的一份盛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