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山花》在“小说苑”和“开端季”两个栏目,共发表小说共60余篇。从主题类型的角度来看,这些小说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小说、社会小说、心理小说、日常生活小说、女性小说、寓言性小说、哲理性小说、边地小说等。
当代史是当代小说的重要题材,很多重要的当代作家的成就都在历史小说上,如莫言、陈忠实、阎连科等。作家对历史题材的重视,在2016年度的《山花》中也有所体现。这些小说不管叙事载体如何,都是指向对当代历史的重新回顾和反思。禹风的《炮台少年》、莫子易的《浮图》、胡雪梅《天下第一香》、包倬的《风吹白云飘》、房伟的《小太君》、张学东的《黑的不是夜》、卢一萍的《牡丹灯记》、张锐强的《突厥蔷薇》、尹文武的《龙凤图》、郭雪波的《狗脖湾干校轶事》、房伟的《幽灵军》和《肃魂》、张 学东《星空》等,都是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总体来说,水平都比较高。语言和叙事功力深厚,有些作者还有意识地体现自己的历史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雪梅的《天下第一香》、房伟的《小太君》、卢一萍的《牡丹灯记》和郭雪波的《狗脖湾干校轶事》。胡雪梅《天下第一香》以朱家两百年老店聚仙大蒸一家三代人做长伙的遭遇作为叙事载体,写了从日本侵华到当下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小说结局出人意外,中国百年老店的手艺居然在中国失传,反而在日本流传了下来。房伟的《小太君》通过一个中国女孩和日本士兵的爱情来写一个反战的主题。卢一萍的《牡丹灯记》写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历史。小说采用的是一种侦探式的叙述模式,让人想起李洱的《花腔》。小说中的主人公村支书刘长腿在这类历史小说中也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总体来说,《牡丹灯记》是一篇有深厚叙事功力的小说,也有反思历史的精神。郭雪波《狗脖湾干校轶事》,选取历史细小的横断面,写出了特定历史时期大难时刻人性美好的一面。这是一种较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历史小说叙事之所以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成就,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兴盛分不开的。对于今天的作者来说,既有的成就既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也构成了一种影响的焦虑。单独来看某一篇小说,我们可能觉得非常精彩,叹为观止,但是放到文学史中去看,可能又觉得缺乏新意。这是当下作家不能不警惕的。
社会小说的主题是社会,社会是超越个体的共同体,社会小说就是呈现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历史小说主要回顾和反思历史,而社会小说则要面对当下。冯娜的《无数灯火选中的夜》、焦冲的《不存在的绑匪》、雷默《苍鹰》、李治邦的《听不到的钟声》、贺奕《卖狗肉的宠物店》、刘庆邦的《乌金肺》、赵瑜《薛木头先生诗歌赏析》、李清源《诗人之死》、孙一圣《花娘》、曹庆军《一桩时过境迁的强奸案》、起子《阳光照在我的眼皮上》、曹多勇的《大象》等,都是社会小说。 在社会历史小说当中,冯娜的《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和曹多勇的《大象》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冯娜的《无数灯火选中的夜》采用了明贬实褒的手法,通过新闻专业实习生何蔚洁的眼光,写出了那个在现实中落魄不堪的陆彦,恰恰是一个有担当的理想主义者。陆彦曾是南国电台前程无量的青年才俊,而她的沦落恰是因为在报道强拆事件中坚持新闻人的理想,不肯妥协。作者写出了新闻事业的艰辛,写出了新闻人在理想与现实的之间的两难。小说以实习生的现实功利观念反衬了落魄的陆彦作为一个新闻人的理想主义情怀。“无数灯火选中的夜”显然具有隐喻的意义,那个“无数灯火选中的夜”,就是像陆彦那样为了光明而牺牲自己的理想主义者。这篇小说写得非常精彩。曹多勇的《大象》,写出了作为长子的“凤凰男”对原生家庭的感情与无奈。小说有一种现实生活的物质性质感。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当然需要理解历史,但是我们也需要感受当下,面向当下的社会小说,给我们提供感受当下,把握当下的路径。我们期待更多具有穿透力的社会小说出现在《山花》上。
心理小说是对在特定处境中人的心理的表现。心理小说的叙述的重点,不在事件,而在于在这些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有具体性,这种心理感受有时候是有意识的,有时候是潜意识的,而更多的时候是潜意识的。走走的《久别》、刘鹏艳的《空房警报》、莉莉陈的《病理》、唐棣的《满洲里来的人》、王海雪《道具灯》、呈兮《飞蛾》、周恺《伪装》、徐畅的《静默如山》、温文锦的《蜻蜓之翼》、邵振国的《豌豆秧儿》、陶丽群的《水果早餐》、洪琛《有关储藏室及其它》、但及的《莲花》、国生的《声音》、尹北《心如破晓》、谢络绎的《耀眼的失明》、陈家桥的《脸》等,都是心理小说。这些心理小说基本都能抓住一种心理、一种情绪、或一种情感,进行表现。可以说,这些小说都体现了作者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卓越的叙述能力。读这样的小说,是对心灵的一种慰藉。写心理小说需要叙述者把握好叙述节奏,读心理小说需要读者耐得住性子。
在日常生活类小说中,日常生活成为了小说的重要主题,日常生活似乎成了一种人物的宿命。在日常生活小说类型中,主人公通常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个体。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平常,像一个无物之阵,人在其中做着困兽之斗。刘汀的《老灵魂》、陶丽群的《水果早餐》、杨凤喜《看社火》、张不退《情书》、李月峰《不过如此》、李黎《午夜的安东尼》、庞羽《我是梦露》、李美皆《我的异次元恋情》等,都是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在这些小说中日常生活主要是以“庸常”的面目出现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挣扎。在挣扎之后,有的碰壁了,如《水果早餐》、《老灵魂》;有的顺从了,如《看社火》;有的逃跑了,如《午夜的安东尼》;也有突围的,如《我是梦露》。日常生活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平民文学,活在生活中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生活,庸常的生活。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面对这种庸常的生活。这些小说,或引起我们的共鸣,或给我们以启示,让我们感到庸常生活中的我们原来并不孤独。
在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之间,有一类特殊的小说类型,那就是女性小说。在这一类型的小说中,作为性别的女性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它具有社会小说和心理小说的综合特征。曹寇的《恶臭》、刘鹏艳的《空房警报》、呈兮《飞蛾》、马拉的《小白情史》、赵卡《像峭壁露出的马脚》、邵振国的《豌豆秧儿》、孙一圣《花娘》、谢络绎的《耀眼的失明》、庞羽《我是梦露》、陈家桥的《脸》等,都是女性小说。女性有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也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处境。女性文学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内有它的特殊意义。文学对女性的态度,或者说,在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性别伦理,是考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2016年度《山花》的几篇女性小说,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与关爱。曹寇的《恶臭》和刘鹏艳的《空房警报》着眼于女性的生理,谢络绎的《耀眼的失明》着眼于女性怕暴露身体的心理,呈兮《飞蛾》和邵振国的《豌豆秧儿》着眼于女性的性心理,甚至是虐恋心理,马拉的《小白情史》和赵卡《像峭壁露出的马脚》着眼于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孙一圣《花娘》写了女性作为流通物的社会处境,庞羽《我是梦露》写了在看这个“看脸”的时代,“丑女”的处境。 在我看来这些女性小说都是非常出色的,尤其是女性作家的女性小说。
寓言性小说往往具有写实和写意两方面的特质,表面上是写具体的事件,实际上是另有所指。通常是以具体写抽象,以小写大。寓言的叙事逻辑与现实主义小说也有所不同,情节的发展往往超越现实性。蔡骏《与神同行的一夜》、申剑《乌木》、章元《他和他的》、曹永小说《花红寨》、杜国风的《无限公司》等,都是寓言小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申剑的《乌木》和曹永的《花红寨》。申剑的《乌木》写了财富对人性的影响。小说以一个金鱼杆杀人案来开头,整个小说就与这个金鱼杆杀人案的形成了互文。在叙事伦理上,《乌木》试图重新锻造社会的伦理关系,体现出很大的雄心。曹永小说《花红寨》也是写实与写意的融合,既是一个具体村寨的现实主义描写,又是一个关于普遍人性的寓言。而且在我看来,作为寓言的《花红寨》远比现实主义意义上的《花红寨》有价值。通过这样一个寓言,曹永试图挖掘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残暴与极权心理。
哲理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呈现出哲学层面的追求。杨映川的《此一时,彼一时》、段爱松的小说《青铜魇》、舒飞廉的《金神记》、夏榆的《彗星划过夜空》等,都是哲理小说。杨映川的《此一时,彼一时》表面上写的是一种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埋藏在人性中的对人自身可能性的一种实现冲动。夏榆的《彗星划过夜空》写了物质性对人的制约,偶然性对命运的影响,日常生活的烦扰,而这些都是人的存在所不能避免的。小说恰恰要写出这些存在对人的影响。在这篇小说中我看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子。段爱松的《青铜魇》和舒飞廉的《金神记》不仅在思想上具有哲学的层面的追求,在叙事上也别开生面,是具有实验价值的艺术形式。哲理性的小说,始终还是小说,它与纯理论哲学是有明确区别的。因此哲理小说的可读性,也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因素之一。
边地小说的主题是边地风情。边地风情是我们所生活的“此地”一面镜子。在边地风情中,我们有了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机会。曾哲的《不折不扣的阿瓦山歌·野青》、谢友鄞的《这里灵魂四处爬》等,是边地小说。曾哲的《不折不扣的阿瓦山歌·野青》写的是在边地淳朴的风情。阿瓦族少女野青对“我”的单纯的性渴望,让“我”这个来自都市文明的人显得有些虚伪。这篇小说实际上属于沈从文《边城》那一类,它是在批判现代文明。谢友鄞的《这里灵魂四处爬》是一篇地道的“边地”小说,小说粗粝而雄浑,给读者开启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物质生存和灵魂生存生命世界。
通观2016年《山花》刊出的这些小说,我们看到,这些作品都展现了深厚的语言和叙事功力,在题材、主题、叙事方法等各方面都覆盖比较广。在特定的每一期内,总是力求是各种题材、主题和艺术风格相互搭配。在小说作者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山花》的良苦用心。在这几十位作者当中,既有如刘庆邦这样的已经成名作家,也有一些知名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写作功力深厚,风格成熟的作家,也有一些正在走向成熟的70后作家,还有正在文坛崛起的80后作家,甚至还有一些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90后作家。《山花》专门的开设“开端季”栏目,给文学新人提供了舞台。作为贵州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山花》既要考虑它在全国的影响力,同时还要为促进贵州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做贡献。通过对2016年《山花》上小说作者居住区域的考察,我认为《山花》很好的处理了这个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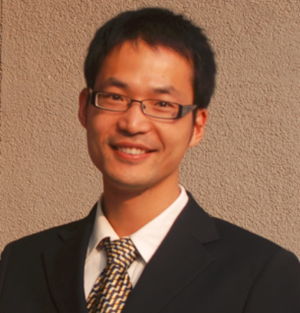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朱永富,男,1983年,山东日照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