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黎:《还魂记》的三重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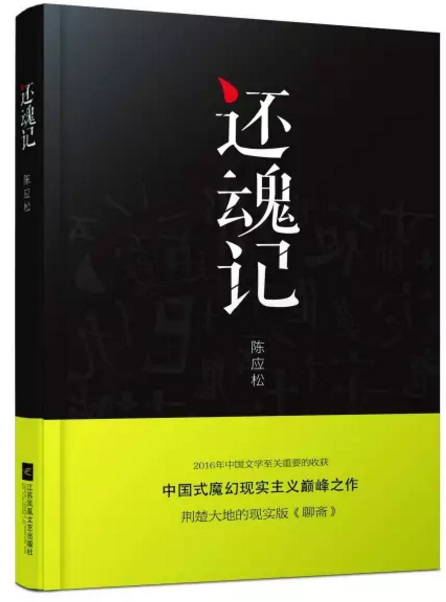
长篇小说的强音
在技术日新月异且产生出无穷尽的娱乐项目的年代,作家陈应松潜心写一部《还魂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这样的长篇小说是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揣测作者为何而写是失礼的行为,因为放弃的理由漫无边际而坚持的决心小而确定,正是类似这样的书写使文学和文字免于沦为一条条一段段。
读了《还魂记》之后,我感觉这是一部早已深藏于荆楚大地深处的小说,它沉默而顽固,作者凭借罕有的意志和长时间的辛劳将它从层层叠叠的现实与记忆之中挖掘出来。这是一部沾满了泥土、根茎、霉菌和骨骸的小说,作者刻意展现这一切,更为了将思辨和批判穿越现实的障碍,穿过曾经喧嚣的乡村生活而抵达每一个生灵的内心。
在作者创作这部无论内容还是形态都堪称厚重的小说时,周遭的现实世界始终在以一种亢奋的状态对应着思想家们的批判性,诸如娱乐至死,诸如单向度的人,诸如孤独的人群,诸如乌合之众……于是,长篇小说的写作自身已经具备了一种声响,在宣誓某种古老而新鲜的执念,有偏执的一面更有天真纯粹的一面。
还魂者的悲鸣
《还魂记》问世之后被称之为“奇书”,“全篇几乎以意象行文,想象奇诡,智性与野性居然相得益彰”(贾梦玮语),体现出作者对长篇小说的思考深入到哲学或诗歌层面,但作者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一个由天灾、人祸、冤案、打斗等不祥因素构成的村庄。如何将这个因为正在消失而显得异常有生机的村庄,以文字这种古老而时刻变动的形式呈现并使之重生,如何使村庄的声音嘹亮生动,如何使每一个因为被遗忘而显得漆黑的人物鲜活起来……这些都是难题。
作者选择了鬼魂的视角。一个亡魂回到“养生地”,目睹了活着的人、死去的人、过去的自己、过去的众人以及自己的归宿,目睹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诸多生灵之间以及人和这片土地之间难以割舍又极为残酷的关系。在鬼魂的视角下,太多的恶显现,温情与善良成了存在于远处而遥不可及的高峰。但鬼魂本身始终充满感情,他的名字叫作“燃灯”。
这种写作是放弃,放弃了通过对精彩情节阅读而产生的生理上的满足感和智力上的优越感的全部读者。这种写作又是超越,超越时空生死、语言自身的束缚、情节诸如圆满带来的伤害,超越了风情的做作、乡愁普遍存在的伪善、居高临下的蒙蔽。作者以一切被忽略的现实存在为描述对象,甚至为叙述手段,又将小说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彻底撕破。
乡土的沉默
时间久了,每个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等待终将不值一提,回乡、回归等也是如此,但初心难改。乡土可以接纳每一个人,它本身也如心脏一样时时跳动,即使风物不再,精神也依旧,可以安置神魂。人们对置身于乡土的渴望与动植物对山川原野的依赖一模一样。
《还魂记》不止于此,重返故里的亡魂看到的是正在消失的乡土,它不仅仅面向未来消失,更面向过去消失,以至于在不复存在之上又有了从未存在的悲怆。那么如何安置目睹这一切的灵魂,一个人的精神到底皈依何处?这个问题因为乡土的变迁消亡而陡然尖锐起来,甚至忽略了现实中的故土故园,成为一种天问。
这部小说反复追问着令人黯然神伤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安置沉重而卑贱的肉身,但是精神上到底归于何处?因为故土正在变为从未有过的存在,那么我们从何而来?对此《还魂记》疑似有所回答。作者寄身时空的穿越、艺术的想象和语言的鼎沸,企图像一位苍老的长者一样帮着掩饰乡土持续的抽泣。
(作者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编辑,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8月8日13版)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