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一位书写历史创伤的大师。在《浮世画家》、《上海孤儿》和《长日留痕》等小说中,他以精湛而巧妙的文学方式揭示社会历史进程对个体的冲击,表现人们的伤痕记忆和精神困境。作为一个幼年即移民到英国的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跨文化经历在他的书写中提供了特殊的文化身份和视角。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梅丽在近期出版的专著《危机时代的创伤叙事:石黑一雄作品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4月)中对相关问题做了详尽的研究,她在采访中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梅丽,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攻英美现当代文学批评,近年来专门从事石黑一雄作品研究。
澎湃新闻:此前有没有想到石黑一雄会获得诺贝尔奖?
梅丽:没有意外,觉得这是实至名归。石黑一雄在当代小说领域的影响力鲜有企及者,且近年来声誉日盛。有一个微妙的证据让我察觉到了这个趋势:近几年来,在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中,每年都有好几篇以石黑一雄为主题的。有一次我拿到7份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审稿时发现竟然有三篇都与石黑一雄有关。另外我的硕士学生当中,也有不少人撰写关于石黑一雄的文章,向各个杂志社投稿,他们会来跟我交流、征求修改意见。这说明研究他的人多、研究资料也多,不由得让我感慨他旺盛的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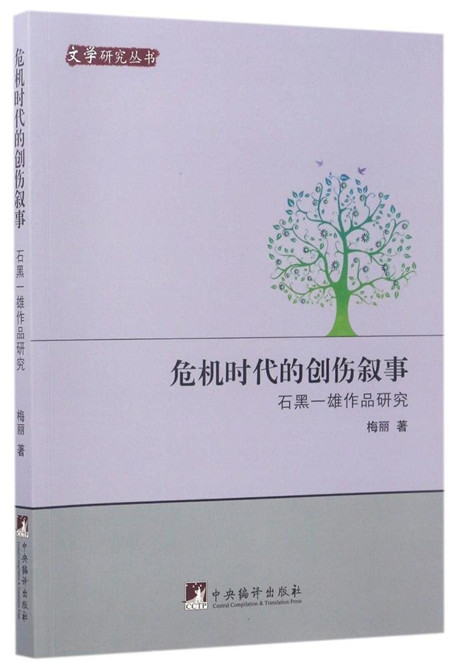
梅丽 著《危机时代的创伤叙事:石黑一雄作品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4月)
我觉得有三大原因促使他获奖。
第一,是他的作品具有比较宏大的历史和社会视野,符合诺贝尔文学奖的一贯评奖标准。
如果你研究一下历届诺奖作家的共同点,就会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非常关注历史和社会问题。例如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莱辛、奈保尔等——而另外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例如弗吉尼亚•伍尔芙、詹姆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卡尔维诺等,他们更多地关注个人意识和小说手法,但没有获奖。石黑一雄的作品主题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军国主义的反思、后殖民时代的帝国命运、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隔阂以及文化冲突等重大主题,因此他受诺奖青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是他倡导的“国际化写作”顺应了当前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趋势。
石黑一雄出生于日本,六岁随家人去到英国,移民的经历使他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开放的文化生存直觉,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先天的通约性语感。他认为作家应该容纳不同的文化背景,反映国际性主题,做“国际性的作家”。他指出作家不能制造文化藩篱和语言障碍,例如不能通过再现衣服的品牌或商品来表现人物性格,也不要使用某种特定语言中的双关语,因为这种信息只对少数人有价值,而且无法被顺利地翻译和传达到别的语言之中。由于他的小说遵循这样的“国际化写作”原则,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不会因为种族、国家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同时读者还会在他的引导和启发之下,对具有全球性的问题进行关注和反思,因而吸引了众多粉丝。
第三,是他不断突破文学类型的边界,具有十足的创新精神。
石黑一雄善于塑造人物的性格和语言,营造小说的场景和氛围,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他不因功自喜、安于小成,而是勇于创新,不断尝试新的体裁和主题。他早期的小说《远山淡影》和《浮世画家》以日本为背景,在英国文坛大获成功,被看成日本文化的代言人。可他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马上转向了英国,塑造了充满维多利亚气质的主人公。正当人们惊叹于他对英国社会风俗画般的细致描写时,他笔锋一转,开始创作具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无法安慰》。第五部小说《上海孤儿》则以探案为线索,将视野投向上海和英国的历史。第六部小说《别让我走》借助生物科技题材,构建了一个悬浮在历史时空中的反乌托邦空间。最新的一部《被埋葬的巨人》更是大胆地采用了奇幻小说的题材。石黑一雄曾说:“我感到文学类型的边界正在崩溃,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作者。”于是在这部新作中,亚瑟王、梅林、精灵和食人兽等纷纷登场,一个仿古的冒险故事被演绎成了一则深刻的现代政治寓言。石黑一雄不断挑战自我,对世界、对人性、对文学进行不懈探索,使得他的作品戛然自异,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这样一位有着独特的文化因子、强烈的写作使命、天才的写作灵感和勤奋的创作习惯的作家,他此次获奖,可谓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石黑一雄
澎湃新闻:您的论文和专著都频繁地提到石黑一雄的创伤叙事,为何选择这一主题?
梅丽:人类在近一百年里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危机。世界大战、种族冲突、宗教战争、恐怖袭击等等,让人们在遭遇创伤的同时,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慌。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危机时代的创伤, 成为具有紧迫性和普遍性的议题,这也是许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探讨的主题。
石黑一雄就是一位直面和书写历史创伤的大师,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大多被卷进战争、 灾难或政治事件中,体验着价值归属的焦虑,承受着迷失自我的风险。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满目疮痍的心灵图景: 尽管灾难都已经过去,但蒙蔽在历史尘埃之下的哀痛和错误,无法通过自欺欺人去抹除。石黑一雄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创伤,呈现了 20 世纪人类在战争、 殖民、极权和各种灾难之下普遍的伤痕记忆。
荒诞的时代、扭曲的人性、残酷的历史、飘摇的未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从1990年代开始,创伤理论作为当代重要的知识话语和公共政治话语,成为西方文论中的一枝新秀,得以蓬勃发展,它对创伤的现代性暴力进行强烈的批判和揭示,同时对创伤叙事进行全新的思考。利用西方创伤理论的前沿性成果来分析石黑一雄,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创作动机和写作特点,这也正是我开展关于他的研究课题的初衷。
举个例子来说,在创伤理论的视野中,人们不再仅仅依靠大屠杀中的证人证词,或者幸存者书写的回忆录,简单粗暴地给甲方或者乙方贴上罪恶的标签。因为根据新兴的创伤理论,创伤作为一种超越人类惯常经验的特殊事件,是否可以被充分言说,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创伤性的经历由谁来说,怎么说,是否具有可信度,都已经成为创伤叙事的考量因素。在石黑一雄的小说里,主人公们反复地走回记忆深处,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表述,到后头来连自己都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事实。在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巨大裂隙里,弥漫着价值失落的迷雾。
再举一例来说,创伤理论强调受害者主体的界定问题,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创伤事件的受害者?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决不能仅仅依据历史教科中的阵营划分,向施暴者吐唾沫,向受害者献花圈。因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往往被集体主义的强光所淹没, 当像《浮世画家》中的小野那样的施暴者们,在其个人生命被集体主义的使命所裹挟、威胁、剥夺,从而犯下愚蠢的罪行时,他们又何尝不是被时代巨轮碾压的受害者。在施暴与受害的轮番对峙中,隐藏着道德消长的潜流。
鉴于石黑一雄的作品主题和细节都相当贴近创伤叙事的研究范畴,可以说他的作品是理解创伤叙事的最佳文本,而创伤叙事理论,又为理解他的作品提供了恰当的分析范式。因此,从创伤叙事这一角度去挖掘他的作品深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
澎湃新闻:您觉得石黑一雄的叙事有什么样的特点?与他的成长经历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他对战争和历史创伤的态度是怎样的?
梅丽:石黑一雄的小说擅长于从创伤回忆的视角,重构在历史话语中“被忘却的记忆”。他认为“每段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总有黑暗的、不为人知的记忆,在当时被刻意隐瞒或埋藏,但何时回忆、是不是该回忆,这是重点所在。”他关注普通人在历史事件中所遭遇的痛苦, 通过个体的不可靠叙事来影射历史,检视历史发展与个人命运之间的矛盾。他的小说主人公们往往运用各种心理防御机制,去阻止痛苦记忆的再现, 或者去压抑难以直面的欲望, 从而减轻内心遭受的折磨。 石黑一雄的小说没有曲折多样的情节和细致入微的动作描写, 并不依赖戏剧化的高潮去推动故事发展, 而是追求一种节制的叙述表面之下的复杂心理与深沉情感。
这种写作方式,与他的移民经历有很大关系。石黑一雄在接受采访时坦言, 背井离乡的经历和被放逐感促使他走上写作的道路。 在儿时和爷爷分离、 遗忘母语、丧失本来的身份,以及在异乡被边缘化的痛苦经历, 促使他用创作来弥合自己心灵上的伤痛。此外,尽管石黑一雄深受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但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庶民剧也让他深受启发:那就要排除任何过于夸张的、戏剧性的东西, 保留下每日平凡的生活体验。石黑一雄并不希望通过绚丽的细节和夸张的情节去迎合观众的期待和减少文化上的生疏感。他要对人性展开最深入的洞察,他所希望的就是:故事不管发生在哪里,人都被看作是同样的人。
石黑一雄认为战争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 以至于个体无论生活在本国还是外国,都一样会感到不安。因此,他在创造小说角色时采用了多变的手法和分散的记忆视点, 让每个叙述者都逐渐融入所处的环境中,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汇处, 去思考个人在社会进程中的价值。
事实上,历史的创伤不会永远在场, 人们无法拥有了解历史真相的时空机器或者时空隧道, 因而任何的历史书写都只能是对历史事件的想象性增补和替换,甚至是僭越和篡改。文本所展现的史实,对于今人而言, 其意义远不如缺席的那一部分。石黑一雄正是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对人们所遭受的创伤历史不断地进行着增补,在小说所呈现的留白、压抑与矛盾的裂缝里,无限地趋向对历史和人类情感的真实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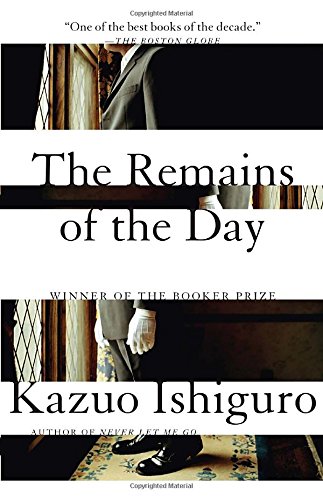
澎湃新闻:能否就《浮世画家》(1986)、《上海孤儿》(2000)和《长日留痕》这几部代表作具体谈谈石黑一雄的叙事?
梅丽:我选择比较突出的两点来谈。
第一,是他作品中的叙事空间具有多元性。
石黑一雄本人十分抵触评论家们将他和拉什迪和奈保尔等后殖民作家归为一类。与那些作家提出意识形态上的诉求以及质疑英国中心地位的立场不一样的是,石黑一雄对帝国主义并未采取一种直接对抗的态度。 在英国和日本之间,石黑一雄站在“第三者”的位置上,从而中立地看待日本和英国这对 “二战” 中的竞争对手,客观地观察它们如何应对传统价值观的急剧腐蚀以及战后美国不断崛起的霸权地位。
《浮世画家》 中的小野,因在“二战”期间对日本军国主义效力,在战后陷入无法摆脱的耻辱;而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日新月异和美国文化无处不在的影响,又使他对战前日本徒增怀念。
《长日留痕》 则是从一名年迈的英国管家的视角来描写大英帝国的衰亡, 展现了达林顿宅邸的所有权从英国贵族转移到美国商人手中的过程, 其暗喻的色彩十分明显。 主人公史蒂文斯一方面沉湎于对达林顿府的辉煌往昔的回忆,一方面又极力迎合美国主人的品味。
而将背景设置于英国和中国两地的 《上海孤儿》 展现的是 “二战”前后英、 中两国的政治和商业纠葛。英国探员克里斯多夫•班克斯在支离破碎的回忆中意识到, 曾经品质高尚的塞西尔先生和菲利浦叔叔在他们的政治抱负和宗教因素的双重捆绑之下,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石黑一雄的小说展现了复杂的文化斡旋,它们既不以帝国主义本身为核心, 也并未谴责任何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 他关注的重点是普通平民在战争浩劫中承受的痛苦。 他的小说都从个体视角出发,在那些令人不安且充满失落和遗憾的回忆中, 展现战争重塑个人生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过程。
第二点,是无国界的国际化写作风格。
有人曾问石黑一雄,你是日本作家还是英国作家。他回答说,我是国际作家。他致力创作国际化小说,使其“包含世界上各种不同古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 展现国际读者所真正关心的问题。
石黑一雄在作品中刻意模糊了移民的主题,不像其他移民作家那样习惯在作品中前置自传性的细节,也不像他们那样利用他们自身或父母在异乡遭遇的价值观崩溃等作为主题。石黑一雄的独特之处,是展现了更加多元的文化反思,将自己的移民经历和思乡之情与角色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身份各异的叙述者。
在早期的《浮世画家》中, 石黑一雄只是将日本作为展现战争对社会造成破坏的一个历史背景,一个只有最低限度地域特征的隐喻性的日本,并且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地名的精确表述, 无论在哪里, 都只是简单地称之为 “那座城市”。《长日留痕》《无法慰藉》 和《上海孤儿》的背景分别设置于英国、 欧洲、中国/ 英国。这表明除了他家乡原子弹爆炸事件,石黑一雄也关注其他国家和社会的战后调整。他探讨了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并创造了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各种角色。

澎湃新闻:石黑一雄最近的一部作品《被埋葬的巨人》(2015)出版以后引起一些争议,不少人评价为是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您怎么看?
梅丽:石黑一雄曾提到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14世纪传奇诗歌《高文骑士与绿衣骑士》,同时与12世纪编年史家杰弗里撰写的《不列颠诸王史》等亚瑟王传奇构成互文。这部小说以戏仿手法颠覆了英国文学经典作品中的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固有形象,暗含着历史真相的悬置和对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权威历史话语的解构。
由于小说涉及对英国古典文学的多重互文,对现实世界的多重隐喻,以及多声部的复调叙事,对读者的知识预设较高,阅读难度较大。也许这部小说身上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和政治信息,例如对英国文明源头的追溯和对英国民族身份的重构,对东欧的民族冲突和卢旺达大屠杀的影射,对历史、集体记忆和创伤之间的关系的探讨,都是极其宏大的主题,而石黑一雄力图拓展写作类型和推进写作技巧的野心也使得小说叙事稍显堆砌,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阅读的魅力,成为了“观念”的容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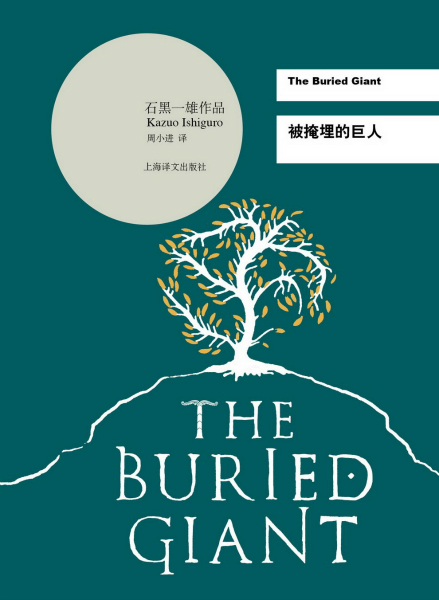
澎湃新闻:能否谈谈石黑一雄小说与音乐的关系?
梅丽:石黑一雄是一位在音乐与文学之间搭建桥梁的实践者。他从小热爱音乐,喜欢弹奏乐器,在大学毕业时的理想是当一位音乐家。他在小说中塑造了诸多音乐家形象,在多部作品中均有大量音乐方面的描写,小说结构也暗合某些音乐作品的形式和强烈的音乐元素,大大扩展了小说在主题、结构和象征方面的内涵。
音乐与小说的融合,是现代小说的形式得以革新、艺术性得以拓展的一种重要的催化剂。石黑一雄小说中的“音乐化”书写,使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去洞见他笔下所呈现的生存的压力、文化的冲突、价值的失落和心灵的困境。对于读者来说,当小说中音乐的意象和音乐的指涉被捕捉和理解之际,正是文本的另一扇窗户被打开之时,由此所能窥见的风景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澎湃新闻: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以后,可以想见会有更多读者对石黑一雄产生兴趣。您会着力推荐他的哪一部作品吗?
梅丽: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部是《长日留痕》,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经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