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以“科幻文学”为主题,两位台湾新生代作家代表——高翊峰与伊格言格外受到人们关注,他们都曾被《联合文学》评选为“20位40岁以下最受期待华文小说家”,此次分别以科幻小说《幻舱》、《噬梦人》亮相2017上海书展。
在上海书展期间,高翊峰与伊格言就他们的小说与对科幻文学的思考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人会失去“爱人的能力”
《幻舱》是一个有关封闭空间的故事。主人公达利被秘密送入一处封闭的下水道临时避难所,此地衣食无缺,唯独没有时间和阳光,可躲在这里的人“安于现状,不愿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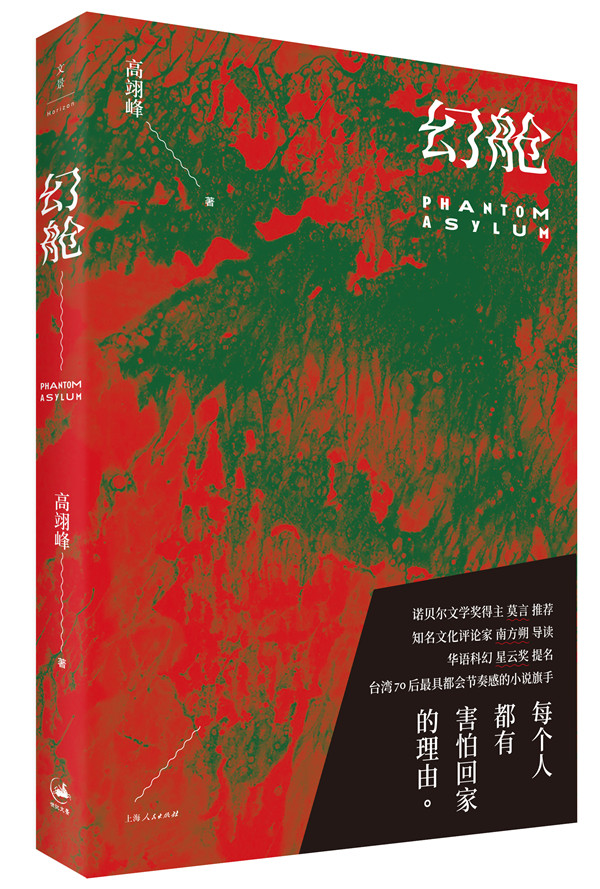
高翊峰著《幻舱》
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源于高翊峰对城市生活的观察:住在1层和住在40层的人,每天看这个世界的视野都不一样,日积月累后就会出现“视差”。住在40层的人更多看到的是缩小比例的城市“有多快”,而住在1层的人更“接地气”,更靠近普罗大众。
“在这样的‘视差’背后,城市人出现了很大的价值观差异,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twist——扭曲。扭曲之后,人会在城市生活中丧失大量与天俱来的爱的能力。”高翊峰举例,“比如,在十字路口遇到一个哭泣的孤儿,会有多少人为他驻足,会有多少人主动上前关心他,又会有多少人愿意领养他?”
“再比如,若今天的上海是一个封闭空间,不是你不能走出上海,而是你心里不敢、不愿离开,这就是《幻舱》中除了达利以外所有人的心态。上海有车,有房,有工作,有美食,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可当你们的心灵状态因不愿离开而被它困住的那一刻,它就开始扭曲你了。”

高翊峰。摄影 张超焱
其实早在2007年,高翊峰就有了这部小说的源头想法,那一年是他写作的第一个十年。他原本打算写三个中篇故事,但因为工作关系迁至北京,事务牵绊之下一直没能好好写故事。
从2008年到2010年,高翊峰只能零零杂杂地做些记录。“刚到北京时儿子才三岁,我、太太和他就住在一个一厅一室的小空间里。那时候认识的人不多,我还带着一个孩子,孩子就是我心灵上的‘幻舱’,我不敢走远,不敢跑远。那样的心理牵挂让我困在了小小的密闭空间。”
“这样的感受直接投射到了《幻舱》里。所以在写《幻舱》时,我也一直在和自己对话。”高翊峰坦言,“所谓密闭空间,小到一个人的心灵状态,大到一个城市,其实都有羁绊的地方。透过这个羁绊,我一直问自己,在这么剧烈、复杂的生活中,我究竟失去了什么。我发现我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儿子。我意识到人爱人的能力会消失的,甚至父亲会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幻舱》想表达的核心。”
一开始高翊峰并没有赋予《幻舱》科幻小说的想象。“其实真正在决定小说题材、素材的时候,我不会特别去分科不科幻,有没有用到科学知识。”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现在我会开始想象这样的科幻写作之于我未来写作的意义。”
高翊峰目前正在创作从《幻舱》出发的第二个故事。据说小说是这样开头的:“达利,以后你就继续用这个名字在这个城市活下去吧。”
“人是什么”这样的极端问题
和《幻舱》相比,《噬梦人》更有科幻作品的味道。“它还是我的书第一次在大陆出版。”伊格言笑称,这是一个讲述生化人匿藏于人类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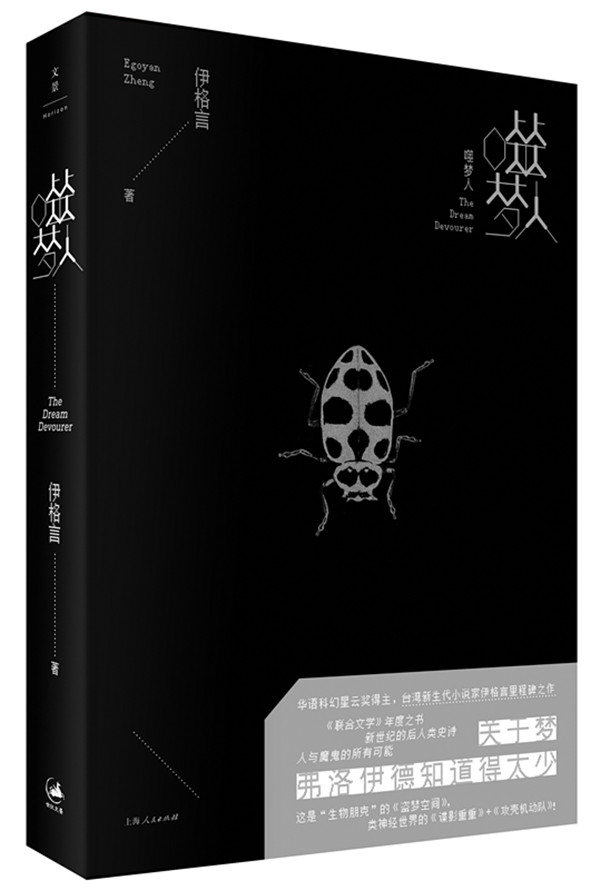
伊格言著《噬梦人》
在这个故事里,人的梦境可被粹取,再通过豢养水瓢虫保鲜梦境。人类研发“梦境分析”筛检法,希望借此准确标识出那些伪扮为人类的生化人。国家情报总署技术标准局局长、生化人K匿藏于人群中,却始终不确知自己真正的来处,终于一道“内部清查”的命令启动了K的逃亡之旅。
这部在2010年被《联合文学》评为“年度之书”的长篇小说共33万字,前后花了伊格言约三年的时间。“其实有没有‘科幻’这个前缀不是很重要,但科幻作为一种题材有这个题材的优势。我喜欢科幻是因为科幻最极端。在科幻里,只要你的设定好,你就可以把人的记忆换掉。如果不是科幻,在一般写实文里,你能把人的记忆换掉吗?原则上不行,但你还可以用隐喻的办法。又比如我们常看的韩剧、婆妈剧,主角被车子撞到失去记忆,也可以换掉了,但很大费周章。”
“应该说,我天生就对极端的问题——人的组成部分中究竟灵魂的部分占多少、肉体的部分占多少、灵魂和肉体是可以二分的吗、人是什么等等很感兴趣。《噬梦人》主要聚焦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
在伊格言看来,梦是最幽深神秘的领域——有朝一日,当梦用以监视、用以控制、用以镇压、用以殖民。当这些技术与人对自我或他人的改造产生连结时——在某些时刻,人自我凌迟。在另一些时刻,外在环境则凌迟个人。
也有人说,《噬梦人》缜密的逻辑堪比一部推理小说。其实为了构思和写作,伊格言前后做了8万字的笔记,他有点嘚瑟地说:“都可以单独出版一本书了。”
而之所以会写这么多笔记,是因为这个构架的故事体量庞大,稍不注意,便会“前后矛盾”。伊格言还专门制作了一份小说“年表”,也因此长了很多白头发。

伊格言。摄影 小路
比如,有个科技在年表中是2150年完成。但小说写到后段,写到2140年某事件时,却可能会不小心写成“该科技已经完成”。“要花时间去一一核对,避免发生这样的错误。”
“我往后的创作,就长篇而言可能就有两条线,一条是《噬梦人》系列,一条是关注社会议题的。《噬梦人》是一部科幻小说,但我在创作时不会刻意去想科幻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就是想把作品写好。”伊格言如是说。
迥异于本格派科幻文学的作品
近年来,中国科幻作品《三体》等连续获得国际奖项或被提名,华语原创科幻文学作品日渐受到人们追捧与关注。高翊峰称,来到上海后,他能感受到沪上文坛对科幻文学的讨论热情。“台北好像没有那么热烈,这或许是两地对于类型小说的差异。”
“现在兴起了‘科幻文学热’,我想或许可以把科幻文学粗糙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本格派的,会用许多大家易懂的科学知识所展开的科幻小说,读起来畅快、舒服、过瘾,读者还能通过一部小说理解了什么叫重力空间;另外一种是他(作者)把科幻当做创作题材,但其实还是想解决人的问题。这类作品或许是非常迥异于本格派科幻文学的作品。”
高翊峰直言,他对第二类科幻作品充满期待。“因为这一块作品其实还没有大爆发。这次的《幻舱》和《噬梦人》,刚好是我觉得台湾过去五年来,从严肃文学出发,但却以实验、科技、人工智能为素材的代表作品。台湾文坛并没有特别对《幻舱》《噬梦人》这类作品进行系统性的讨论。其实在本格派科幻之外,还有一群过去尝试纯文学写作的人用别样的视角接近科幻文学。”
“就如高翊峰所言,我们都是纯文学出身,在我看来科幻比较接近于一种题材。”伊格言说,如果是有艺术价值的科幻,它的未来应该是指向现在和过去的未来,不单纯是未来本身。
“比如最近流行的《人类简史》,尤瓦尔•赫拉利提到截至目前影响人类最大的三个制度——货币、国家和宗教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们可以对人类这个物种巨观的演化进行推测:未来宗教或许会被科学取代,国家也会被货币慢慢弱化,最后最强大的会是货币。”
在伊格言看来,如果再从“谁掌握了过去就掌握了现在,谁掌握了现在就掌握了未来”这个出发,继续预测人类的文明走向,科幻就会变成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