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书之美》 韦力/安妮宝贝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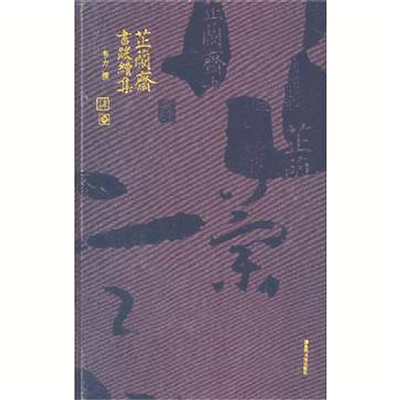
《芷兰斋书跋续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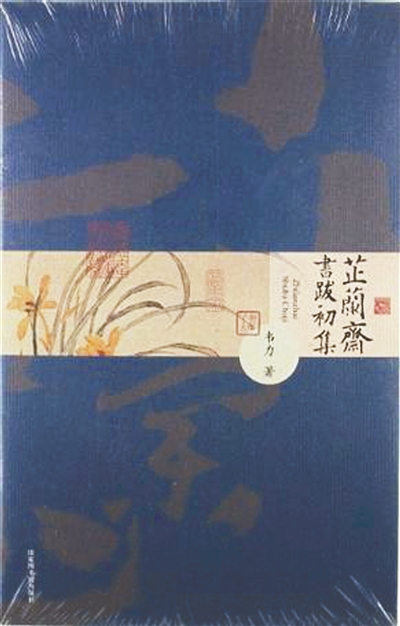
《芷兰斋书跋初集》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5月

《中国古籍拍卖述评》 紫禁城出版社 2011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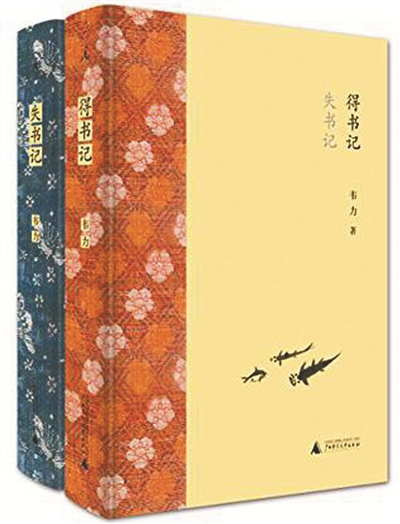
《失书记·得书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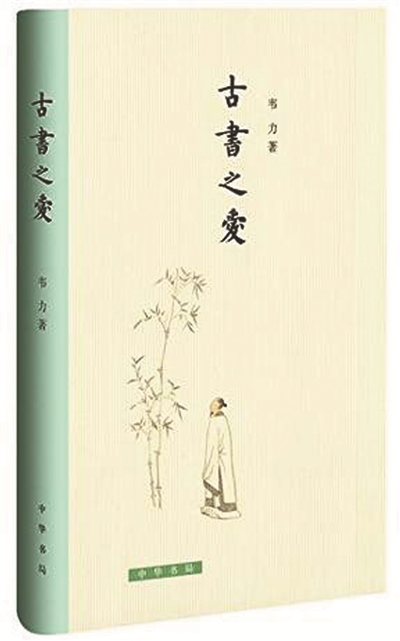
《古书之爱》 中华书局 2016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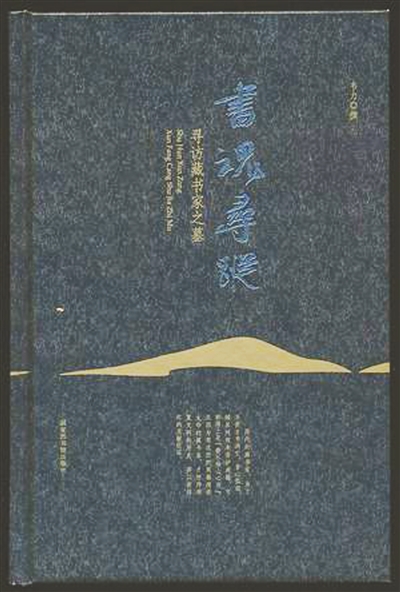
《书魂寻踪:寻访藏书家之墓》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6年7月

《觅宗记:佛教八宗一派遗迹寻访》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11月

《书楼觅踪》 中信出版社 2017年3月

《上书房行走》 海豚出版社 2017年7月

每次韦力出现,身边都会聚拢一批书友,问的问题大都是“您能传授一些拍书秘笈吗?”“为什么您总能买到好书,都是怎么发现的?”“××书究竟值不值得收?”拥有30多年古籍收藏经验的韦力,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古旧书市,乃至第一场古籍拍卖,见证了古籍在市场的流通。而在他进入拍卖行的20多年来,与韦力同场“搏杀”的大买家已经消失了五拨,只有韦力还像一只“不死鸟”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古籍的保存和传播。
谈拍卖
“从排斥愤恨到欲罢不能”
晶报:我们都知道,您早年收的很多书都是在各地古籍书店买到的,但是这些年,越来越难在书店买到上好的古籍善本了,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韦力:最早,古籍的流通除了私人之间的买卖,主要还是依靠古籍书店。在1956年到1957年间,全国开始搞公私合营。这个时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城市只能保留一家古籍书店,所以就把其它的古籍书店合并为一家。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古籍书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滞销,甚至有些私人的古籍藏书因为历史的原因也归入到各大书店,造成各大书店的巨大古籍库存。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中国书店向文化部申请销售古籍,得到批准后,在北京的海王村举办了全国第一届古旧书市。古籍被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往书市,整整运了十几车,其场面极其壮观。当时不论厚薄,每本5毛钱,第二年涨到一块,后来价格越来越高,一直举办到30届就停办了。此外,中国书店下属有多家分支的古籍书店,每年中国书店都会从库存中选取一些古籍给下属的书店以供应市场。于是古籍书店就成了人们得书的主要渠道。
后来古籍拍卖出现了,打破了这种局面。当时拍卖行也是从各大古籍书店征集一些好的古籍,然后标上高价进行拍卖。那时候进预展场还需要购票进入,就像参观博物馆一样,古籍书被放置在透明的玻璃橱窗里,也不能翻看。我当时看到标价上好几个零,专门把服务员叫来问这些零中间是不是忘记点小数点了,服务员还白了我一眼说就是这样。我顿时对古籍拍卖产生了一种厌恶和愤恨,扭头就走了。
晶报:时过境迁,您现在可是多家拍卖行的顾问了。
韦力:我对拍卖怀有一种复杂的情感,从最初的排斥愤恨到后来慢慢接受,最后竟演变成了一种欲罢不能的依赖。人都有思维定式,藏书也是如此。人们总会习惯于做某些事情。拍卖对中国来说是稀缺事物,因为中国从1993年才开始有,而在西方,比如索斯比、佳士得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拍卖古籍了,可见这之间的差异悬殊之大。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一个人接受拍卖其实很难。
晶报:那您最后是如何接受的?
韦力:当年中国第一个搞古籍拍卖的嘉德,不知出于何种策略,把拍价坐地提升十倍。可是即便这样的高价,这些古籍书也竟然成功拍卖。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致。很多参与竞拍的人并不像我一样对古籍书店熟络,无法了解到其它的得书渠道。不管价格标得有多高,只要有人买,就有市场。随着古籍拍卖的发展,书店里的古籍书价也随之飙升。于是,大量的古籍被送到了拍卖行,爱书之人也被迫到拍卖场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书。这就是吸金效应,把卖家和买家都吸引到这里来。
真正进入到该行业以后,发现也不是如最初那样的可恨。拍卖行有他的技巧,从以低价吸引买家开始,我就发现,拍卖时大家都在抢几种有名的书,却把次要的、没有研究透的古籍忽略掉,于是,到卖主那里可能3万才能买,但是在拍卖会1.5万就拍回来了。这让我突然意识到拍卖会是一个捡漏的地方。
“在拍卖会上最能体会‘知识就是力量’”
晶报:但是这个漏不是每个人都能捡到的?
韦力:所以在拍卖会上,何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知识就是力量!能否买到钟意的好书,全凭知识积累。你读的书比别人多比别人深,你捡漏的概率就比别人大。慢慢我就喜欢到拍卖会去了,高价货就让那些有钱的大佬斗去吧,我捡我的漏。这么多年来就我一个人在写拍卖会的书评,每一场的亮点是什么,好书是什么,哪些是漏的,我都写出来。这些书评已在前几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中国古籍拍卖述评》(上下册)。
晶报:为什么写这个?
韦力:上千年来,我们都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到书店里买。只有拍卖会出现了,才彻底打破了这个格局,改变了中国古书流通的格局和渠道。但是对于这新鲜事物,人们往往不介意,不去研究。几年后才知道价值巨大。而我恰逢其时,从第一场开始就在场,所以要把它系统地记录下来。
晶报:这么多年是不是很少有像您这样一直买下来的买家?
韦力:20多年来,已经有5拨大买家不见了。比如说当年有个买家,很疯狂也很张扬,每次都办81号牌,大家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号码,他说他要像解放军一样,要打败古籍市场的所有人。但是后面听说生意失败,也就再不见人影了。就这样一拨一拨,我就看着潮起潮落,人来人去。这么多年了,我就像个“不死鸟”还有这里。
晶报:这些年,民间的藏书意识越来越浓,对于这些新手藏家,您觉得除了知识储备,在拍卖时应该注意什么?
韦力:其实与别的艺术品相比,古籍需要知识密集度最大,不读书而藏书的概率不高。所以这项事业还是读书人的爱好。就价值而言,在古代的时候,古书的价格比现在要贵。比如说地方志会记录当地的藏书家,但是你不会看到藏画家和藏诗家。无论什么艺术品,都需要典籍去印证它的价值。所以,文字的载体书籍,永远高于其它门类。
晶报:似乎在拍卖会上看不出这种优势?
韦力:没错。古籍在拍卖会上的表现却不是如此。张大千的一幅泼彩,齐白石的一幅虫草,那价钱比古书高多了。因为今天文化的断层,使得大家普遍以炫耀作为人生价值的体现。而古籍不利于炫耀,因为必须对方也要有一样的审美情趣和知识储备。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你,在当代,古籍远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价值。言外之意,它依然能捡漏。
晶报:但即使就是漏,你也得拿钱堆出来。那是不是钱少就不能藏书?韦力:其实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玩法。不能说我一藏书,就要收藏宋元时期的。爱书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没有等级之分。我藏宋元的我快乐,你藏明清的不也一样快乐吗?快乐是一种自身的感受。你完全可以在自己经济能力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做出选择,设定范围,买自己心爱的书,从中得到知识,感受到愉悦,这就够了。用不着非要一步登天。我对于爱书人的建议,是在经济能力之内,选一个专题,系统地搞下去,就可以得到很多快乐。当把它搞得很完整的时候,就体现出它的价值。这样既有精神上的收获,也有金钱上的所得,何乐不为呢?
谈收藏
“我拥有这些古籍可我不能禁锢其内容”
晶报:历来私人藏书家有两种体系,一种比较封闭式的,一种是流通式的,比如天一阁就是封闭式的只进不出,我们知道您也是只买书不卖书,是否可以算作与天一阁这种藏书体系有相似之处?
韦力:天一阁是个异类,当年的藏书品位极低。范钦(天一阁第一代主人)当年收藏的都是当代印刷品,真正能称之为书的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印刷垃圾。范钦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祖训,把天一阁用七把钥匙分管于七房,必须七房同时拿钥匙开门才能看书。恰恰因为天一阁不能让人阅读阁中书,所以才保存得好,流传至今。但它却是一种封闭的状态。
但我的“封闭”和天一阁有所不同。我这些年一直在陆续出版一些孤本,为什么呢?就是想让研究者使用,这本书归我,但内容属于读者,我拥有这件文物的物件,可是我不能禁锢这文物中内容的传播。所以近些年来我出版了一系列的书介绍这些孤本中的思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作者的思想。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需要利用这些技术。
晶报:您这些古书的储存是按照什么方式分类收藏?
韦力:从近几十年的藏书史来看,大部分的藏书家都按照专题收藏的范式分类。专题收藏的好处是便于研究。所以很多学者型的藏书家,比说朱希祖研究南明史,郑振铎收集大量与苏联文学相关的文集。傅惜华专门研究小说史,就收藏了大量的小说、戏曲等方面的藏书。
可是中国传统的藏书史以整体性为依据。既有为了保护典籍,也有为了治学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但以我的观点来看,有功利目的绝不是真爱。真正的爱书之人是为保护好书,让书能够流传下去,不在乎此书好不好用。我藏书是为了能把书很好的保留下去。我的藏书既有内在的体系性,又有其专题性。
晶报:您一直把稿抄校本作为收藏的正统,近几年才开始收集一些其它种类?
韦力:中国古代有个校勘学派叫虞山学派,主要搞古书的刊本校勘,因此产生了大量的藏书。由于中国语言系统的特性是以元音发音为主的语系,很多字同音不同义,在传递的过程中会出现谬误。因此,中国古书中以讹传讹的不少,于是就有了校勘学,将许多古书抄本进行校勘。
校勘学催生了许多的藏书,校勘学也留下了许多的藏本。版本越多,你才能判断出哪个字才是真正正确的。样本越多,比照的也就越精确。只有更加接近正确,才能正确理解古人的思想。因为校勘学产生了许多的版本需求,因此校勘学的产生而出现了许多的批校本。批校本是中国藏书中重要的一个品种。这就是为什么抄校本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专题。
“我比古时藏书家下的力气要多得多”
晶报:您有没有对比过以您的藏书水准和数量,相当于古代藏书家的哪个段位?
韦力:我的藏书质量和数量综合起来,可以达到清代中期,乾嘉时代大藏书家的水准吧。但是不谦虚地说,我达到这个水准,比当年那些大藏书家都难,原因是我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不同了。
晶报:具体说说有何不同?
韦力:首先,从1949年之后,我们变成了公有制社会,大部分的私人藏书汇进了公共图书馆,不能拿出来参与市场流通。市场上可以流通的这些善本,比古时少之又少。我今天能达到这种规模,比古时藏书家下的力气要多得多。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所有的书都是流动的,大部分的善本都是私人的,通过私人的交换和买卖进行交流。
但是,有赖通讯和交通的发达,我比古时的藏书家得到书的信息要便利很多。比如说,古人在广州发现了一本好书,他写信告知北京的友人,而告知信要在路上行走好些时日才能到达北京,等那个友人知道这个信息后,也无法知道这部书是不是真的具有价值,到广州亲自去考察又需要花费几个月的路途时间。因为当时没有照相技术和网络科技,而我呢,接到电话,坐上飞机,就可以跑来一探究竟。这是我比古人便利得多的地方。但是天下事总会有利有弊,我比他们便利的同时,选择余地就比他们少了许多。这就是客观的比较,我比古人有便利的地方,也有艰难之处。
晶报:您是否有心仪的藏书家?
韦力:有一个人我比较崇拜,那就是黄丕烈。在他之前的藏书家都是校勘家,这是站在学术的角度看。黄丕烈不同,他把古人的校勘学发展成了书跋。他的这些书跋主要记录了他当时的得书经过,得书心情以及得书的花费等等。有些人认为他写的这些书跋毫无价值和意义,但是后世却对他极其的喜爱。现在黄丕烈写的这些跋语按照国家定级标准来看,一律都属于一级文物。他所写的书跋被后人称为“黄跋”,是中国古书界的四大名品之一。就是他写的这些看似无用的文字,在今日具有非凡的价值。
黄丕烈是第一个把生活、把文人写入书跋之中,而不是一种冷静的学术研究。他开创了一个题材,把一个死板的研究文本变成了可读性强的人文文章。以前的学者认为这是闲笔,这就是学者与文人之间的不同,也是黄丕烈的独具个性之处,他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有意思的文本。而我的写作,也借鉴了他很多。
“在机会来的时候能够快速识别并拿下”
晶报:藏书这么多年,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呢?
韦力:其实从藏书来说,人性使然,得不到的总想得到,没有得到的总是好的。而所有印象深刻的,也总是没得到的。人人都津津乐道于捡漏。捡漏是意外所得,意外所得都来自于自身广博的读书。捡漏就意味着你得有充分的准备,在机会来的时候,能够快速识别并拿下,这种获得就刻苦铭心。
晶报:能说说您有哪些意外的捡漏吗?
韦力:举个例子,许多藏书家都喜好收藏《二十四史》,1920年,柯劭忞写了《新元史》,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将其称为“第二十五史”,但是《新元史》的手稿谁也没见过。有一次我阴差阳错,在北京遛地摊。说起来我向来不遛地摊,因为觉得地摊一般都不会有太好的书,那天也是心血来潮,看见一个摆地摊卖书的,注意到两大捆脏兮兮的书,我无意翻阅,发现内容是《新元史》的内容,再核对笔迹,正是柯劭忞的笔迹。于是,确认《新元史》的手稿。我就很激动,问卖主多少钱,卖主伸出来两个指头,我问“两万?”卖主摇头;我又问“两千”?卖主说“两百”。我高兴坏了,当即买下拉回家了。
这么重要的手稿我就花了200元就轻易得到了。这人生际遇得益于我之前所做的准备。首先是我认得宝,知道这个东西的重要性,才能“轻易”得到。
晶报:现在很多人搞主题收藏,比如印谱等,有什么诀窍呢?
韦力:古代印谱一直是中国古书收藏的一个门类,印谱的数量比印书少得多。古书一般情况下刷印是三五百套,而印谱只有二十套左右。站在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谈,它显然要比同代的书要贵。这是人们没有意识到的。
一般收藏都是原钤印谱,要一个印一个印打上去的。而我们市面见到的印谱,大部分是印刷物,这个没有特别大的收藏价值。一句话概括,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就是你要藏别人没有的东西,如果别人有的,你的要比别人的好,或者比别人的有特色,这是收藏的基本理念。
晶报:您在收藏时是否发现不同地域的不同收藏风格?
韦力:北方藏书和江南藏书最大的不同是北方注重皇家刻书。中国皇帝是家天下,因此刻书会用最好的纸,最好的工匠,最好的装帧、最好的印刷技术。皇家刻书代表每个朝代最高的印刷水准。从印刷史的角度来谈,它的确达到了每个时代的极致。书都是纸制品,每个时代的装帧都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北方藏书家注重皇家刻本和装帧艺术。而南方藏书更注重校勘的作用。
晶报:在您看来,广东地区的藏书情况是怎样的?
韦力:清代出现了重要的文人和藏书家,尤其在清代中期以后,满清政府开始搞通商口岸,广州是当年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聚集了很多洋人和大商人,比如说像伍崇曜,是广州十三大家之一,在广州建起了当年比较重要的藏书楼,叫海山仙馆。再晚一些有东莞的莫泊骥,西医出身,当时与军阀关系甚好,敛了很多钱,建了很大的藏书楼,叫五十万卷楼。后来因为战争的原因,他的藏书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收录在广州图书馆。
清代之后,广州出现了很多的藏书家。主要是因为有钱。毋庸讳言,藏书是很费钱的事,如果没有钱很难收集完整的一套藏书。有一个让我疑惑的是,广东和福建很近,福建从清代以来就是全国的刊刻重地,被称之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同时又离广东这么近,为什么没有把这些书运到广东?迄今我也没弄明白其中缘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