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11月29日,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音乐理论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我最为敬重的中央音乐学院老院长赵沨诞辰一百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隆重的赵沨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活动。我这个不务正业的弟子怀着异样的情感、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
赵沨院长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活动有两项内容:一是赵沨译配歌曲以及著名弟子们演奏的音乐会,二是赵沨学术研讨会。出我所料的是,当钢琴大家刘诗昆同学演奏完《降A大调波兰舞曲》 、小提琴大家盛中国同学演奏完维尼亚夫斯基作曲的《传奇》之后,琵琶大师刘德海同学右手怀抱琵琶,左手拿着一只宜兴小壶走到舞台中央,向着赵沨院长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一躬,接着说道:
“赵院长,我知道您爱喝名牌咖啡,可我没有,只有普洱茶一杯,我一边弹奏《听茶》 ,一边请您品茶,希望您在《听茶》 、品茶中感到我们对您的感恩。 ”
刘德海坐在琴凳上,酝酿了一下情绪,遂动情地奏响了似能穿透时空的《听茶》乐声。全场师生屏息听乐,真是安静极了!很快,随着刘德海同学那紧扣心弦的《听茶》琵琶声,我渐渐地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很是自然地想起了赵沨院长对我这个穷孩子的特殊栽培……
一
1958年初夏,一列驶向天津的慢车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与客车里播放的《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的气氛是那样不协调。我坐在热得赛蒸笼的座位上,左手抱着半袋俺娘亲手蒸的白面馒头,右手拿着两支装在俺娘亲自缝制的布套中的竹笛,心无旁骛地幻想着投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那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河东区大王庄,附中设在离院部不远的一座院子里。我因为在天津举目无亲,被负责接待的师生安排在一间琴房里,临时给我搬来一张破旧的木床。我操着浓重的吴桥话说了一句“谢谢! ”他们相视一笑,什么话没说就走了。我看着他们的表情感到是那样的不舒服,遂暗自说:“不要以貎取人,咱们走着瞧! ”接着,我去院子中找来一块青砖当枕头,把俺娘亲手蒸的那半袋馒头放在砖头旁边,从布套中取出一支昆笛,似示威性地吹响了难度很高的南派风格赵松庭的《早晨》 。
七月初的天气是很热的!白天,渴了就对着水龙头喝几口自来水,饿了就啃一个俺娘蒸的白面馒头;晚上,我穿着那身农民装束的衣服倒在没铺没盖的木板床上,枕着那块青砖,就像在老家那样任凭蚊子叮咬,我自岿然不动,很快进入梦乡继续做着考试的美梦。
就要进考场考试了,我学着家乡比武、打擂台的样子暗自说:“一定要吃饱,吃饱了,参加考试心才不会慌。 ”可是,当我从布袋中取出馒头一看:白白的馒头皮上长出一层绿毛,我知道这是天热造成的。没办法,我只好把眉头一皱,一边揭去长毛的馒头皮,一边吃着变了味的馒头。
这时,考生陆续走进了附中的大院,嘈杂之声越来越响。
为了不影响自己考前的情绪,我连头都不抬一下,继续低着头啃着长毛的馒头。突然,我住的琴房门口安静下来,正要自问“发生了什么情况” ,就听见一位操着上海口音的女声十分可亲地说道:“考生同学!赵院长来看你了。 ”
我一听赵院长来看我了,惊得我慌忙抬起了头,只见一位身材微胖、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镜片的眼镜、叼着一个从未见过的大烟斗的中年人很有艺术风度地向我走来。我急忙站起,手拿着半个长毛的馒头说道:“您、您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沨院长? ”
“对!你准备考什么专业? ”
“我准备考作曲理论和民乐笛子两个专业。 ”
赵沨院长听后笑了,说道:“有意思,一个农村的孩子竟然报考两个专业。你会吹笛子我信,可你凭什么要考作曲理论专业呢? ”
我听后急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地方小报:“这是我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歌曲,您看? ”
赵沨院长接过我手中的小报看了看我写的歌曲,信口说道:“有点意思。 ”接着他又问道,“你的笛子吹得怎样? ”
我赶忙答说:“南派风格的会吹赵松庭的《早晨》 ,北派风格的会吹冯子存的《喜相逢》 ,还有山西风格的刘管乐的《和平鸽》 ……”
赵沨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不要说了!我不是考你的老师。结果如何,由考你的主考老师说了算。 ”他说罢于无意中看见了我手中那半个长毛的馒头,随手拿过去看了看,严肃地说道:“你为什么要吃长毛的馒头?知道吗?吃了是要生病的,赶快把它扔了! ”
我听后猝然之间来了气,噘着嘴说道:“我把它扔了吃什么? ”
“去街上买烧饼吃啊! ”
“我没钱!再说啊,有钱,俺娘就不给俺蒸这些馒头了。 ”
赵沨院长听后沉默了,当他听我讲完自己讨饭的童年以后,当即取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请给这位考生十元钱、十斤全国粮票。赵沨。 ”接着,他又关切地对我说:
“你拿着这张条子去院部总务处,他们会给你全国粮票和钱的。一句话,长毛的馒头不能再吃,要扔掉。 ”
就这样,我用赵沨院长特批给我的全国粮票和钱,如愿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作曲和民乐笛子两个专业。当主考老师问我入校后选择哪一个专业学习,我毫不犹豫地答说作曲理论。当主考老师问我为什么,我说了这句至今还记得的话:
“我想当中国的贝多芬! ”
说来也巧,中央音乐学院于暑假搬到了北京,本科和附中在一起。因此,我真正在音乐学院读书是从北京开始的。
中央音乐学院被称为“贵族学院” 。我的学长郑伯农在回忆当年我在音乐学院读书的情形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音乐学院是个颇带洋气的单位,这里的教师有不少是欧美留学生,音乐教材多是西欧和俄罗斯的古典音乐。柱子在这个单位里显得有点‘另类’ 。他来自河北农村,是个土气十足的穷学生。冬天穿着一身黑棉服,裤子的裆特别大,一张嘴就是口音浓重的河北土话,活脱脱像个燕赵小‘老农’ 。 ”可以想见,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在“贵族学院”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同学们取笑似的学我说话,偶尔拿我“开涮”也是家常便饭。就说个别洋范十足的老师吧,也曾公开地说我是“赶大车的”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也有一些不入流的生活习惯让同学们产生反感,或曰难以忍受,竟然告到附中女校长俞慧耕老师那里,出我所料的是还惊动了赵沨院长。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我从小在土坑上睡大的,从来都是赤条条地倒在坑上就睡着了,不知短裤为何物。再者,我自幼喜爱读书,苦于农村无书可读。因此,一见音乐学院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书,我就借回宿舍里,光着身子躲在被窝里打开小手电筒读书不止。不知是哪位同一宿舍的学友向俞校长告了我的状,一场传遍全校的笑话发生了……
俞慧耕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她长得非常漂亮,我记得那时她烫着发,擦着淡淡的红色唇膏,和我说话总是微微地笑着,从未见她发过脾气。一天晚上,熄灯的铃声响了,我照旧爬上木床的上铺,脱去衣服,一丝不挂地钻进被窝,打开手电筒看书。正当我兴致勃勃地看书之际,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宿舍的电灯被人打开了,我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俞校长走到我的床前,撩开我的被子,对着我光着的屁股“啪、啪、啪”打了三下,我来不及弄清这是为什么,只是本能地缩着身子用手捂着下身遮丑。这时,俞校长生气地责问:
“王朝柱!你睡觉为什么不穿短裤? ”
“对不起俞校长,我从小就没穿过短裤。 ”我赶忙一边捂着下身一边答说。
“为什么你母亲不给你做短裤穿? ”“好像我的父母也没穿过短裤。 ”“明天,你必须去街上买两条短裤换着穿,不准光着屁股睡觉,你听明白了吗? ”
“我听明白了,可是我没有买短裤的钱。 ”
俞慧耕校长哑然了。有顷,她声调很低地说罢“熄灯后不准看书,这是校规” ,遂转身有些沉重地走出了宿舍。可同宿舍的同学却发出了开心的笑声。
第二天,我在院长办公室的大门口见到了赵沨院长,他看着我有些难为情的样子说道:
“你们的俞校长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不要不好意思,我已经特批了给你买短裤的钱。 ”
“谢谢赵院长。 ”我近似哽咽地说道。
“不要谢,说不定啊,你穿上短裤还不习惯呢,甚至连觉都睡不着! ”
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一直想不通一个一院之长,为什么对我这样一个穷学生如此关心。事后,俞校长告诉我:赵沨院长辞谢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来音乐学院任职之后就提出招收工农子弟学音乐的主张,尽管当时有着不小的阻力,但他坚持在附中办工农子弟班。就这样,我才能如愿考取附中作曲理论学科,接着又升入本科,念了五年作曲系。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虽然说音乐的语言是无国界的,但是一个听惯了传统民族音乐的文艺工作者,你再是音乐天才,也听不懂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外国音乐大师的交响乐。对此,我是有深刻体会的。
我早年在家乡曾经看过《贝多芬传》 。从这部传记的作者——法国文学巨匠罗曼·罗兰的笔下深深地感到了贝
多芬的音乐是何等的崇高和伟大。那时,在我少年的心中还十分天真地坚信:只要能听到贝多芬的交响乐就一定会着迷的。为此,我正式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之后就订了一个学习贝多芬音乐的计划:每天除去正规地上入门的音乐课程之外,我还雷打不动地坚持听一个小时贝多芬的音乐,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先从小奏鸣曲听起,一直听完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结果一年下来,我还是没有听懂贝多芬的音乐。与此同时,当我再看到准备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的殷承宗、鲍惠乔等同学摇头晃脑地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作曲家的钢琴协奏曲以后,我真的对自己想当中国贝多芬式的作曲家的理想幻灭了。我历经痛苦的思索和抉择,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叩开了赵沨院长的办公室,一见面就有些惨然地直言相告:“赵院长!我打算休学回家种地。 ”“为什么? ”赵沨院长有些惊诧地看着我问道。
我把一年来学习的经历细说了一遍,遂又不堪回首且又是万分痛苦地说道:
“我连贝多芬的音乐都听不懂,何谈当中国的贝多芬式的作曲家呢!用我们老家的话说:麻袋片做龙袍,我不是学音乐的料,还是回家种地的好。 ”
赵沨院长听后十分平静地告诉我:“这是十分正常的。不要灰心,听我的话,你再继续听一年到两年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之后,如果还是听不懂,我就批准你休学。 ”
暑假到了,我回到故乡看着那熟悉的青纱帐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心情是那样的愉悦。但是当我想到在未来一年到两年继续听贝多芬、莫扎特等音乐大师的无标题音乐后,内心又泛起一层似乎拨不开的愁云迷雾。
第二学年开学之后,恰逢是开国十年大庆,全国人民非常关注的十大建筑如期完成了,的确给古老的北京增添了新鲜的光彩。一天傍晚,我和几个约好的同学信步走到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文化宫,看到剧场的门前挂着一块巨大的演出广告标牌,大意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苏联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来华告别演出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吉赛尔》 ,地点:新落成的民族文化宫剧场。这些结伴同行的所谓天之骄子们一见来了情绪,并借题发挥,谈完了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在舞蹈界不可撼动的至尊地位,又大谈柴可夫斯基为舞剧《吉赛尔》写的音乐有何等的伟大。最后,当他们再回到现实之后,一个个又喟叹不已地说道:“咳!要是有张舞剧《吉赛尔》的票该有多好啊。 ”对此,我是一言不发,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像这样高级别的观摩票我是没有份的。
翌日下午傍晚,我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只见赵沨院长迎面走来,拿着一张票对我说:“朝柱,你想不想看乌兰诺娃的告别演出啊? ”
“想啊!是她跳的《吉赛尔》吗? ”
赵沨院长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是! ”遂又指着自己手中的票说道:“这是文化部有关的演出单位送给我的观摩票,你拿去看吧! ”
我急忙摆着手说道:“不,不!还是赵院长您去看吧。 ”
赵沨院长知道我矛盾的心理,遂告诉我他还可以向演出单位要票,保证能看到乌兰诺娃的告别演出。
我双手接过赵沨院长手中的票,下意识地向他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转身近似小跑似的快步走去。或许是太激动了,我是如何连走带跑赶到民族文化宫剧场大门前的,真的是一点印象都记不起来了,到剧场门口检票员伸手拦住我,接过我的票看了看,遂又表情严厉地上下打量我的穿着以后,我才回到现实,并生气地说道:
“看什么!我的票是假的吗? ”
“票是真的,可我怀疑像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首长席上的票呢! ”检票员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是你应该管的事嘛! ”我一把夺过戏票,把头一昂,挺着胸脯走进了剧场大门。
赵沨院长曾出任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艺术局局长,送给他的观摩票自然是首长的席位。那天,我坐在六排一号,在我的左右前后的观众多是西服革履的官员和艺术家,像我这样一个尚不满十八岁——且又身穿农民衣着的小青年坐在正中央的坐席上的确是扎眼了点。对此,我是习惯了,有意把腰板一挺就等着大幕一开,听着音乐大师柴可夫斯基的音乐,观看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跳《吉赛尔》了。
演出前的铃声响了,紫红色的大幕徐徐打开,随着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吉赛尔》的序曲结束之后,乌兰诺娃等男女演员相继上场,用芭蕾舞蹈那特有的舞蹈语言演绎着舞剧《吉赛尔》的情节。我从未看过芭蕾舞的演出,更不知道乌兰诺娃是用脚尖跳舞。他们一会儿跳独舞,一会儿跳双人舞,一会儿又是满台的男女演员跳起了集体舞,这和我在家乡看的戏曲演出怎么也联系不起来。令我更是不堪入目的是乌兰诺娃等女演员的舞蹈服装——在当时的我看来几乎是没穿衣服。我强忍着看了十多分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遂悄然站起,擦着黑离开了座位,接着又沿着剧场的人行廊道大步踉跄地走出了民族文化宫剧场。
翌日中午,我应约赶到院长办公室,赵沨院长请我落座之后就十分严肃地问我,看了芭蕾舞皇后乌兰诺娃的告别演出有何感想啊?我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观感。令我震愕的是,赵沨院长猝然变色,非常严肃地说道:
“朝柱,你说的和我想象的差不多。 ”
“那您为什么还要我去看她的演出呢? ”
“我想借此认真地批评你一次。 ”
接着,赵沨院长指出:你听不懂贝多芬的音乐,看不惯乌兰诺娃跳的芭蕾舞,这说明你的艺术思维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看社火、跳大秧歌的水平。党把你从农村招到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是想让你把全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舞蹈、歌剧等学到手,然后再创作我们自己国家的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这时,他点燃烟斗深深地吸了两口,又问道:
“你应该知道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吧? ”
“知道。当年我在农村还曾组织同学们演出,是我亲自指挥他们唱《黄河大合唱》的。 ”
“很好!你知道吗?大合唱在外国叫‘康塔塔’ ,是冼星海成功地把它移植到中国来的。这部《黄河大合唱》唱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灵魂,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走上战场,打败了日本鬼子,迎来了我们的新中国。 ”
说句自我吹牛的话,我从小就很有些灵性,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孩子。因此,未等赵沨院长把话说完,我就抢先坚定地说道:
“赵院长,您不用说了,我全都懂了!今后,我会向冼星海那样向一切外国的优秀艺术学习,努力地创建中国的艺术学派。 ”
从此,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海中学习游泳,未经两年,我不仅听懂了贝多芬、莫扎特,而且还把艺术的触角深入到印象派大师德彪西、拉威乐的音乐中去了,待到我升入本科作曲系在二年级学习的时候,竟然写出了无调性的钢琴小奏鸣曲,受到了一些老师的批评。就说看芭蕾舞吧,我不仅看懂了她那独有的艺术之美,而且在赵沨院长兼任中央芭蕾舞剧院院长的时候,在他领导创作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过程中,我还从旁说过一些见解。为了弥补自己艺术上的无知和过失,苏联解体不久我就到了莫斯科,请友人带我到乌兰诺娃的墓前,我亲自献上一束向大师补过的鲜花,并在墓碑前恭恭敬敬地默哀一分钟。
三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我正躺在邮电医院的病床上等着做盲肠炎切除手术,同班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在院长办公室的东墙上贴了我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名字叫“打倒赵氏王朝一根柱! ”我一听怒火中烧,遂提前出院,立即投入到用大字报方式的论战中去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想想我和赵沨院长的关系,同学们贴“打倒赵氏王朝一根柱”这样的大字报不是很正常吗?可是那时我年轻气盛,一听就火冒三丈,心里想:“钢琴没有你们弹得好,但是我写反击你们的大字报一定比你们写得好。 ”事后想来,我在“文革”初期一定伤害了不少出身不好的师生,愿借此向远在音乐天国的老师们致歉!
好在,我保赵沨院长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被可爱的同学们打成了铁杆保皇派。对此,我的学长郑伯农写下了如下这段文字:“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到来后,柱子并没有走进造反派的潮流。他是学校保守派的中坚人物。保守组织被冲垮后,他也没有弃旧图新、改换门庭,起码对运动持观望的态度。这在今天看来,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在当年,却被视为‘顽固不化’ 。为此,他在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被审查、被批判……”就是知道了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革命’ ,王朝柱也没有跟着走,他经过认真的独立思考,站到‘文革’的潮流之外去。 ”后来,“我曾听说,他在天津葛沽的日子很难过,受到批斗。 ”在这期间,我见赵沨院长的机会不多,像过去那样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就更没有。或许是老天开恩吧,我在天津葛沽劳动改造的第三个年头,管我们的解放军同志希望我去保定三十八军外调赵沨,了解有关音乐学院教学的一些情况。我欣然同意,第二天就轻车简从,一个人赶赴三十八军的学生连。
我住在三十八军一个师的招待所里,坐在一个原木制的桌前,有些不安地等待赵沨院长的到来。有顷,门外传来“报告”声,我学着军队首长的口气答说“请进来! ”只见一个警卫员引消瘦许多的赵沨院长走进来,警卫员刚刚走出大门,我就禁不住地叫了一声“赵院长! ”几乎是扑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了赵沨院长。出我所料的是,赵沨院长却十分理智地推开我,连声说着“不好!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 ”我把赵沨院长搀扶到一张木椅子上坐下,仔细地打量我熟悉的赵沨院长。
赵沨院长看了看我的样子,冷静地问道:“朝柱,你来找我是外调吧? ”
“不!准确地说,很久不见了,想来看看您。当然喽,我必须打着合法的理由——那就是外调,才能达到看您的目的。 ”我说罢引得赵沨院长也忍不住地笑了。
在我们的交谈中,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了解两边师生的情况上,自然也问了赵沨院长的生活和健康状况。那天他很开心,还一块在招待所里吃了顿客饭。最后,他问我:
“朝柱,我听说你在辩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时候,人家问你是什么出身?你答说‘我从周口店就是贫农’ !有这事吗? ”
“有!那时,我纯粹是拿中学生们寻开心。当然,也是为了给我反对这副对联增加一些砝码。 ”
赵沨院长听后开怀大笑。接着,他又认真地说道:
“你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讨过饭的孩子,现在林彪集团被粉碎了,我估计你会很快调回北京的。 ”
赵沨院长的判断是正确的,转年我就调回总政文工团工作。接着,我又到总政干校劳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赵沨院长。再后来,我因为各种原因由作曲改行搞文学戏剧创作了。一是隔行如隔山,再是我有着一种无脸见江东父老的心理,很少回中央音乐学院,更不愿意见到赵沨院长。我记得在北师大举行大学生电影节的时候,组委会主席黄会林大姐向我发出邀请,并代表生病的老领导丁峤出席,讲几句祝贺的话。我准时走进贵宾休息室,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所熟悉的赵沨院长叼着大烟斗坐在首长席上。我急忙走上前去,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十分愧疚地说:
“赵院长,我是王朝柱,您还认识我吗? ”
“你就是烧成灰我也认识! ”赵沨院长说罢用手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坐在这里,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来学校,也不到我家来看看我? ”
我扼要地讲了自己的理由,并希望赵沨院长见谅。但他仍然不依不饶地说:
“你没写出交响乐,却写出了那么多的文学、戏剧作品,不也是很好吗?再说,我看了你写的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 ,我就很喜欢。 ”
“请赵院长放心,我相信明年七月一日播出的长篇电视剧《长征》 ,将会更好,到时请老院长批评。 ”
这时,铃声响了,赵沨院长站起身来,把他手中的黑皮包递给我,几乎是命令地说:
“搀着我,进剧场开会去。 ”
“是!我终于给您当了一把秘书。 ”我搀扶着赵沨院长走进了剧场,一起出席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
翌年七月一日,我写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准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原本想等着《长征》的光盘出版以后,多带几套去看赵沨院长。没想到我所敬爱的赵沨院长于九月一日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为了寄托我的哀思,也为了让后人永远地记住这位音乐战线上的一代宗师,我在写长篇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的时候,把他和光未然、李凌、李元庆等大艺术家写进剧中,在重庆庆祝《百团大战》胜利的时候,由年轻时代的赵沨亲自指挥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我记得再见到师母——吴锡麟教授的时候,她激动地拥抱着我,连声说着“谢谢!谢谢……”
随着琵琶大师刘德海同学演奏的献给赵沨院长的《听茶》的结束,我对赵沨院长的追忆也就定格在心灵的屏幕上。是日下午,赵沨院长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开始了!当大会司仪宣布我第一位发言后,我快步走上主席台,向着我敬重的赵沨院长的遗像深躹一躬,遂简要地讲了赵沨院长作为当代音乐界的一位代表人物,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和音乐活动等战线上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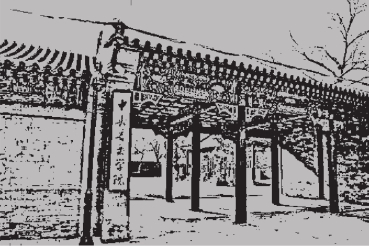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