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任:相比改造这个世界 我更想去理解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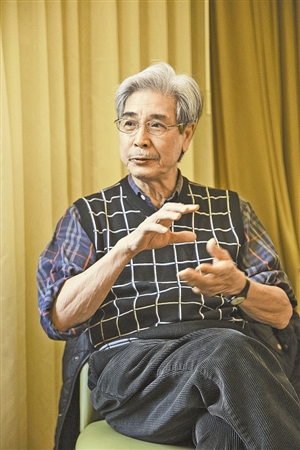
《当下四重奏》开篇《搬海棠的那天》,刘大任便提到搬家时移植海棠的故事,我们对他的采访,也就从他醉心的园艺开始。
谈园林哲学:应尊重植物的生命
晶报:在您的小说中经常会写到“园林”,您好像对很多植物、动物都相当了解。
刘大任:我从小就爱玩儿这些东西,一面玩一面就会找书看,越看越多,慢慢就积累了这些专业知识。
晶报:您书里写的“翠园”真实存在吗?
刘大任:是的,我经营了不到四年,整个地大概11亩,几乎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原来的园主就只种了一些韭菜,我现在种的东西慢慢多起来,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荒凉,很多野生动物常常在我们家后院玩耍。
晶报:您笔下的园林是否寄托了某种想法在里面?跟海外华人的处境有关吗?
刘大任:所谓园林,西方的园艺学,就是在地上建造天国,即你可以控制的环境,这是第一种哲学。第二种哲学是是仿造大自然,把大自然迁移到自己居住的环境里面。这是英式园林的理念。
晶报:您说您的园林参照英式的园林,但是从您书里看到的意象,满满都是中国。
刘大任:这个不奇怪。因为中国大概是世界园林文化里最喜欢人工栽培的国度。
晶报:那为什么是英国式的,而不是中国古典式园林呢?
刘大任:中国古典式园林是把人的居住环境跟大自然里面人认为最美,最喜欢,最喜欢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有的植物都是为人而活的。人喜欢听下雨时雨打芭蕉的声音,所以芭蕉就要住在廊檐的附近,人爱听,但是芭蕉不太快乐吧,打久了叶子会烂掉。所以中国的园林是为了人的快乐、享受而存在的,涉及到的哲学是不太尊重植物。英国园林的设计它第一个哲学就是尊重植物的生命,把它种在园林里的时候尽量模仿它原生态的环境,这样的话植物当然长得好,长得快了。植物最美并不是说灌了很多的肥料,开了很多花是最美的。植物最美的时候是它非常喜欢它生长的环境,你就觉得它真的很快乐。
谈鲁迅作品:其中力量让人震撼
晶报:您年轻的时候看鲁迅比较多?是如何接触到他的作品的?
刘大任:我当时念大学二年级。我父亲是一个工程师。他那时候参与建设台湾第一个水库,所以他把家搬到水库的建设工地那一带去。通过朋友介绍,把他安插在图书馆附近住,弄了一个行军床。他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堆本来准备丢掉的书,就拿来给我看,其中有一本就是鲁迅选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鲁迅,相当震撼。
晶报:震撼在哪些方面呢?
刘大任:可能对每个人的震撼程度不一样。但对我而言,第一个就是他的语言,不仅仅是简约,里面藏着一种力量,这个语言是我在台湾其他的作家里面没有看到过的。他文白夹杂用得很好。在台湾能看到的作家(作品)是徐志摩、朱自清等人,他们很喜欢用形容词,初中看还觉得不错,高中以后,就觉得有点滥情。再跟鲁迅的文字一比,马上就会觉得无力。鲁迅在小说里面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感情,是在台湾当代文学里面看不到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像他的《药》,批判辛亥革命的失败,但同时对中国的国民性有一定的批判,但是一个批判的词都没有用,完全用形象,让你自己判断。
晶报:您说过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留学生中间传阅最广的是陈少校的《酒畔谈兵录》《金陵残照》。
刘大任:这两套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陈少校的《酒畔谈兵录》,共有六本,大概讲的是国共斗争期间的各大战役。它不能算是专业的写法,但有很多专业知识在里面。《金陵春梦》是一个演绎式的小说,是香港的左派作家写的,现在看它是宣传品,里面有很多歪曲的事实,但那时候我们看得很过瘾。
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觉得有两种心情决定我们的想法。一种心情就是屈辱感,历史的屈辱感,另外一种心情是民族文化的自豪感,这两种心情很矛盾,可是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感情基础。
晶报:你现在还偏“左”吗?
刘大任:我不认为自己是左派。如果把自己看成左派,需要有一个理念,就是你要改造这个世界。我觉得我理解这个世界还来不及呢。
晶报:参加“保钓”运动对您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大任:那一段经验把我的整个人生规划完全打乱了,但是很多事情都会打乱我们的人生规划。就像我原来到美国来念书,打算念个硕士就回台湾,我在台湾有一批朋友,我们有一个计划,连名字都取好了,叫“大汉计划”。至少有5到6个人,有的是搞摄影的,有的是写作的。那个时候就是想大家把力量集合在一起,慢慢形成现代传播事业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台湾连一个现代化的广告公司都没有,电视也才刚刚开始。所以搞文化事业会大有前途。我们那时候办的《剧场》杂志,对侯孝贤影响也很大,但参加运动把这些规划都打乱了。
谈小说创作:希望文字简短、含蓄、有力
晶报:您在联合国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在那边做翻译的话应该接触的大部分都是公文吧,是如何继续创作小说的?
刘大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搞“保钓”运动,我的文字风格就变成战报体,宣传体,搞翻译以后,翻译的文件性质种类很多,预算委员会的报告就完全谈财政的问题,如果是一个海洋法委员会的报告,那就完全谈法律的问题。所以做翻译需要有各方面知识,最重要不能出错,而且我们在联合国做翻译有一个要求,原文出现的每一个字都要照顾到,不能够跳过去一段,省掉一两个字,尽量使它读起来流通。受工作的影响,文字就会变得很怪,和搞文学创作的文字不一样。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多阅读多思考,想办法慢慢找出自己的路子来。
晶报:您的小说很喜欢用短句,这是您自己琢磨出来的风格吗?
刘大任:我在对抗联合国文体和运动文体的时候,开始找《左传》《战国册》《史记》《聊斋》这类的书来读,因为想改变自己的文字,就要看人家是怎么运用文字的。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也有点拖沓,喜欢用形容词,慢慢渐入中年后这样的文字自己也不喜欢了,看了古人的一些文章以后,慢慢就很自觉地在让文字往简短、含蓄、有力的方向走。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