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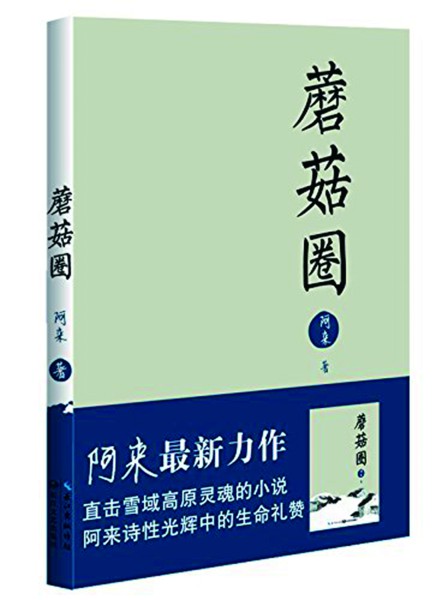
日前,阿来携自然文学三部曲“山珍三部”《河上柏影》《蘑菇圈》《三只虫草》现身上海书展并接受记者的采访,他表示:“我不愿意改编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一遍。”
最好的调整方式 源自写作本身
“去年我突然就想,一定要写一个轻松、轻盈的、透明的小说,我觉得只有写作,才是对自身从情绪到思想上都是一个调整。我想作家写作最好的调整方式,就是用写作本身来调整。轻盈、轻松的目标,在第一篇作品《三只虫草》中基本达到了,后来我觉得沿着这个路子再写,写第二篇《蘑菇圈》,第三篇《河上柏影》。”阿来介绍说,《三只虫草》确实反映了乡村,中国边疆地带的教育问题,我们教育的资源,也是大量往城市集中。《蘑菇圈》谈到的是这样一种东西,在乡村秩序到底起到什么作用,怎么又重新调整乡村的秩序。
在阿来看来,如果只是关注消费社会,那些边疆可能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风景比较好,文化保存比较完整,旅游开发的目的地,这样大家进入一种消费,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这种地方出产一点城里人稀奇的东西,就是消费社会需要的消费价值。“所以我就选了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虫草,第二个是松茸,这两个都是吃的东西,有营养、很珍稀、价格很高。虫草几十万,比黄金贵。松茸这种普通的蘑菇,它的当地卖价700块,到高档的酒店,上个松茸汤,常常漂着一片松茸。”他表示,《河上柏影》更是奇妙的,今天中国人对稀缺的东西都疯狂的感兴趣。“今天走到一个人家里,你看有张桌子,不是桌子是怎么样的,是说这个桌子是什么木头,我有个柜子,这个柜子是什么木头。当成功的人、有钱人消费这些木头的,其实意味着在野外稀缺的资源大面积消失。”
风格并非刻意制造
阿来说,三部小说是轻松、透明的,透明也是《尘埃落定》比较擅长的风格,有评论者将其看做一种回归。
“我倒是没想过回归,或者语言风格的问题。我们很多写小说的人,愿意自己建立一种风格,容易被大家识别,说这是谁的文字。我自己反倒是,我总觉得,当然一个当家能有自己的风格更好,当然我希望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刻意制造出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转换不同的书写对象,也就是写作的题材在变化,有时候需要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结构方法,我想也会带来叙事方式的变化。所以我说轻松、透明,可能第一部是大道理,比如我自己需要调试,刚好又写的小孩子在高原上,有点像历险记,我觉得他是进入社会的历险记,我的意思是,不要让他在探险中自己迷失掉。”
写完《三只虫草》,阿来有些高兴,觉得自己没有失去那种力量,他相信人性永远向着美好、文明一面的发展。“但是我们没有信仰,我们自己都对这样的力量表示怀疑的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假大空的东西,最后写完以后,他居然没有迷失自己幼小的心灵,这是写小说的自觉、自信,我倒觉得我自己身上还有一种干净的东西,在文学中相信信仰的力量。”
不想改编自己的作品
“80年代以后的文学,受西方文学影响比较深。不光是某一个流派、技巧,现代文学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力、荒诞、反叛,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社会的恶、人性的恶,这方面比较多。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在这些方面这几年的书写,也应该说有比较大的成就。”阿来举例说,现代的文学上,最早在中国组织翻译现代文学的一位老先生,临终之前他有个反思,他说现代文学是非常极端的,它的深刻是通过某种偏激和极端,但文学本身,至少回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不是主张这样的文化观念,要把人性中蕴藏的东西,善良、美好、温暖的东西发掘出来。
“所以我自己希望在本来并不美好的社会,本来存在种种缺陷的人性当中,我希望慢慢从中发掘出来一点东西。我们经常把文学和拯救联系在一起,我们觉得是连接不起来,只有这样,文学这个词才能跟情感拯救联系在一起。”阿来说。
很多作家选择亲自改编自己的作品,对此阿来表示,从来不改编自己的作品。
“我知道改编比较挣钱,但是我知道这辈子用不了那么多钱。第二,我不愿意改编自己的东西,因为这个故事我已经讲过一遍,在讲这个故事之前,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是不知道的,写作的乐趣在于,我在故事展开过程,不断捕捉它的种种变化、种种可能,看到一个故事慢慢成型,乐趣就在这儿。如果写完了,下次再来改编,整个故事不会再有新的东西。如果改编电影电视,要更多往更为通俗、意义更为单薄的方向发展,它跟小说、文学不一样。好多人说,改编你的小说少,编辑很难改编,如果你愿意改编,你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改编,我说不愿意。有人让我改编,我说既不改编自己,也不改编别人,我重新写一个新的作品,写个新的电影,他们说可以尝试。我写过一个,作为剧本还算成功,因为几大电影节最佳剧本奖,至少提名奖都得了。”
“你可以把剧本写得很好,但不能保证,最后成品拍出来,是不是一致的。尽管这样,架不住,这个世界总暗藏着一两个能说服你的人,说服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有个人说服我,再写个电影剧本,我正在受此煎熬。”阿来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