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谢有顺的文学批评之道:“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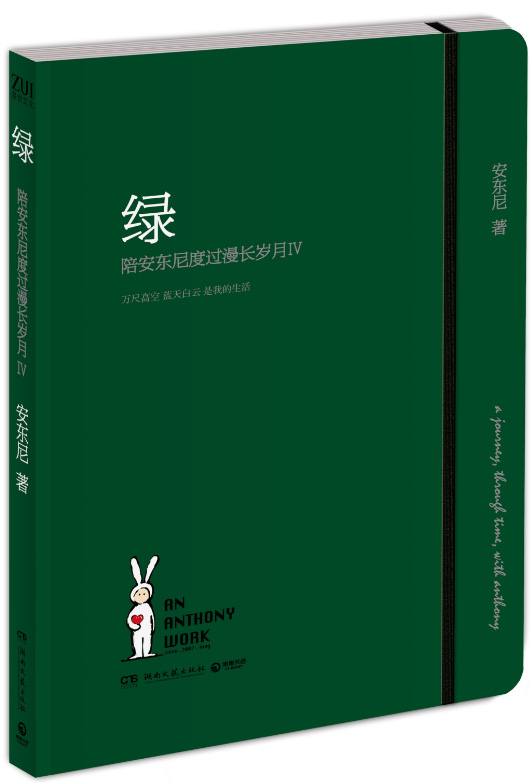
2017年4月28日,作为第二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的重磅评委之一,谢有顺受邀来成都参加了该奖项的颁奖典礼。不管是来自全国各地出席典礼的青年作家,还是四川本地文学圈的作家,见到谢有顺,都有一种亲切的敬佩感。找他签名,邀请他写书法留墨宝。面对如此鲜活、灵动、丰神俊朗的白面书生,人们很难不产生好感。而这一切欣赏和好感的背后,正是对谢有顺一流的文学才华的认可。谢有顺的文学批评文章,在朋友圈被同道同行热传,人们佩服他的洞见,又惊喜他的行文气质,感到一种心灵的畅饮和精神洗礼之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能大概分享一下您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吗?
谢有顺: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这可能是最为理想的批评。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时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倾全灵魂以赴之,目的是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所以我所梦想的批评,它不仅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更是有见地和激情的生命的学问。只是,由于批评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批评家普遍不读哲学,这可能是思想走向贫乏的重要原因),批评情绪流于激愤,批评语言枯燥乏味,导致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批评这一文学贱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难以改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从您的文章可以看出,您对乡间故土的依恋。现代化、城镇化对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让很多有乡村背景的人有一种创痛感。很多写作者开始了自己的书写。从整体观察来看,您如何评价这种书写?您本人作为写作者,感到自己有责任作出自己的书写吗?您作为一个文学的专业研究者,对文学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高度的热情。对于自己的写作,您有怎样的愿景?
谢有顺:尽管现在的新作家,很多都出自都市,但在血缘上,多半还是植根乡土;离开了乡土,就无从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费孝通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乡土社会。确实,无论城镇化的进程如何迅猛,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国族精神还是乡土的:社会规则的建立,多和乡土的伦理有关;每年清明、春节大塞车,大家多是往乡下去;最动人的文学描写,也多是作家关于乡土的记忆。中国文学中,最好的作品,都是关于乡土叙事的,这种乡土资源里,隐藏着一整套关于中国人生存的解释方法。这是极为重要的认识尺度,离开这个尺度,对中国人的描述就可能是残缺的、表浅的。我们这块土地有如此深重的苦难,也有如此灿烂的荣耀,这么多人在此生生不息,活着,死去,留下了太多的故事,也留下了太多的叹息,可在现有的书写者中,还远没有写出真正震撼人心的故事,也还没有挖掘、塑造出这块土地上真正得以存续的精神。二十世纪来,中国的文学多是揭露、批判,写法上也多是心狠手辣的,它对黑暗和局限的描写,达到了一个深度,但文学终究不仅是揭露的,不仅是对黑暗的认识,它也需要有怜悯和希望的声音,也需要探求福克纳说的“人类永垂不朽的根源”。就我个人而言,我很想为自己的家乡写一两部书,相信记录个体的乡土经验是有价值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一个青年作者,要找到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方向,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有不少人发现,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同质化的现象,比较严重。您作为文学研究者,会怎么说?
谢有顺:这令我想起一个“80后”作家对我说的话。她说,我们已经无法再进行《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了,更不可能像古代作家那样,细致地去描绘一种器物,一张桌子,或者去描写一个人的穿着,一次茶聚,一场戏。古代作家由于地域和交流的限制,他所看到、遭遇的经验各自不同,他写这种有差异的个体经验,谁读了都会有新鲜感。但是,现代社会不同,现在的孩子,从小到大吃相似的食物,穿相似品牌的衣服,甚至戴的眼镜、用的文具盒都可能是同一个品牌的,大家的成长经验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假若有哪个作家在小说里花很多笔墨去描绘一个LV包,或者讲述自己吃麦当劳、法国大餐的滋味,岂非既无聊又可笑?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作家经验的差异,以建筑为例,以前有北京四合院、江南园林、福建民居等地域差别,现在,从南到北,从新疆到海南,房子都建得几乎一样,衣服、饮食亦是如此。大家说一样的话,住一样的房子,穿差不多的衣服,接受几乎相同的教育,这样的公共经验已经不足以成为一种写作资源。所以,写作如果只靠阅读经验或书斋里的想象,就容易变得苍白、无力。我经常说,好的写作,既要用心写作,还要用耳朵、眼睛、鼻子甚至舌头写作,要有丰盈的感觉,作品的气息才会显得活泛。同时,经验的同质,也迫使作家开始转向内心的写作,这反而是好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您曾经说,当代文学令人兴趣越来越小,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所提供的精神容量越来越小。对当下国内文坛的写作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您总体有怎样的观察和印象?
谢有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面几代作家,几乎都是通过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来塑造自己的文学影响、文学地位的,可如今,这个由期刊、评论家和文学史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在“80后”这代作家以及更年轻的作家身上,似乎解体了,代之而起的是由出版社、媒体、读者见面会所构成的新的三位一体的文学机制。而出版社、媒体和读者见面会背后,活跃着的是消费和市场——正因为这一代作家不回避作品的市场问题,所以,他们的写作,多数是读者在场的写作,他们不是关在密室里写,而是注重读者的感受,也在意和读者的互动;通过网络、读者见面会或媒体报道,他们能时刻感受读者的存在,这个存在,也从正面肯定他们的写作价值。这当然是一种断裂,但也绝对是重新出发。我觉得,他们终将会改变我们对“文学”的固有理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在当下,视频直播、影视作品吸引了年轻人大量的时间,有的是纯为了娱乐,也有从中寻求精神产品的欣赏的。文学这个事物,应该在现代人精神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有人说,文学未来更多会以碎片的形式,散落在很多载体之中,您怎么看?
谢有顺:文学一是让我们洞察人性的复杂与丰富,二是建立起人类精神的标高。作家个体的观察与体验,永远是独特的,不可或缺的。所以,有创造力的文学还会在各类文字艺术中起引领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影视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很热。因此有评论家认为,纯文学有一部分要走向市场,通过市场获得新生。您认同吗?您有怎样的观点?
谢有顺:不必刻意联姻,但也没必要拒绝。市场如何,不是作家本人可以决定的,卖得好的书也不是可以预先策划的,它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作家不该天天琢磨市场,而该专心写好作品。每部作品都有自己的命运,但好作品一定会有好的命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有一个说法比较常见: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是小部分人的事情。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您有怎样的观察体会?我们当下处于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种种纷繁复杂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心灵样貌。是一个特别值得书写的时代。应该说,这样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与之呼应。但至今好像一直没有出现这样级别作品的迹象。您怎么看?
谢有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精神的主流、潜流,也有写作的主流和潜流。我们很容易加入到时代的主流合唱中,写精神的主流。但我们不能忽视主流之外的潜流,不能忽视一个时代有可能正在发生的那种细微而又不可忽视的变化。
一个作家如能成为领风气之先的作家,他一定能率先看到时代内部可能发生的细微变化。如鲁迅在他们的那个时代,率先发现了别人所没有发现的事实,才能写出那种具有高度的时代概括性的作品和人物。可当代的许多作家,是在惯性里写作,被时代卷着走,他们对一个时代精神气息的流转并无察觉的敏锐,也无引领的勇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