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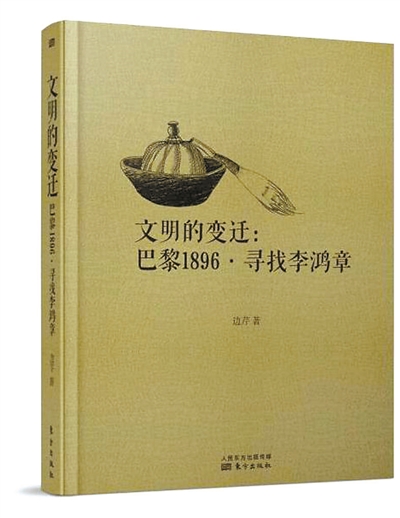
边芹曾常年旅居法国。2005年,她的第一本著作《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出版,备受好评,然而某些读者似乎未曾觉察这本优美的“法国文化随笔”之下暗藏的潜流。此后,随着专栏文章的发表和《谁在导演世界》、《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的出版,潜流澎湃而出,边芹致力于揭示西方构建“中国话语”的娴熟机制,文章中时有政论式的风雷之声。
今年3月,东方出版社推出了边芹的新作《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1896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出访,巴黎是重要的一站。一百多年后,边芹根据当时报刊记载和已解密的官方档案,一一细访李鸿章所到之处,文明的变迁,就在两个中国人相隔百年的足迹之中。边芹说:“这本书的重点不是解读中国,而是想透过李鸿章的西游,让读者感受十九世纪工业文明与古老农业文明在一个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都市的碰撞。”
历史的叙述意味着现实的激情。边芹为重新认识西方打开了一扇窗,她呈现的风景,与我们习见的迥异。
对十九世纪的再认识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
青阅读:首先请教您的新书《文明的变迁:巴黎1896·寻找李鸿章》的写作缘起。您是怎样注意到了李鸿章的法国之行?
边芹:早在写作《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一书时,由于大量阅读,触碰到西方的十九世纪,这种触碰要比从前在国内泛泛了解世界史深入而细致。由此发觉那个世纪不同一般,至今牵制人类命运的资本战车及其目标“全球化”就是从那时全面起动的,其大规模的工业化和社会变革与今天的中国有着很多相似的轨迹。今天世界的大变革都能到那个世纪找到导火索,包括为衬托工业化的“西方”而找到的对立面“东方”(农业社会)这些前定了我们思维的概念。对十九世纪的再认识,对我有点翻天覆地的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九世纪于我们是一个致命的世纪,是这个世纪开启了中华文明前所未有的内在崩溃。千百年来不管多少武力强悍的异族入主中原,中华文明从未失去其文化自信,然而十九世纪同样是武力征服,且并没有被全面军事占领,却动摇了不可动摇的根基,令我们至今生活在那个断层上。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在用文明的对比这一被引入的歧路归结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然后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这一被引入的歧路在长时间里和大范围内锁定了我的思维轨道,直到我利用旅居之便,接触到第一手资料,得以绕开舆论先导,绕开他们专门为我们进行的解释,深入早已被过滤掉的细节,进入转换后丢失的场景,才茅塞顿开,发现了西方的理论家们一直避免向后进国家提示的“要点”,即“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中国之间真正的决定因素,不是文明的差异,而是大资本与工业化。你只要深入十九世纪大工业热潮中的法国,这一真相扑面而来,是工业化改变了一切,从无到有创造了一切。工业文明有别于人类任何一种古典文明,将工业化社会与农业社会对比,并由此总结文明的差异,进而引入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是一种蓄意误导,差不多就是让人沉疴不起而出具的假药方。
此一发现还伴随着另一发现,即从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形成了至今并未有根本改变的“中国话语”——针对中国的话语。此一话语正是从那个世纪起始,一改十八世纪之前的话语,产生了它的固定模式,我称之为“征服模式”,从此怀疑、否定、蔑视、敌对甚至暗中构陷成为难变的底蕴。此一话语构成了从精神层面主导、诱导中国大量文化精英的“国际舆论”,在军事战场之外开辟了另一征服战场。
这两大发现如果合在一起看,实际上是同一个大进程呈现出的两面,这个“大进程”就是当时名词本身尚未被设计出来的“全球化”,资本要闯入全球每一个有利可图的角落。从这个视角出发,十九世纪与今天便连成了一条线。李鸿章在十九世纪末的那次西游,也就超出了中西关系狭窄的两点,而露出了掩藏其下的棋盘、棋子和棋局。这是我关注李鸿章西游的大背景。当然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在巴黎旧书报摊意外瞥见一张1896年7月26日星期天的《小日报》头版,上面是一幅李鸿章的肖像画,下书“法国的客人——中国特使藩王李鸿章”。
这些必然和偶然因素,让我觉得如果能透过西方的“中国话语”解读十九世纪中国对西方的第一次正式官式访问(1866年清廷派出过一个考察团赴欧,虽然也是官派,但名义上是民间非正式访问),尤其参与者还是李鸿章,对国人思考我说的那两大发现,意义自不同寻常。细读这本书就会体察我在追溯李特使旅法足迹时,对一些重点事件和地点的记述,都尽可能还原十九世纪的氛围,让对近代史感兴趣的读者去体味史书上没有的细节,进而思考十九世纪的中国为什么会落到那一步。
当然我的目的并不是做史,尽管书中有关李的行旅每一个细节都有出处,并不敢添加想象。我更愿意读者把它当作一本追踪寻迹的文学随笔,那样可以更放松地跟着我的追索去体味翻天搅地的十九世纪。
青阅读:您的书不仅追溯了李鸿章的足迹,也呈现出巴黎的百年变迁。今昔对照,在寻访的过程中,您最深切的感受是什么?
边芹:我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殖民大帝国收回到原有疆界的速度,以及弱者的报复。今天中国旅游者看到的漂亮法国,大半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工业化迅速暴富而留下的遗产,全世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加上那时尚存的手工留下了细节的奢靡,后来的世纪已经很难做到。单看看巴黎的大博物馆里有几件宝物是自家地下挖出来的,就心中有数了。
但如果你把两百年的历史铺展开来看,那惊涛扑岸的征服也带来了回水倒流,几乎每块被征服的大陆或多或少都抛回了一点贫困和卑贱,几乎每个大城市边缘的政府廉租房都挤满了遥远征服地的移民,他们做着法国人不愿做的活,住在优雅市中心和田园乡村之间的丑陋地段,大量地生育以领取政府为推迟老年化社会而发放的生育补助金。工业化和消费社会虽然提供了充裕的物质生活,但也以飞快的速度拆毁着保证一个文明绵延的内在机制,这非常可怕,那种社会机体在歌舞升平中的自解,就在你眼皮底下发生。
欧洲从文明的角度而言,确实在急剧地衰老
青阅读:在新书中,您谈到了“在奢华中迅速衰老的欧洲”。这些年来,法国固然仍令人追慕,但是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唱衰法国、唱衰欧洲乃至唱衰整个西方世界的声音(比如对西方民主的不信任,对“白左”的嘲讽等等),对此您有何评价?
边芹:我个人认为,用“唱衰”这个词带了些许贬义,不如说是事物复归原位,真相浮出水面,虚构的价值泡沫正在一点点被挤掉。对西方民主不信任,是因为实地去看的人发现那远远不是我们以为的民主,而应称之为民主的幻觉。当然能把幻觉做得百姓当真、世人皆慕,也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在这点上我由衷佩服西方的上层精英。
欧洲从文明的角度而言,确实在急剧地衰老。美国《时代周刊》大约十年前曾发过一篇文章,大意是“法国文化已死”,当时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歇斯底里式的反应。我作为局外人,客观来讲有同感。其实不光法国,西方文化整体都在堕落。原因诸多,其中资本垄断致使文化“低俗化”、“幼童化”,“政治正确”一统天下,生育不足致低素质人口增长快,是主要症结。资本说到底就是靠让百姓变得更蠢来统治的。中国才搞了三十年市场经济,你看如今文化变得多媚多俗,就知道了。人家已搞了两百年,能保持到这份上,就不错了。我在书中说“文明越走越灿烂是痴人说梦”,就是这个道理。文化整体陷落,产生英杰的温床便不复存在,也没有吸收的土壤了。
我们在二十世纪仰慕的西方,正是十九世纪工业化的辉煌和短暂摆脱一神教的精神桎梏催生的历史巅峰,这个巅峰还有一个烘托的基础,就是剩下的世界之文明文化被打翻在地,一个上升一个下坠,将十九世纪以前相对均衡的世界打碎了,由此产生了必要的敬慕和不切实际的崇拜。这种状态不可能永久维持,何况“巅峰”上的人自己作茧自缚。讴歌“原始文化”、“保护少数族群”,让音乐、舞蹈落到何等原始地步?“当代艺术”又让美术堕落几何?所有旨在摧毁国家的暗手并没有提升文化。法国精神领域的“独立和自由”还剩多少幻影?“政治正确”的阴影笼罩着几乎每一个文化领域。仅以我最熟悉的电影为例,除了脱衣尺度这一看得见的自由,体制的控制无孔不入,对会看的眼睛,就是一切政治挂帅。这种“政治挂帅”与我们中国人理解的直接喊口号很不一样,这里的“体制”也不是政府,控制更不是明的,而是暗的,深含技巧。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几乎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全球征服的武器。我们中国人想想都会奇怪,一个“民间、私营、独立于政权”的文化组织为什么带有如此使命?百万法国民众上街强烈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电影节就马上捧出一部同性恋电影给予其最高荣誉;伊朗被制裁,电影节就成了其反政府“艺术家”的大本营;为了推翻叙利亚政权,再没有水平的电影都可以“破格”入围……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最高艺术甄选标准是政治这条暗线,这就埋没了多少真才,又捧出了多少虚名!什么样的文化经得起这样的暗手长久折腾?
青阅读:欧洲目前确实问题重重。欧洲文明自身似乎也走到了一个焦灼的关口。您认为欧洲文明有渡过难关、自我修复的能力吗?
边芹:先来确定一个概念,我个人以为您所提的“欧洲文明”范围不好界定,我理解您指的是西欧这一片,也就是近代最早经历工业革命、殖民扩张的国家。为避免概念纠缠,还是用“西方文明” 界限较明晰,这是他们自圈的概念。
“西方文明”的崛起,有一个本质的因素,就是紧紧伴随着军事的强大,也就是说不是发展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这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上傲视东方并非靠军事摧毁对手,而是靠发达的农耕和手工业。工业化彻底结束了冷兵器时代的力量对比,使得西欧这几个历史上好战的小国打遍天下无敌手,以古典时代不可思议的速度通过殖民主义迅速占领和控制全球资源和市场,建立起史所未见的庞大帝国,要知道英、法帝国的边界一度都与中国接壤。所以“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傲视群雄,有两大因素是不可回避的:一是殖民主义,二是工业革命。这两大因素的前提条件,就是军事上可以事先摧毁对手,以利自己巧取豪夺。
历史即便不被表述,也已经摆在那里,正是通过殖民掠夺和工业化,欧洲快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后来让全世界其他文明都产生自卑感的“西方文明”就是在财富的堆积上建立起来的。但如果军事上不再能指哪打哪事先削弱或摧毁对手,“西方文明”在逆势的时候会如何表现,历史还没有证明过。这与中华文明能在逆势中涅槃的历史很难比较。过去西方也出现过类似危机,他们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对外战争是西方解决内部问题的一个捷径。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还不仅仅产生于自身,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他们正在失去工业革命的绝对引领地位,中国这个在十九世纪被他们打垮的苦难国家艰苦卓绝地弯道超车,令他们一手经营的不公平世界之种种便利不再那么理所当然,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我还真有点怀疑,西方一旦失去其压人一头的强势地位,是否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以及长久维持文化霸权的可能。
西方的话语权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
青阅读:您的几本著作致力于揭示西方文明隐藏的话语运作机制,痛感中国人普遍丧失了“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而不自知。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和您在法国的生活经验有关吗?比如说,2008年的几件大事唤醒了很多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对您而言呢?
边芹:2008年只是出现强烈拐点的一年,但精神准备要远远早于这一年。西方社会的实质有点像西方人的本质,收藏极深,然后通过层层包裹呈现出想让你看的那一面,比如比你强盛,他先说是因为基督站在他们一边,后来又说是得自古希腊便有的民主自由。你读十九世纪的书报便会发现,当时“民主”这个词并不像如今这般时时挂在嘴上,那时主要强调基督教战无不胜和种族优越,比现在直白。
在西方长期旅居或定居的中国人,或早或晚会面临一个选择,即你在哪一边。并没有人公开来逼你,但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反华、排华会将中国人送到三个阵营里,最广大的一群我称之为“利己派”,他们不去听、拒绝看,全部的精力都用于为自己奋斗,无所谓西方人怎么对其母国,只为狭处求生存;第二群人我称之“融入派”,这群人的行事特点就是“你们不是讨厌中国吗?那我比你们更讨厌中国”、“你们打中国一个嘴巴,我就打三个嘴巴”。唯有这样,方可安生。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要么麻木,要么“比你还”。不这么做就得落入第三群人——“压抑派”,这群人的特点就是为其良心所累而长期处于精神抑郁中,敏感的人甚至会有时时被铁烙的痛楚。这就是2010年前的现实,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但基本现实很难根本扭转。在这样的处境里,你只能在这三个阵营里选择一个,甚至都谈不上选择,而是随着自己的本性走,能麻木的,会过得心安一点;能“比你还”的,就融入了;心思转不过来的,就只能痛定思痛了。我就是在痛定思痛中,得以绕开西方预设的话语,去阅读、观察、思考,进而有所发现的。
青阅读:“二战”以后,西方文化界、学术界逐渐出现一种“反西方中心”的倾向,您怎样看待在西方内部兴起的“反西方中心论”?
边芹:这是为大目标“全球化”做的舆论准备的一部分。早在“二战”刚打完,“世界统治集团”就已经策划解构实体的殖民帝国,因为难以为继、成本太高,尤其是道义成本。新形式的“经济殖民”、“精神殖民” 收益大而成本小,已经无须十九世纪的军事入侵和占领。看看现今的中国就一目了然了,三十年代哪怕租界遍地的上海,你能找到一个染金发取洋名的人吗?现在的“西方中心论”根本无须那头公开挂牌,这头已能自产自销了。
青阅读:中国需要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话语权。那么,如果我们需要和西方争夺“审美权、道义权、历史解释权”,您认为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边芹:说实话,这问题不好答。一方面,西方的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一种完美的技巧构成的。我们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首先得参透西方的话语技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比如我发现的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战技之一。所谓电影的细节接力就是利用画面对人潜意识的影响,反反复复地用同类细节进行精神移变。由于细节并非一部电影的主题,甚至也游离于情节之外,可以是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或偶然提及的名词,也可以是一个道具,或某类人的形象、某种场景的氛围,但如果这些细节被有意识地长期植入各种电影的画面中,所暗中形成的“接力”便能在受众不知不觉中对其潜意识实施控制。应该承认,西方对人的心理研究超前于我们,我们没有将此作为战略目标,像对导弹、卫星那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西方的真正统治者(并非政府内阁)深藏幕后,知道“温柔的独裁”和“话语统治”才是现今和未来世界的统治利器,早在上世纪上半叶就已全力投入研究。这三十多年,以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名义走遍中国城镇乡村甚至穷乡僻壤的西方某类学者,多半是在从事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工作。在软实力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力量对比,还处于十九世纪长矛大刀对火炮军舰的不对等状态。如果不迎头赶上,要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也只能是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我们的精英层如果不能自悟“审美权、道义权和历史解释权”是如何在无知无觉中被易手的,又怎么来“重新夺回”?我们是自愿把这三大权力拱手送给奥斯卡、金棕榈、金熊,送给诺贝尔、格莱美,送给汉学家……谦虚不等于丢掉自信。我最近偶然看到浙江某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宋》,在分析南宋历史时,此片以世所罕见的“公允”将历史解释权分到四拨专家手里:德、日、美、中。中国史学家未受到一丝一毫的“偏袒”,不是为“主”,而是其中不多不少的一分子。尽管纪录片并未对立中西专家的观点,但这么做明显是在告诉观者,中国宋朝历史自家学者的观点也不足为信,必须有外国(西方)专家来证言。试想法国人拍一部解释拿破仑战争的纪录片会请中国史学家插嘴吗?所以首先必须自醒、自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