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江西作协 江西文学 为推动江西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2021年7月,江西省作协举行了乡村振兴和现实题材中短篇小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丛书书稿征集活动,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活动共收到应征作品21部。 经组织专家认真评审,共有樊健军的《向水生长》、文非的《渔船来到雨庵镇》、罗聪明的《树》、王明明的《风筝知道天空的颜色》四部作品入选。 近日,该丛书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 江西高校出版社编辑、诗人江榕撰写了评论文章《用悲悯情怀书写人类精神的原乡——浅评“乡村振兴和现实题材中短篇小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丛书”》。本公众号特推出该文,读者朋友们可从该文中管窥该扶持项目丛书作品风貌一二。 ——编者 20世纪初,倡导了“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曾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在诸多文学艺术形式中,为小说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其后经由新小说、“五四”新文学运动等,在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创作实践的跟进下,小说这一文体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群体,甚至从社会性的角度而言,逐渐获取了文学大家族中“长子”的地位。 毋庸置疑,在深入细致地表现时代、发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方面,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功效和角色塑造能力,先天具有文体上的优势,这也向广大小说家提出了课题:如何在文学史的漫漫长河中,为自己的小说作品寻找到一个相符的位置。 江西高校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乡村振兴和现实题材中短篇小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丛书”,辑录了樊健军、文非、罗聪明、王明明四位优秀的江西中青年小说家创作的《向水生长》《渔船来到雨庵镇》《树》《风筝知道天空的颜色》四部中短篇小说集。这套小说集,笔力稳健,题材求新,风格多变,地域特色鲜明,具有独特的叙事学魅力。四位小说家在创作的同时,展现了其所具有的书写时代的野心,他们或许风格和题材互不相同,但他们以阵列的形式,共同呈现了写作者对人类个体命运的终极人文关怀。 这是一种独立于叙事技巧之外的,关于人类精神原乡的悲悯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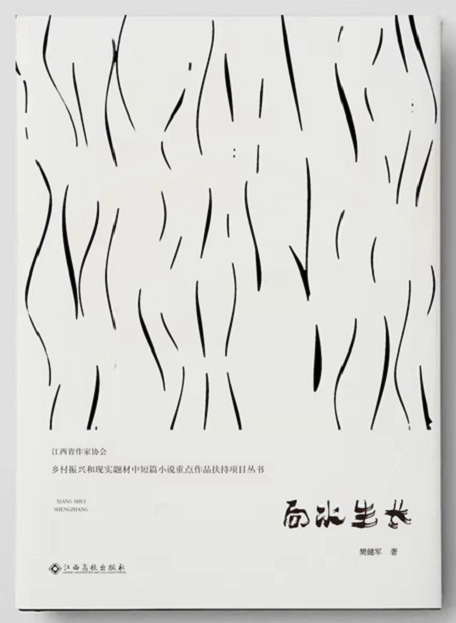 《向水生长》樊健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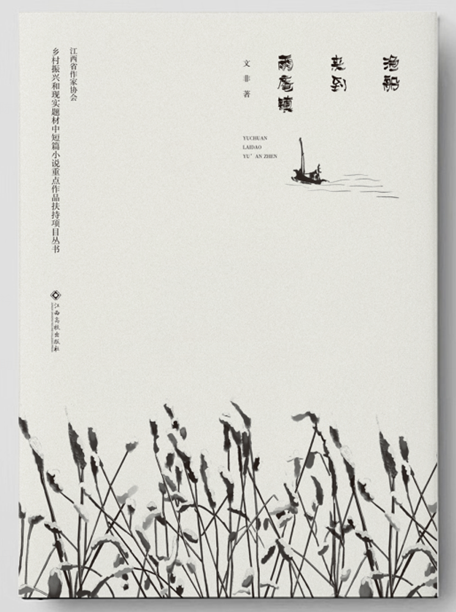 《渔船来到雨庵镇》文非 著 一、以原乡讲述表达悲悯情怀 在四本小说集中,作者均构建了一个虚拟的原乡,作为其故事共同的发生地。如樊健军的小说集《向水生长》中的“水门镇”,文非的小说集《渔船来到雨庵镇》中的“雨庵镇”,罗聪明的小说集《树》中的“神冲村”,王明明的小说集《风筝知道天空的颜色》中的“东北林场”。这些场所或作为故事主要的发生舞台,或作为一面虽然并未出现,但始终挥之不去的背景墙。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虚构的地域场景是他们乡土写作的载体,是乡愁的暗号与密码,这些虚构出的场所,是作者对于原乡的印象与幻想的集合体,也是作者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的寄托。 在四位作者的“原乡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各自表达悲悯的方式。 樊健军的语言丰富而开阔,文本间有不断回旋深入挖掘的力量。他擅长于呈现命运齿轮间个人的受难与抵抗,并从中迸发出悲悯的力量。在他的小说《向水生长》中,塑造了一个离家出走进城讨生活的水门镇青年平上喜的形象。他拥有一个并不平和,甚至可以说暴烈的家庭环境,在一次与父亲的冲突之后,他在一片茫然中进了城,面对未来,他毫无依仗,只能流浪度日。作者在此时让他遇见了贵人——贩卖木炭讨生活的胡佑德。相比于平上喜,胡佑德的条件并不优渥到哪去,充其量不过也是一个在城镇中挣扎求生的底层人员,但就是这样两个底层人员的相遇,却充满了互助的温馨。平上喜接受了本身并不宽裕的胡佑德的接济,分享了微弱的萤火之光,并在日后以一种温馨而持久的回馈相报答。而小说中还埋设了一条隐线,即胡佑德的儿子胡大鸣屡屡的不成器背后,埋藏着一段童年时期因恐惧而对小伙伴的见死不救,以及其后数十年的内疚和自我救赎。这样的情节设置,寻求的并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完美救赎,而是并无差异的生命个体之间的相携与互助。 在罗聪明的小说《树公树婆》中,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种角度描绘的乡村互助。神冲村的钟一阿婆九十五岁了,和丧夫失子之痛对抗了大半生,最后不得不和对她不好的儿媳月桂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她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和相扶走过大半生的从城里省亲归来后的明九老娘去“打讲”一番,好好说说这段时间以来心中的抑郁。而明九老娘,也并非家庭和谐到令人羡慕,虽然表面上光鲜亮丽,实则已经与丈夫老倌子形同陌路,从城里回来后向老倌子讲述子女的招待,也更多的是一种寻求观众的渴望。但即便如此,明九老娘也始终将钟一阿婆这位多年的闺蜜放在心上,当听说钟一阿婆意外落水之后,原本只想着送一件旧衣服的明九老娘犹豫之后,选择了送出自己亲手做的最为珍视的一件黑棉袄。但罗聪明在处理这段情节时,却并不是让人物简单地履行动作,而是将多方面心理因素的影响立体地集中在一个人物上。因为黑棉袄丢失而错过第一时间慰问钟一阿婆的明九老娘随即被钟一阿婆的反常举动所惊吓,从而对这位一起度过大半生的闺蜜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慌张。在此时,作者安排了钟一阿婆深夜叩响明九老娘的窗户,寻求“打讲”的桥段,在前奏所埋下的慌张情绪影响下,明九老娘以近乎躲避的态度拒绝了钟一阿婆显已癫狂的迫切需求,这直接导致了最终钟一阿婆的落潭身亡。罗聪明的小说立足乡土,侧重于对现实的关注,她擅长以明暗线写作,将对个体的悲悯与时代的渲染结合起来,我们从中看到的不是强者对弱者近乎施舍的帮助,而是不相称的施予与回馈之间隐藏的原乡的悲悯情怀。 类似的原乡讲述,在文非和王明明的作品中也是主流。文非的《对影成三人》,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一个让二叔耿耿半生的樊耕,而他令二叔耿耿于怀的原因,在于他遗失了一张记录了自己家乡地址的借条。在此后的生活中,他每次与二叔交集,都是在寻求这张借条,实际上,他寻求的是自己的家乡所在。小说在最后揭破这一冲突,使得前文中那些隐藏在荒诞之下的悲悯突破抑制,溢出到前台。此外,他的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写作对于现实独特的提纯和放大作用。不论是他的小说《对影成三人》开头,赋予二叔拥有独立生命的“第二条影子”,还是在《乡愁症患者陈自福》中,赋予陈自福一双可以听清蚁行虫鸣的神奇耳朵,又或者是《风筝》中那个把自己做成风筝,悬浮在半空中的父亲,文非对现实的种种魔幻化写作,最终都会落到“原乡”这个永恒的主题上来。相比于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写作手法更让我想起澳大利亚小说家理查德·弗兰纳根或波兰小说家布鲁诺·舒尔茨,他们在片段空间的讲述中都具有敏锐且鲜活的洞察力,对于异化的生活表述精彩纷呈。 王明明擅长多样化的写作,侧重于在故事之外的延伸,这尤其见于他的小说《气泡》。小说记录了女主人公苏澜的故事,伴随着外公的去世,已经迁往城市生活的苏澜一家从血缘到人情上,与原乡的最后一丝联系也告中断。作者对此的处理隐忍并且克制,用平静的口吻,不厌其烦地叙述外公后事办理的每一个流程和环节,其中却又冷不丁地穿插进几个舅舅家对苏澜一家的生疏与隔阂。原乡并不完全是地理范畴的概念,同时也是宗族和血缘的概念,王明明就用这样冷静酷似解剖刀的笔,将苏澜一家本就已经荒疏的原乡情结一一分解、剥除,并从中表达出对现代人精神漂流、无所依傍的悲悯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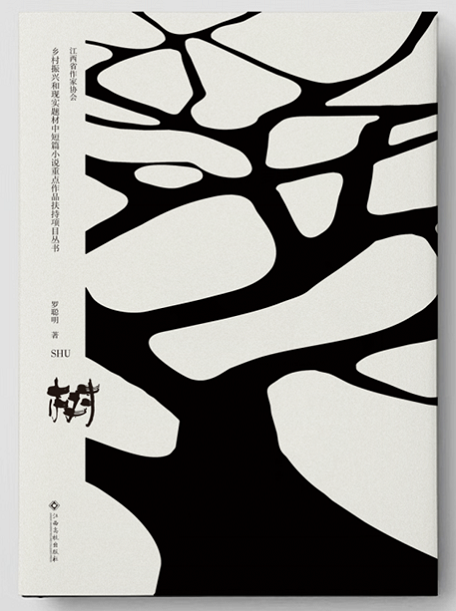 《树》罗聪明 著  《风筝知道天空的颜色》王明明 著 二、用悲悯情怀反哺日益远离的原乡 在四位小说家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对现代人日益远离的原乡的怀恋与哀悼,还有借由这种悲悯情怀所形成的共情效益,这使读者对原乡情结形成回归,并觉醒原乡概念所延伸出的精神之根的意识。 樊健军的小说《从何说起》中,借由返回水门镇考察的画家“茹先生”,将今天的所见与当年下乡知青时的回忆,以穿插的形式对比讲述了茹先生在水门镇下乡插队时的经历、他所爱过和被爱的人、他所遭受的磨难和受到的保护,并通过现实与回忆的不断闪回,一次次让读者见识到陶厂过去的欣欣向荣与现在的冷清破败。“茹先生”眼中的陶厂如同时间里的水门镇,物是人非,精气神全无,连茹先生此来,也更多地仿佛是走个过场。最后在为陶厂画出一批陶器之后,茹先生以一场突如其来的重感冒而终止了这场返乡的“拯救之旅”。其后,虽然茹先生为陶厂绘制的这批陶器卖出了不菲的价格,但对于陶厂而言,也仅仅只是回光返照的一次起搏。没有核心竞争力,仅仅重复过去生产方式的陶厂的衰败是必然,而陶厂又不可谓不是原乡的象征,在这样鲜明的象征叙事体系中,对暮气沉沉的水门镇的悲悯让我们不由得思考,原乡的出路何在? 罗聪明在小说《父亲的“花花世界”》中,以一条较为纯粹简单的叙事线,通过父亲为自己准备的寿材这条线索,将寿材的得失放在“我”的成长大背景中,作为串联起情节的线索。这篇小说,几乎纯粹以饱满的赤子之心的情绪讲述进行支撑。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乡,而这种满满的父爱,将原乡对于作者而言独特的安全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令读者不由得意识到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借由亲情与一方水土构成的社会性纽带连接,是那么地恒久而具有生命力。 王明明则选择书写精神意义上的“原乡”,即一个人初心的萌发之处,与其若干年来的坚守。他的小说《在南方欢聚》,小说主人公林夕人到中年,却突然重新拾起了“横漂”的初心,他说:“随着他一步步沉入现实生活,这个梦想被他渐渐埋在了心底。但毕竟是根深蒂固扎在那的。”对于一个事业并不成功的中年人而言,横漂的梦想就像肥皂泡一样华丽但不现实。林夕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对家人的责任感和生活的压迫之中感觉到绝大的阻力,但他却在这样的阻力之下,一步步有预谋地走向自己的梦想,那精神中的“原乡”。作为经历生活磨砺的社会人这不可理解,但作为纯粹的生命个体,这又并非完全不可理解,乃至于他所拜访的朋友刘天然对此感到不可思议的震惊之余,也最终选择了沉默的包容。我们可以看到,当林夕最终告别了一切,孤身一人走向理想之时留下了泪水。我们可以品味出那泪水中所蕴含的,是对在生活重压下蹉跎半生的自己的挥别,是对卸下责任的内疚与战栗,更是对初心和理想这一“精神原乡”的近乡情怯。 在文非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作家对于讲故事手法的重视。文非愿意在文本中立下一座又一座充满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比如在《乡愁症患者陈自福》中,痴迷故乡声音的陈自福用他的天赋为乡人解决了很多烦恼,但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能力渐渐成为乡人抵触和仇视的对象。作者在此时向陈自福投射了寻常逻辑上的悲悯,一种理想与现实、爱与背叛之间的挫痛。但面对乡人给予的压力和背叛,陈自福并没有选择最简单的离开,而是选择了一种极端的固守态度。他固守的固然是某种底线,也是对失去的故乡的缱绻。这种悲悯,就从陈自福上升到了原乡,对象也由个人转化为了群体。因此在最后,在他被埋在自己的堡垒一般的陈家土屋地下后,文非安排“有人用簸箕或手推车运来积雪,倾倒在土包上”,如此反复直至“很快,废墟上耸起一座洁白的雪塔,它的高度超过雨庵镇任何一座建筑”。这样的安排看似没有什么道理,但无疑这是一幕具有仪式感的纪念碑,它象征了一个人逝去的坚守与精神中的原乡。 四位小说家的作品,以他们各异的原乡写作,或深或浅地介入到现世的人文主义关怀当中,通过对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戏剧化处理,展现了“善”与“不善”、“美”与“不美”的对峙、冲突、妥协与转换,完成对角色的立体构建以及紧随其后的深入解剖。可以看到,他们迫切地寻求在作品中创造一个与现实相互映照又高度超越的叙事空间,并且借此表达自己对于时代浸染作用的宏观印象和对于个体精神世界的思考。 肖洛霍夫说过:“对于人类的悲悯是一个作家应坚守的基本原则,失去这个支点,任何美丽的叙述都只能是没有终极支撑的空中楼阁。”他们的写作,代表了当代小说家见证时代异化作用的勇气,也表达了小说家对于在“真善美”的影响下,人类自愈功能的期许。他们的写作,不避讳也不偏向底层写作,他们在冲突当中寻找个体与时代相处的方法与力量,而这力量便是源于人类共情功能下诞生的原乡情结与悲悯情怀——这一“人类的终极支撑”。 【作者简介:江榕,1988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国作协会员,江西评论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扬子江》《文艺报》《中国艺术报》《江西日报》等。】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