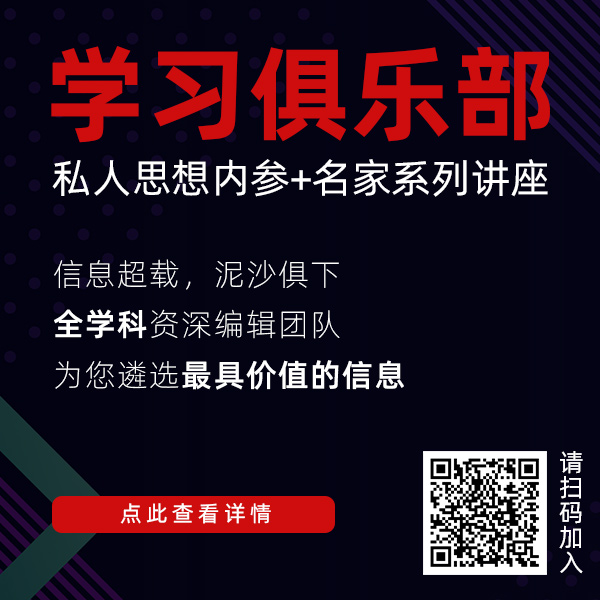 晚明文人,是近代当红群体,在各种《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中备受歌颂。你经常会读到描述他们如何深刻揭露了封建政治与道德的反人道的功绩、如何破除礼教、如何发展出了“左派王学”。 但是,你如果相信其中任何一句话,你就完蛋了,就再也不可能了解晚明思想发展的实况啦! 一、他们反礼法?不,是克己复礼的 李卓吾等晚明文人根本不反对礼法,他们非常强调礼法。 以李贽(卓吾)最亲密的友人焦竑为例,他不但不反对儒家之论礼,更试图调和老庄和儒家在有关礼法问题上的冲突,认为老庄也是讲礼的。指出:礼与道、礼法与性命,不应分开来看:无礼的生命流荡状况,更不能做为人生的正途。 所以礼就是道,外在的礼法其实也就是内在的性命。 但礼有两种,一就是这种能使人达到生命和谐状态的真正的礼,另一种则是一般世儒所胶执坚守的那种纯然外在的名义器数之礼。他反对后者,谓其“不知礼意”,而热烈呼吁恢复前者。 可惜大多数讲明史的朋友,头脑都过于简单,又疏于检核文献,于是一看见他们批评世儒之胶于礼法、执于器数,便立刻赞扬他们是反叛封建礼教的急先锋,认为他们揭露了礼法做为统治者钳制异己的本质。 甚至还有人据此推论到:李贽等人讲的“童心说”,就是基于反对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所以要“把人的自然欲望,如好货、好色、富贵利达等,做为正当的东西来宣扬”。 这真是睁眼说瞎话了。 由焦竑的言论来观察,焦竑等人对礼的强调,是无以复加的。一般人总觉得礼是外在的道德与行为规范,焦竑却将礼内在化、本体化,说:“礼者,心之体”“礼者,体也”(《笔乘》续集卷一)。因此人之行礼,并不是去依从一种外在的规范,而是生命与德目合一,耍祛除生命的情欲知见等障蔽,让心性本体得以恢复其清净,所谓“克己复礼”: 礼者,体也。仁不可名,而假于礼以名。…… 视听言动,而勿于非礼,即为复礼。……子瞻云:“如人病眼,求医与之光明。医曰:我但有除翳药无与明药。明如可与,还应是翳”。由此言之,世之求明而得翳者,岂少也哉? 礼不是外在的,所以只要视听言动不非礼、不妄生知见情识,就是克己复礼了。礼内在于人,一旦去除知见情识之翳障,就“恢复”了心体的合礼性。 这是心即理即礼的思路,自与程朱那种致力于存养天理的法门不同,但其重视礼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因为礼若局外在形式化之规范,人尚可以本心为权衡;现在,礼既然就是本心,则人在本质上就不能是非礼的存有。视听言动一旦不合礼,即是有病的生病状态。故而,本体论上对礼的强调,必然导致他们在现实活动上亦以礼法为主要衡断事务的依据,焦竑说:“晏子曰:惟礼可以为国,是先王维名分、绝乱萌之具也。定公为太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礼;三家为尾大不掉之臣,故欲教之以忠。” 直谓“唯礼可以为国”,且以忠孝为说。这才是他们用以评断或处理世务的原则,而非现今一般论晚明思潮者之所云云也。 二、内在化、本体化的礼:心即礼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时,曾筹资刊印过《太上感应篇》,人皆以为该文谈因果报应,太过肤浅,他则认为:“是篇言简旨严,易读易晓。足以破小人行险侥幸之心,以阴助刑赏之不及。” 以此书为世俗的道德教化工具,用以辅助朝廷的刑赏措施,吓阻小人作奸犯科。 他任官时如此,辞官而拟出家时,也写信给周友山要求资助,并说明若获得这项供养:“夫福来何以受之乎?唯有礼三宝、塑佛诵经,以祈国泰民安、主寿臣贤而已。” 这几句话系对老朋友告贷,所以也不必伪饰。他之落发出家,不是反叛的,而是辅佐的。并非基于对君臣政刑及国家礼法之反叛而出家,乃是出家以弘教护国,“阴助刑赏之不及”。态度与其刊印《太上感应篇》实甚类似。 等到他正式为龙潭的住持以后,在僧人的国度中,他的主要作为及用心所在,可说正是要继续贯彻“唯礼可以为国”的原则,替僧人建立严格的生活礼仪规范,用以整顿惰习、建立僧格。 《焚书》卷四收有〈豫约〉一文,指出僧人应注重礼仪:“岂可效乡间老以为无事,便纵意自在乎?”同卷又有〈告佛约束偈〉详细规定了上殿课诵的规矩。 这些规矩约束礼仪的要求,表明了做为僧人的李卓吾是刻意强调戒行的。而且他也认为当时僧俗败坏,非如此不足以建立僧格。故云:“切以诵经者,所以明心见性;礼忏者,所以革旧鼎新,此僧家遵行久矣……余以为非痛加忏悔,则诵念为虚文;非专精念诵,则礼忏为徒说。故此二事,僧所兼修。” 这种建立僧人礼度的工作,曾得到莲池大师的赞美,《竹窗随笔》谓:“其所立遗约,训诲徒众者,皆教以苦行清修,深居而简出,为僧者当法也。” 李贽这位被视为破弃礼法者,事实上正是以能建立僧徒之礼法而获得佛教界之敬重的。 要从这些线索上看,我们才能了解李贽为何要评《水浒传》,为何又称此为《忠义水浒传》。 照一般的看法,《水浒传》自然是描写魔君出世造反的小说,李贽却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充分肯定了梁山英雄们“忠于君、义于友”的精神,认为宋江是忠义之首,他们“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因此并非犯上作乱之人。他特别在《水浒传》名称上加冠“忠义”二字,即为阐明此一观点。 推此义例,他论〈拜月亭〉,是表彰该杂剧:“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兰比雀重名,犹为闲雅,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终始不相背负,可谓贞正之极矣。” 论〈西厢〉,则谓:“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 他最推崇的这三部小说戏曲,无一例外地都由君臣朋友、忠孝节义这个角度去诠释,难道还不能显示李贽对礼法的重视吗? 就是因为他十分重视礼,所以他常批评当时一般人讲礼都不通透。不通透的原因有二,一是执泥古礼,二是只以外在的律法条约为礼。 执泥古礼之病,是太执着。为了破除这种执着,他讲了许多破执的话,强调:“圣人之言,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 结果这些话,竟被现今讲明代思想史者拿出来做为李贽“非圣无法”之证据。真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 至于反对只以外在的约束规条为礼,李贽的讲法是: 今之言政刑德礼者,似未得礼意,依旧说在政教上去了,安能使民格心从化?彼盖但知礼之为中、齐之为齐……夫天下至大也,万民至众也,物之不齐又物之情也,若一一而约束之整齐之,非但日亦不给,依旧是走在政教上去矣。彼政教之所以不能使民格心归化者,正以条约之密,无非使其就吾之条理而约给于中,齐其不齐,而使之无大过不及之病也。是欲强天下使从己,驱天下使从礼。人自苦难而弗从,始不得不用刑以威之耳。是政与刑自是一套,俗吏之所为也,非导之以德者之事也。 此显然是发挥孔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理论。认为当时讲礼的人,其实仍只停留在政刑的层次,是俗吏之学,其所谓礼,其实非礼。 这种区分,和焦竑是一样的,批判那种外在化、形式化、以人为规定的条理规约来规范各个不同的个体生命的做法,而呼吁重建一种合乎礼意、能使民格心归化,又不往政教方面走的礼。 这样论礼,自然也就内在化,转向心性论的路上走了。 在各个不同的个体生命处论礼,有关礼之讨论,便转入有关个体良知的讨论,〈童心说〉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此。所谓童心,李贽说: 童心者,绝假纯真,最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 谓人放失本心而要我们“求放心”,是从孟子开始,儒家就一直强调的事,李贽之说亦属此类。但他以“童心”形容本心,则是受了罗近溪“赤子良心”说的影响。谓人童心之所以丧失,是因以闻见道理为主,更与焦竑所称“礼者,心之体。我有此礼而已,见生焉则歧”相似。 何以见得?李贽〈四勿说略〉言: 由中而出者,谓之礼。从外而入者,谓之非礼。从天降者,谓之礼;从人得者,谓之非礼。由不学不虑不思不勉不识不知而至者谓之礼,由耳目闻见心思测度前言往行,仿佛比拟而至者,称之非礼。 此乃转外在之礼法、礼文、礼仪、礼教为内在的本心童心也。 其理论之重要性在此,但局限也在此。 张载《正蒙》曾批评:“人病其以耳目见闻累其心,而不务尽其心。”李贽之说不免此病。反覆强调勿以道理闻见障蔽童心,却未从尽心、发扬本心明觉功能方面去申论。 他所推崇的泰州学派先辈,如王心斋就曾说道:“良知既觉,私欲便除。”本心良知自身的明觉性,是可以转识成智、转成心为道心的。李贽于此,却未发挥。 反之,闻见道理,也未必只有障蔽本心的功能,像王船山就说:“多闻而择,多见而识,乃以启发其心思而会归于一,又非徒恃存神而置格物穷理之学也。”“见闻不足以累其心,而适为护心之助。”(《正蒙注》卷四)李贽对此,亦甚少辨析。 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关怀重点,并不在良知的性质或良知与闻见之知的分际及关系,而在于礼的内在性。故对于上述诸问题,均未暇思考。 三、转识成智:是要去人欲,不是发挥欲望 强调礼,并以心即礼的方式讲克己复礼,焦竑与李贽虽然论点未尽一致,但大体是相同的。他们所显示的这种论礼方式,事实上也是他们一批同志好友共同的主张,如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就很能证明这一点。 袁宗道认为:“礼,即是克己复礼之礼。不知礼,即浑是人欲之私,其身颓然屈于万物之下而颠仆矣,故曰:『不知礼,无以立。』”(卷十七〈读大学〉)他不是肯定人欲,而是要祛除人欲;但又非存天理以去人欲,乃是以心即礼的方式,克己复礼地祛除私欲。 此等言论,显见其工夫所在,即在于克除人欲。 因此对阳明后学之流于狂禅一派,殊不以为然。焦竑〈刻传习录序〉明言:“国朝理学,开于阳明先生。当时法席盛行,海内谈学者,无不禀为模楷。至今称有闻着,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没,传者寝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实际未诣;或以放旷自恣,而检柙不修。”(《澹园集》卷十四) 这些,都可以看出“克己复礼”一事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它成为整个工夫论的重心,也是很自然的。 但彼之克己复礼,实与其他人不同。不同处,一是礼的性质,他们都以礼为心性;一是克己的方法,是要以不消灭人欲的方式去克除人欲。这两者,都可以在《白苏斋类集》中找到文证。 袁宗道说:“仁、义、礼、智,性之德也。圣门单提一字,即全该性体。如复礼之礼、不违仁之仁、义之与比之义是矣。”因此,礼就是性,不是外在之物。而且“礼即是仁,仁即是礼,以其为天然之则,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