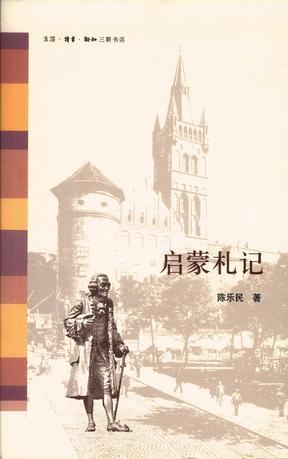 读到陈乐民先生这句“思想家的影子可以拖得很长很长”,一时感动得怔住了,它像一行很美的诗句,不,它本身就是一首小诗了,令人吟诵良久。 在万圣书园看到陈先生的这本《启蒙札记》(三联书店,2009年10月),差点“哎呀”一声叫出来,仿佛心中某个隐藏的秘密被揭穿。陈先生在书中论及的18世纪,虽然其社会、政治领域仍为黑暗所笼罩,孔多塞形容为“政治暴政”与“宗教暴政”的年代,但是在思想方面,却是最富有生长性、也是最有魅力的时期。 所谓现代性更意味着一种“现代心智”,它意味着怀疑、理性、批判和驳诘,意味着朝向现实而非经院的知识态度,并天生伴随着一种挑战权威的精神。后人可以对当年的“启蒙运动”说三道四,而这一点恰恰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永不满足,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歇步。 陈乐民先生比较了四位启蒙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他说自己最喜欢伏尔泰,因为“伏尔泰最有人性,也最理性”。而且尽管“伏尔泰一生经历不少坎坷,但他的性格却是欢快的、活泼的”。我一见陈先生喜欢伏尔泰,就喜欢陈先生了。可惜始终没能当面向陈先生有所请教。这样的机会永远失去了。 可是我也喜欢狄德罗,因为狄德罗最淘气,对自身人性的幽暗处了解最深。伏尔泰说“自然法就是令我们感到公正的本能”,“这种自然法既不整人,也不是拿别人来取乐”。狄德罗谨守了这两点,他只是喜欢拿自己来取乐。将自己一分为二之后,他写出了《拉摩的侄儿》这本也是活泼欢快的小书,堪与伏尔泰的《老实人》媲美。 陈先生这样形容狄德罗:“狄德罗的脑子像一群晚餐会上聚会的人在吵吵嚷嚷,你一言我一语谈笑风生。”这使得我更加热爱狄德罗了。 陈先生稍前出版的那本《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陈乐民、史傅德对话,晨枫编译,三联书店,2009年1月),其中有关公民社会的话题,也是令人深感兴趣的。陈先生试图强调,公民社会的诞生,并非朝向一个新的理想国,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在欧洲历史上便是如此。陈先生提供的历史维度,对当今实践者,极富启发意义。 伏尔泰开创的“理性”与“人性”的传统,被不同人们继承下来。不同的人们分享了伏尔泰精神资源的不同方面,或者让这两部分得到不同的新组合。 《欧洲精神——围绕切斯拉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范炜炜、戴巧、翁珊珊、吴幼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8月)一书中提到的作家和思想家,如诗人米沃什、哲学家扬·帕托切克、小说家米兰·昆德拉和伊万·克里玛、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以及政治学家伊斯特万·毕波,主要生活在20世纪东欧这个地区,在上个世纪纳粹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的多重灾难中,这些人们发展出某些独特的人道主义传统,其重心是对人类尊严的维护。 诗人米沃什曾经形容自己为“一出道德剧的罪人”。比起他内心生活的紧张压力,他外部生活的起伏跌宕几乎算不了什么。早年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其精神底色是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但是后来深陷的现实,却一再让他卷进相反方向的思考,即对于民族、同胞及善恶的思索。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