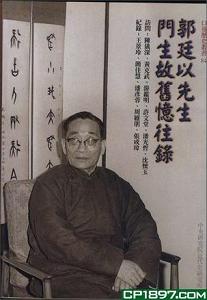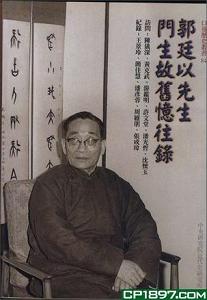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 “给我们谈谈……1830年代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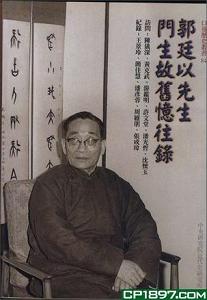
李公明
“给我们谈谈1830年代吧 / 那电光闪闪的时代 / 谈谈它的战斗,它的热力……”泰奥多·德·班维尔的这几句诗可以成为所有激进思想史回忆录的永恒主题。在我们的精神成长史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就是这类主题中影响巨深的著作,它既是大革命的余焰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心灵中燃烧的明证,同时也成为了后来各类所有曾在威权专制下挣扎、抗争的“青春之歌”的回忆原型。
读郑鸿生的《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12月),不仅对于过去仅略有所知的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校园民主抗争、保钓运动等有了更多感性的认知,对于台湾左翼思想的脉络、暗潮和历史的吊诡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时更产生了对于“谈谈1830年代”这类“青春之歌”的反思。作为书中记述的主要人物的钱永祥教授为该书撰写了《跋:青春歌声里的低调》,以十分严肃、冷静的心态分析了在该书的记忆叙事中潜藏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反对”这个概念,他说不能容忍这个概念的庸俗化,因此必须在威权与反威权的框架之外更要追问价值理想的问题,要追问反对者的价值理想的内核是否更能使人具有做人的尊严、反对者的价值理想是否能在反对的行动中得到深化、扩展和取得认同。他继而深刻地揭示了台湾社会思想价值环境的“贫瘠破碎”:保守者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知识分子仅以符号式的反威权自恃、被压迫的草根被迫求助于各种反现代导向的族群主义。由于价值意识的贫乏、扁平化,“反对”沦为“取而代之”、民主变为政治动员的操作术。因此之故,宪政原则、社会整合、公共政策等等问题难以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展开公共讨论。钱教授说,往者已矣,新一代仍以“反对”为念的人应该三思关于价值意识的问题:“自己的承诺究竟何在?”(第311-315页)又比如,他指出应该把“反对”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从而使事件与思想相互撞击、发酵的实际情由和可能具有的丰富性得以呈现。更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对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形象的分析:屠格涅夫对于“反对”作为实践模式的矛盾和游移,而“我们”时而坚信、时而虚无彷徨的命运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思想局面所决定的;这种命运“注定既不快乐、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到今天,这个局面仍未改变,并且看起来也不会改变”(第322页)。
掩卷之后,犹有几个问题无法释怀。首先是对广义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遗产,实有一些基本分野。萨科齐在当选法国总统后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可以认为,“抹除”六十年代的精神遗产是一类有普遍性的威权心态和意志表述,无非证明了六十年代精神遗产仍有其尖锐的、挑战性的品格。而对于像西德尼·塔罗、莫里斯·迪克斯坦以及所有《青春之歌》的作者来说,无论如何批判地反思,“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 迪克斯坦语)。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幸存”不是符号象征的光环或怀旧,而是思想与学术事业的结合。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这些主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一直是当代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与青年造反运动的联系显而易见。其次,关于“遗忘”。朱尔·米什莱在写作《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正痛苦地目睹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悲剧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但他声称自己仍然相信大革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把“遗忘”作为比死亡更可怕的性质,用以描述那个专制的时代。于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站出来说: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人和事不会被遗忘。……连空气都不会被遗忘。还有,关于“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的命运可以回到赫尔岑那里得到理解:他说文学、艺术与历史使我们看清楚了这个荒唐的环境、侮辱人的风习和畸形的权力社会,我们对这种生活既不可能适应,也不愿意和它搏斗而被毁灭。这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说话:要离开还太早;因为看来在死魂灵的背后,也还有活的灵魂”(《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第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5月)。那么,重新谈论 “1830年代”就是命运的安排和使命。
为了反抗“遗忘”,文献档案与口述历史资料的相互参证有重大意义。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相继进行了“口述历史访问计划”的工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保留了一批涉及政治、军事、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史料。当初这项工作是由近代所筹办主任(后任首任所长)、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宗师郭廷以先生拟定推行,他自己无法料到的是,在他辞世近三十年后,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组完成了对其门生故旧的口述资料整理工作,出版了这本“口述历史丛书”之八十四《郭廷以门生故旧忆往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年4月)。该书收录了郭先生门生故旧的二十二篇访问记录及六篇回忆录,以大体论,所录者不外是对郭氏学术风范、成就及筚路蓝缕之艰辛的追述,以及学生门人在郭师引领下进入学术生涯的历程。但从细处看,这些访录还记述了不少因门户歧见而导致的人事恩怨、借国际冷战氛围而产生的告密诬陷,以及官僚政治干预学术等史实。诚如多位访谈者所言,近代史所自筹创之际便充满着各种或明或暗的忧患,其间郭廷以先生更是经受了不少的冤屈和打击。而近代史所仍能在“内忧外患”中坚守学术之职、取得国际瞩目的成就,实与郭先生的坚韧努力和学术卓见不可分割。陈永发教授为该书作的“序”中认为,“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同时经受得起特务政治和检举文化的折腾,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所言甚是,这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在两岸所经历的共同景况和愿景。
与这部口述历史关系甚密的是张朋园先生著的《郭廷以 费正清 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7年5月)。张是郭的重要门生,在上述《忆往录》也收有他很平实、客观的访谈,而该书所论自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也是台湾史学发展的重要节点。余英时先生为该书作的序更把郭、费、韦三位以学术为道而超越了各自的政治、团体利益视作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关键,可见此段个案研究的深意。
(责任编辑:admin) |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