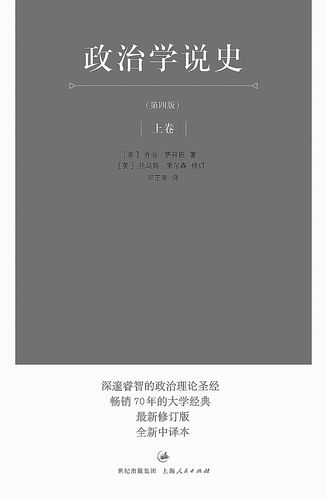 《政治学说史》一书是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的名著,初版于1937年问世,后经三次重版,由索尔森(Thomas Landon Thorson)于1973年修订。此书被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列为政治学教科书或必读参考书,享有盛誉;中译本自上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在我国政治学研究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次翻译是根据1973年修订版译出的全新中文本,在学术规范等诸多方面较之旧译本均有提高。 萨拜因写作本书的视角是休谟式的,亦即赞同休谟对自然法理论的批判所作的结论。休谟从经验论出发,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他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观的知识和数学与逻辑的知识;另一类是从经验推理中得到的知识。休谟认为前类知识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但后类知识并非如此。因为当两个事实或事件具有因果关系时,人们能够真正认识的只是它们确实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规律性一起发生。除了实际发现它们一起发生的经验外,不可能由一个事实推出另一个事实。所以,因果关系间存在的只是经验上的相互关联,来源于人们的习俗,同数学或演绎推理有根本区别。所以,要严格区分在这两种情形中的理性。 但是,人们也通常把理性运用于人类行为。自然法理论声称存在着能够被证明是必然的和无法规避的理性原则,从中可推出有关公正或自由的自然权利体系。但休谟认为,在这些场合,主张某一行为是好的或善的,不过是人们的愿望或意向。理性只是指明用何种手段达到合意的目的;至于结果本身是否为人所接受,是无法用理性衡量的,无所谓合理与否。这就是休谟对事实与价值所作的划分。所以,在休谟看来,旨在表明任何事物必然存在的理性形而上学是不能成立的。公正、自由、权利等这些价值观念来源于人们的习俗。这些习俗的根据在于通过它们,人们可形成多少带有稳定性的行为规则,从而给人们行为带来预期。这些观念与规则在人们生活的经验中证明自己,如果它们给人们带来了过多的不便,人们会对它加以改变。所以,休谟把观念和规则的有效性论证归结于功利,亦即它们是使人们适应环境、带来便利的手段,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萨拜因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写作本书。总体而言,他把政治学说看做政治的组成部分,是作为政治本身在其中生存的环境的正常部分而产生。政治思想是同各种体制、政府机构及其所涉及到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种种压力一道演进的。换言之,没有亘古不变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人们应付环境压力的产物,随着特定时空的政治经验、政治过程而演化。所以,从全面上看,很难说某一政治理论是正确的,或许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政治理论中对事实的判断或对趋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萨拜因这一总体性的立场贯穿于整部著作中。例如,他在对古代希腊政治思想的考察时,指出希腊人要在人类环境的无穷限制和变化中追求永恒,从而使人类生活达致相当合理的境界,这一点使得希腊政治哲学要追求变化中的不变和多样性中的统一;在现代考察列宁政治理论时,从俄国当时落后,农民占多数而无产阶级弱小这一情景出发,指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民主成分的抛弃,对党组织理论的发展,都紧紧贯穿了上述立场。 但萨拜因的立场其实并没有得到彻底地贯彻,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政治思想的评价上。因为如果真的把政治思想看作历史环境压力的反映,认为没有一种不变的正确的政治理论,那么他就不能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评价为非理性的,也不能说共产主义在道德上比民族社会主义处在更高水平上之类的话。其实萨拜因受制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承认他认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被信奉的自由主义价值——自由与平等。 修订者索尔森也持同休谟和萨拜因一样的立场。总体而言,修订是对原书的增补、继续和发挥,而不是对其原旨和内容作实质性的改动。 本书考察从古希腊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思想史,气势恢宏,是一部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史诗性经典巨著,非常值得一读。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