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莉,笔名乐颜。文学博士,青年学者。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中国现当代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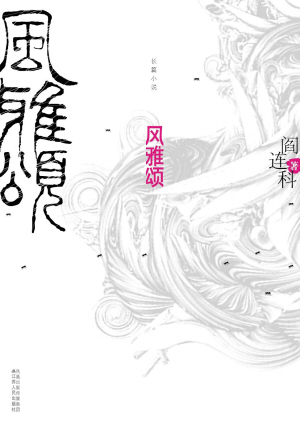
阎连科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8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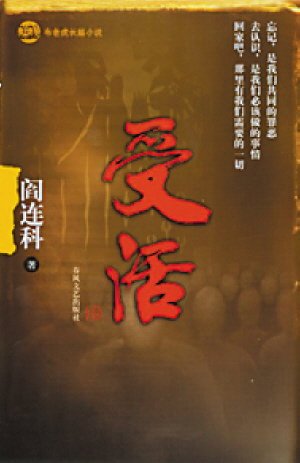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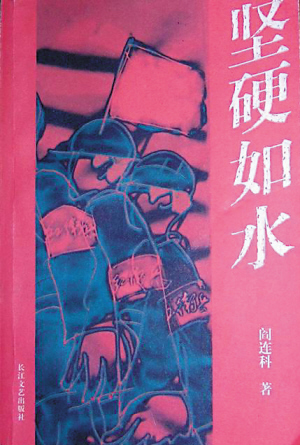

如果你问我,《风雅颂》是一部失败之书吗?我没有办法回答。正如你问我这是否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我也无从回答一样。如果把这部小说的作者换另成一个不出名的小说家,大部分读者和批评家大约都会称赞作者的勇敢和创新。而当你一旦意识到这是写出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等一系列优秀作品的阎连科时,又不能不坦率地说,《风雅颂》差强人意,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一个小说家的冒险尝试,一次“向死而生”。
我相信,任何一个当代文学的爱好者,都无法抵挡住阅读《风雅颂》的冲动。阅读期待是有力量的——当一位小说家的盛名累积到一定高度,一种无法触摸的情绪便会深深进入读者们的阅读情绪——他们渴望小说家给你一次惊艳,犹如我们希冀刘翔每次比赛都打破世界纪录一般。
老实说,《风雅颂》中叫杨科的当代高校知识分子带给我巨大困扰。他身上有那么多高级知识分子的符号:《诗经》研究专家,著名高校的学者,在讲堂上夸夸其谈的师者。但是,阅读这部小说时,我却时时忘记他的这些身份。我觉得他就是个识字者——百无一用的书生。人物的形象是那么的不清晰,不明确(事实上这种不明确也是整部小说的基调)。他性格暧昧,模糊,含混,模棱两可,他软弱,左摇右晃,没血性,没骨头,没担当,可怜,可憎,可恨(也许还有那么一些可爱)。他和他的《诗经》研究一样,是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多余者”,他的课不受学生喜欢,但却受到疯人院的追捧。他在清燕大学受到排挤,但在乡下却被人尊为教授和大人物。杨科在两种甚至多种语境中离奇地生存。他被老婆背叛,自己也毫无忠贞可言——一切价值判断在他的身上都被消解,一切有力量和有逻辑的东西在这里也变得灰色。读者随着他就那样无所事事地游荡着——我们来到清燕大学的红砖文科小院里,我们来到他的家乡遇到他当年的初恋伏珍,我们和他一起游走在天堂街,看着他与年轻的“姑娘们”一起相处,和青年学生一起抗击沙尘暴,看着他被人踢出学校。杨科经历的一切,既是现实的,又是荒诞的。
小说有些段落让人记忆深刻。杨科回到家乡后,很多孩子的父母要求他摸小孩子的头——这么大的教授摸了孩子的头,孩子一定会聪明。此细节有着复杂的意蕴:你会意识到乡村对于以“知识”代表的权力的渴望——但那是对贫穷的畏惧,而不是对知识的真正尊重。可是,当你意识到这个被仰望者其实是被皇城根大学“休掉”、被当作疯子隔离、被老婆戴了绿帽子的男人时,那一切又是何等的嘲讽和荒诞。杨科在天堂街和很多个姑娘“一起”——没有人能想象这是一个研究诗经的专家在做的事情,这看起来是多么的淫乱和令人难以忍受啊,可这个细节却不让你觉得肮脏而感受到莫名其妙的“厌世”情节和对身体的厌弃。
当然,最令人难忘的细节是杨科把自己的衣服和伏珍一起合葬:杨科看着另一个杨科死去。这细节打动我,不是因为那么多的蝴蝶飞起,而是小说里的“我”看着“杨科”死去。阎连科令人感触地传达他想传达的情绪:这是一个中年男人对死亡的“向往”与“恐惧”。这是一次精神上的死亡与新生,这也是小说家在隐喻层面上的再出发——杨科身上带有浓厚的“无家可归”的痕迹,这恐怕是当代识字者共同的命运,有如一个无根的人渴望大地但又永远找不到家园一样,他们“恓惶”,“软弱”,无可奈何。叙述人对生命的热爱与厌弃,对人的存在的种种纠结,以及凝结在他内心深处的种种荒凉与无可依傍,读者应该都能体会。老实说,小说家为此部小说付出了种种艰辛的努力,他裸露内心勇于和自我反省的精神使我颇为感慨。
作为阎连科多年的读者,我也想坦率指出小说的缺憾。小说以“风雅颂”为题别具深意——小说家试图以杨科研究的《诗经》的世界与杨科生存的现实世界相对照进行某种“互文”。的确,以《诗经》为代表的与民间的、性灵的、无拘无束和自在张扬的生命力也足可以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一种强大的、充满想象力和魅惑力的想象背景。但是,小说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一次汪洋恣肆的想象力的释放。《诗经》没有能完成它在文本中应该有的力量和某种话语指代。作为《诗经》的研究者,杨科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中,没有体现出一位执着的《诗经》研究者与一位普通的古典文学学者(或一位普通的文科教授)的区别。读者不能体会到《诗经》的研读岁月给予他血液中的影响。我的意思是,小说家借用的小说人物的身份的不可信,成为了读者阅读小说的最大障碍。
另外,以《诗经》中的诗句作为标题或引别具想象,但问题是这些诗句没有能如“水”一样浸入整个小说成为其内在的肌理。作为《风雅颂》的标题和作为《诗经》的背景——小说内在精神支撑和新的形式的探索间的没有“和谐相处”。形式与内容的“表里不一”最终使小说失去了某种该有的神性与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