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中国传媒大学于根元教授于2019年8月22日因病逝世。 于根元先生1940年8月10日出生于上海市,祖籍江苏省泰兴市。1963年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语文》杂志编辑部做编辑和研究工作。1984年到新建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曾任副所长、《语言文字应用》杂志主编。1998 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做教学和研究工作,生前任中国传媒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语言传播研究所所长。还任中国应用语言学会(筹)常务理事。 于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语言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编了《应用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应用语言学史纲》等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 先生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中国当代作家作品语言、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新词新语、广告语言、网络语言研究,是我国最早研究语言生活的专家之一。近十几年来致力于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的建设,发展了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发展了“交际到位的程度——交际值是衡量语言规范的重要原则”和“语言内核外层互补”等学说。 本刊为纪念于根元先生,特转发于先生刊登在《语文建设》1989年第6期的文章《留心各种语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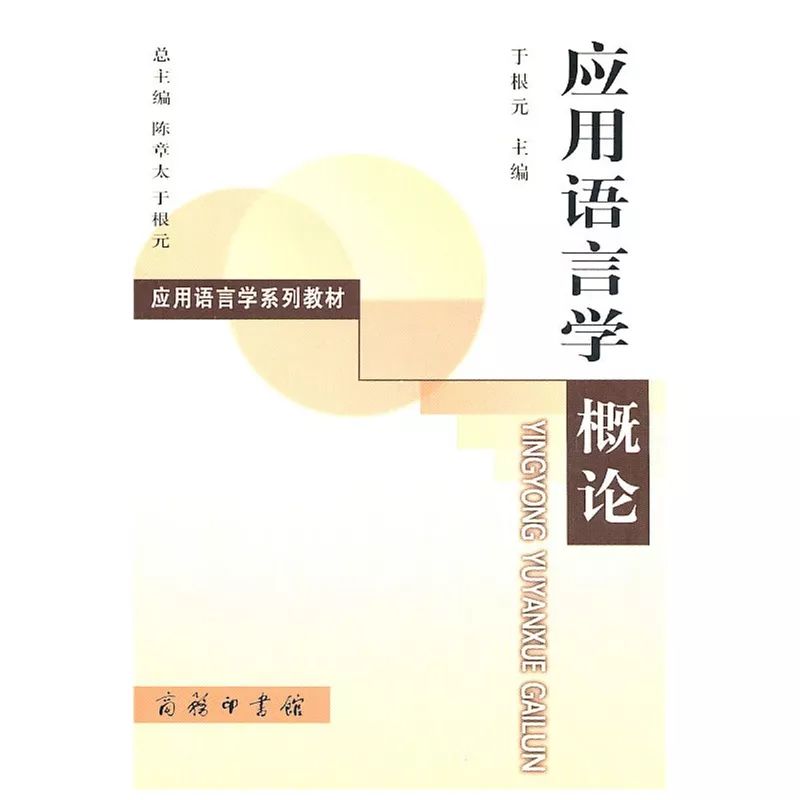 应用语言学概论  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 留心各种语言现象 于根元 一 留心不妥的语句。 语文评改、词语评改,视野要开阔一些。不要老是在成份残缺、搭配不当、褒贬不当一些方面做文章。 《中国语文》丛书《词语评改五百例》(语文出版社,1984),把性质大体相近的篇目归纳了一下,分为十三类:用词,指代,虚词,词语搭配,句式,成分,语序,事理,修辞,汉字,标点,杂例,编校。够多了吧?可是编者在《后记》里写道:“从篇目可以看出,这本集子并没有全面涉及现代汉语使用的各种问题,它仅仅提供了在实际使用中几个方面的部分材料。”十三类之内小类不全,十三类之外还有类。 编《词语评改五百例》我也参加了。我们总觉得有新意的开拓一个新的方面的稿子太少。作者也觉得这种稿子难写。恐怕也是因为我们对一些不妥的话不够敏感,甚至长期以来以为是对的。一些文学作品里评了些不妥的话,我读了之后感到很新鲜。我就想:我怎么就没有发觉这些话不妥呢? 例如史铁生《山顶上的传说》里说:“后来那个记者找了他,可他一听什么’身残志不残’一类的话就够够的了。人都不应该志残,和人都应该吃饭一样,与身残没有任何联系。”(《十月》1984年第4期117页)我觉得,这就是史铁生本人的话。我们不老是跟着说什么“身残志不残”吗,这话成了套套,一张口就来,没有想过它对不对,实际上是不了解广大残疾人的心,伤了他们的心。 再如《我们是同行》里说,公交公司一位男同志乘电车吃瓜子,女售票员指责他,说“在电车上不许吃带皮的食物”。一一侯宝林相声《夜行记》里谈过,公共汽车上不许吃糖炒栗子,看来这个规矩早已有之。相声里逗哏认为这个规矩不妥,不过他是个不守规矩最后自食其果的挨批评挨嘲笑的人物,捧哏赞成这个规矩,逗哏也没有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反驳。这个相声说了几十年,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我没有听到谁对相声里这一段有微词的,我也没有。女售票员指责男的,男的开玩笑不承认吃了。女的过去检查:地上没有壳,附近窗户关着。原来男的把壳放在自己口袋里了。男的接着评论开了:“‘在电车上不许吃带皮的食物’,好吓人的口气!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而荒谬的。难道乘客都是受管制的犯人吗?你应该改成:‘不许往车上扔果皮和脏物’,是‘扔’而不是‘吃’,这才对哪!”(崔亚斌《我们是同行》,《当代》1983年第5期46页)男的这段“语文评论”语气尖刻了些,但有道理。 上面说的大体上是生活里的社会上的用语。报刊杂志和书上的不妥的话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理由的《骄子》里写道:“若要写出在这同一时刻处在不同位置的所有的人们,即令有一支如椽大笔,也难以尽述。”(《十月》1985年第1期51页)有了“如椽大笔”也“难以尽述”,意思是现在没有,更没有办法。那么有了总比没有好一些了?其实有了又有什么帮助呢?如果写得大,有了“如椽大笔”是有用的,现在是“要写出在这同一时刻处在不同位置的所有的人们”,需要的是许多手许多笔,要“如椽大笔”干什么?扯不上!还如:“‘扑隆’一声,惊飞了屋顶上的麻雀,空旷的车间里寂然无声,唯有蜘蛛还在八卦阵中做着它的梦。”(李荣德、王学彦《铸造神剑的人们》,《当代》1985年第6期61页)蜘蛛做梦,出声了没有?没有——大概醒着也不出什么声。老大一个车间“寂然无声”,蜘蛛也“无声”,单独把蜘蛛提出来干什么,这个“唯有”从何谈起呢? 《中国语文》上的“语文评改”文章,要求评大报刊杂志的,大手笔的。因为低层次的毛病太多,评改的价值小。评高层次的,影响大,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评得好,说得清楚,要进行一番研究。“语文评改”有时被人视作雕虫小技,一个原因是不少评改就事论事,太浅,有的只是简单地套几个帽子。其实,举一反三,找出规律,提出新见,有的甚至可以写成论文。如是,语文评改也是做学问入门的一座门。 二 还要留心常常被人说成不妥而实际上是很好的语句。 例如:“全村人都走了,你怎么还没走”“池塘边上种满了树,只留了一个通道”一类,常常被当作病句来叫人评改。很好的工具被指责成坏东西,不许人们使用它,这本来就很可惜了,还教育人们厌恶它,教育人们说出为什么厌恶的,这就把人们——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脑子搅胡涂了。有时候有人会愤愤然:这些话人们都说,大作家也说,教科书上也有,意思挺清楚的,而要我们来修改,说是语法书上写了这是病句,这个语法太……。此外,说这种句子可以用,因为习惯如此,或者是不合逻辑但合语法,似乎也不太能说服人。“习惯如此,不合逻辑但合语法”用多了,很可能成了“说不明白”的防空洞。 其实汉语的全称里常常可以少掉一些什么的。例如:“我们全家去车站接我爸爸。”请问,“爸爸”算不算“全家”里的一员?再从“全都……包括……”格式来看,“我们大家包括我都要吸取这个教训”,这里“大家”不也少掉个“我”吗?此外,怎么算“满”了?“池塘边上”再种上一棵两棵树还种得下吗?总是种得下的。“满街的人,满脸皱纹”,都没有“满”到顶点。那是一种小夸张而已。 近来看到一个地方说下面这些话有毛病:“站满了这么多人”“办公室挤满了四十多个人”“南边那块地盖齐了十几排房子”。作者的结论大概还可以商榷,但是作者留心到了这些语言现象,向大家提出了这些值得深入研究的语言现象。近来一则广告,说一种新农药“包括已经使用和没有使用速灭杀丁的都可以使用”,是否也值得注意和研究。 三 留心各种新鲜的用法。 《词语评改五百例》“后记”说:“少数几篇是谈正面用例,分析了某些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当时,我们很希望多得到一些谈正面用例的稿子,但是未能如愿。留心正面用例——各种新鲜的用法,似乎更要费神:一要知道过去大体的用法,才能知道这些可能是新的用法;二要知道这些新用法是规范的,是好的,而不是少数人生造的;三是新用法往往是刚冒出来的,用得少,人们研究得少,要分析出个道道来也就困难一些。不过,我们可以先把这些新用法记下来,至于研究,有的可以暂时不论,有的可以先少评几句。 新鲜的用法还是不少的。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说,小孩子的手让锤子打破了,有人还叫他干活,小石匠说:“你让他瘸着只手到队里去干什么?”(《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185页)人们往往把跛腿说成瘸腿,这里说“瘸着只手”很新鲜,而且好像很难换成更好的说法。又如有的事过去了,不值得提了,可以说成“不足挂齿”,“陈谷子烂芝麻,不提了”,当然还可以说成别的。潘军《篱笆镇》里又提供了一种说法:“那事馊了,不提了。”(《中国》1986年第3期55页)一般说饭菜馊了,还有把身上有了一股汗味说成“身上馊了”的。这里说事馊了,意为时间长了,发霉了,长毛了,变味了,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的说法。还如,有说目光在人身上“挖”的“盯”的“扫”的“烧”的,孙见喜《自然铜》说:“眼梢儿在我脸上一舔一舔地”(《中国》1985年第6期28页)。还如说某人“嗓门比裤腰还粗”(左泓《月亮》,《当代》1988年第2期135页);说某人年岁大了“头发‘下放’当了胡子”(戴厚英《高的是秫秫,矮的是芝麻》,《中篇小说选刊》1982年第4期112页);说不把人放在眼里,放在哪里呢?“放在鼻孔里(出气)”(高晓声《糊涂》,《花城》1983年第4期15页)。还如下面几例: “六毛钱半斤?你定的价?你还的价?” “都这么卖。” “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都是都,我是我。”(桑恒昌《半斤花生仁》,《人民文学》1982年第7期110页) 来拜年的好应付,况且如今自己已经结束了公职,是个“员外”,不会再有人来请示他、求他、磨蹭他。(李占恒《元旦那天——春节这天》,《莽原》1984年第2期88页) 你这个大记者,写的什么新闻,我先闻闻。(高禄堂《山水人物》,《柳泉》1983年第2期38页) 梦佛娇嗔地啐道,咯咯笑起来。那笑声丢进锅里,能熬糖。(熊尚志《雾霭里的明珠》,《清明》1984年第4期7页) 其实不是我挤对他们,这帮年轻大夫有几个顶事儿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一群“对付”!(徐小斌《河两岸是生命之树》,《收获》1983年第5期6页) 口语里也不乏精采的用语,近些年来“满脸的旧社会”一说便脍炙人口。去年,朋友间比年长,甲头发白了,人们说年长,乙头发黑,实际年长,人们却不认为他年长,乙说“我蒙了不白之冤”,满座大笑。我屡次为人说及此事,听者无不拍案叫绝。还如,几个月前,春天,乍暖还寒,街上,一阵寒风过来,年轻的母亲责怪衣着漂亮而嫌单薄的女儿说:“今天可真是美丽动(冻)人了。”后来一打听,北京年轻人几乎都会这么说。 四 培养语感,留心各种语言现象,收集研究,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便可以对某个领域的问题作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个人的体会是,平时觉得有意思的材料,赶紧记下来。有的材料反复出现,显示出了内在的某些规律,可以根据材料多少和心得多少作文了。有的材料只有一两例,可能又过多少年才又来几例,这就要耐心等待。作文时对材料要筛选,所以备料要多。有时候多也不一定管用,有了跟文眼有关的材料才能写,有了跟开头、结尾或者过渡有关的材料,才好写。有时找一些语言材料相当难,可是文章写好了,甚至寄出去了,再读书,一看这类的语言材料怎么这样多啊!后来一想,这是因为写了文章,经过了一番思考,语感强了。后来,我为了避免许多好材料用不上,于是注意写札记,写一组里的某些篇小文章,把它作为写较大的成品的中间阶段,既加强了语感,成果还没有最后完成,发现新材料还用得上。 有的小文章一开始不一定是有了成组的计划了才写的,而是写了几篇之后才有了成组的计划。我给上海《汉语拼音小报》写了《滥用方言的轻重》和《小说里如何注释方言》之后,觉得材料和认识可以谈一个更大的问题,于是后来写了《文学作品的方言使用》。又如,关于问话和答话,我1982年同陈章太合作了《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小册子,不久把其中一段写成《礼貌和答话》给了《语文学习》。1984年夏天,在《汉语学习》编辑部办的一个讲习班上讲了“问答琐议”,年底写了一篇《反问句的性质和作用》发表在《中国语文》第6期上。两三年之后,才陆续写出跟问句、答句有关的《说“一面应答”》《说“怎么样”》《“布尔蒂尼不在”》《“用嘴讲!”》《“哪儿”和“干什么”》《问答链》《“那位说了——”》《给个没有》等。打算以后写个专门谈问话和答话的小册子。所以,各个阶段的留心各种语言现象,还是为在某个领域里比较系统的研究作谁备。 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收集材料的时间长,写起来倒不很费时间。平时积累材料,大体上也就是积累思想。材料差不多了,思想也差不多了,写,基本上是组织组织。有时候备了十个月的材料,不够一个月写的,而且是在有了十来年材料积累的情况之下。最好是平时、零星时间、次佳状态收集材料。备料备好了——包括部分预制件备好了,找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最佳状态下来写。 五 古代有人把材料比作小钱,把理论比作钱串子,于是开辟了钱跟绳子之争。其实,从这个比喻来说,不存在不串小钱的钱串子,也没有不在钱串子上的呈游离状态的小钱。钱跟钱也不一样,只有镜花缘里某个地方的人买橘子,才有的币不分。钱有金银铜之分,有大小之分。从钱,能推知是串在什么绳子上某个部位,这头是什么绳子,那头是什么绳子,还有上头、下头、前头、后头,还可以知道它的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是什么钱。绳子也有长短、粗细之分。从绳子,能推知是串什么钱的,它的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是什么样的绳子。从钱出发而论,是材料检验理论,材料中见理论、体现理论;从绳子出发而论,是理论结合材料。钱与绳子孰贵孰贱?我看无所谓贵贱,因为小钱有绳子串着,绳子上串着钱。这部分钱和钱串子,同那部分钱和钱串子,有小局部与大局部之分,有低层次与高层次之分,有纲部与目部之分。钱与绳子是不可分的,只是我们要认识它的各种关系,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小局部到大局部,由中观到微观,有一个学习和研究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从考察钱开始,而且找钱所花的时间比较多。具体到一个人,不妨某个阶段多考察钱,然后花一段时间多考察一下相关的绳子,然后再用进一步的网络意识来侧重考察钱,螺旋般前进。 我并不轻视语言学理论,有一段时间我花了许多精力在理论上。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我的注意力至今还侧重在理论上。这里侧重谈留心各种语言现象,就要说一下理论和材料不能偏废,不研究小钱也就无所谓研究理论,绳子大体上是钱与钱之间复杂关系的规律。此外,研究钱串子的人,研究到家了,一定熟知这段串子上的钱的情况,而且善于鉴别真伪,预测这里以后大概会少掉那个钱,增加什么钱。换句话说,对某些语言现象的敏感应该是对有关语言学理论知之甚多者的本领,而不是相反。 把一堆似乎杂乱无章的钱的关系讲清楚,甚至对这堆钱作些整理,让人们用好,或许是理论探索的重要的入门,也是宣传理论的有力的手段和成功的策略。 至于研究方法,这里不及详说。只是采用长期有生命力的归纳之共和比较法,需要比较多地占有材料。比较,要比较这些钱跟那些钱的大小质地色彩及排列等关系,自然离不开精细地鉴别各种语言现象的细微的同异的本领。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