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陈述的形式配置》是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理论的一篇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本维尼斯特明晰地阐释了关于陈述的定义、前提、特征以及其实现的框架结构的思考,并在文末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特别指出关于书面陈述中的复杂话语形式还有待作进一步地分析。本文即从此处入手,运用本维尼斯特的陈述和对话结构的理论,试图按照书面陈述中的陈述层面、陈述对象、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的不同来重新梳理小说中的对话结构,同时针对小说对话模式中陈述行为指示词“XX说”的缺省现象,运用本维尼斯特陈述理论中的“参照指涉”概念,来对小说叙事变革过程中叙事者逐渐隐身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关 键 词:本维尼斯特/陈述/小说中的对话结构 作者简介:张怡,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秉承索绪尔“语言作为话语进入行动”的主张,埃米尔·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在其两卷本《普通语言学问题》(1966年,1974年)中提出话语是“行动中的语言”这一重要论断,并在研究中更进一步将话语研究与陈述行为紧密结合,指出话语即“陈述的外现”,而陈述意味着从“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这一重要的事实。本氏认为,陈述是个体语言的实现过程,它使得说话者将语言的形式配置占为己有成为了可能,也使得语言和世界有了能产生关联的中介。换言之,即在陈述行为发生以前,语言只代表一种语言的可能性,只有凭借陈述行为,语言才可能在话语时位中成为现实。说话者一旦进入了陈述之中,便会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使受话者也进入陈述,最终构建起一种本维尼斯特称之为以“我:你”极性(le rapport je-tu)为基础的主体间交流,而由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关系,又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关于“陈述的形象框架”(cadre figuratif)的问题。①通过论文《陈述的形式配置》(L'appareil formel de l'énonciation),本维尼斯特针对陈述行为的定义、实现情境、形式特征及其得以实现的框架结构,进行了明晰的阐述。他强调陈述是以语言为工具的说话者的行为,是说话者依据自身需求发动语言的事实,简言之即“通过个体使用行为得以实现的语言的实际运用”。(Benveniste:80) 纵观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首先不同于其他语言学家,他将说话者这一陈述的必要条件的参数引入研究视野。本氏特别指出,对陈述行为的考量必须置于标志说话者与语言关系的语言特征之下,这一在日常使用中司空见惯的语言现象,恰恰在语言学理论研究领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陈述行为,“说话者将语言的形式配置占为己有,通过某些特定标志并借助某些辅助手段,来陈述自己作为说话者的立场。”(Benveniste:82)陈述行为一旦发起,说话者同时在其对面又树立起一个他者——不论后者是否在场,任何陈述行为都必定预设一个受话者。而在说话者动用和占用语言的过程中,语言一旦被用来表达与世界的某种关系,又势必引入“指涉参照”(la référence de l'énonciation)这一个体语言实现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陈述将说话者引入其语言,通过话语进行指涉,使每一个话语时位都构成一个内在的参照中心;另一方面,说话者和受话者双方为实现会话的语用协调,又存在着进行共同指涉的必要。因此,指涉参照与说话者、受话者三者同为陈述行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支配陈述行为的这一整套参照机制则主要由人称标记(我—你)、指示标记(这个、这里等)以及关于时间形式的表述聚合三类特定形式构成。不同于有完整恒定位置的语言实体,这部分语言的特定形式只源于陈述行为本身,并且只涉及说话者的此时此刻。由于它们的存在,说话者与其陈述之间才建立起某种恒定且必然的关系。 在陈述行为中,无论受话者是真实的抑或想象的,无论是以个体的形象出现还是以集体的形象出现,陈述行为的特征都强调了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的话语关系,即一种被称之为以“我:你”极性为基础的主体间交流。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关系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又引出关于陈述的形象框架(le cadre formel de la réalisation de l'énonciation)的问题。本氏指出,“作为话语形式,陈述设立了两个同样必不可免的‘形象’,一个是陈述的来源,另一个是陈述的目标。这就是对话结构(structure du dialogue)。两个形象处在交谈者的位置上,轮流充当陈述的主角。这个形象框架是随着陈述的定义而必然产生的。”(Benveniste:85)简言之,本氏认为陈述的形象框架即为对话结构;陈述外的对话抑或无对话的陈述都不可能存在。 至此在这一篇《陈述的形式配置》中,本维尼斯特试图在语言内部从陈述所实现的个体外现出发,去勾勒陈述的形式特征的目的已基本达成。然而在《陈述的形式配置》的文末,本氏又提出关于陈述理论的一个新问题,即区分口头陈述(l'énonciation parlée)和书面陈述(l'énonciattion écrite)的必要。因为“后者是在两个层面上运行的:作家通过写作来自我陈述,而在其作品内部,他又让一些个体进行自我陈述。”(Benveniste:88)他认为如果从其所勾勒的陈述形式框架出发,对复杂的话语形式的分析还大有可为。 因此,本论文将尝试从本维尼斯特在此处留下的开放式提问入手,运用其陈述理论与对话结构,尝试按照书面陈述中的陈述层面、陈述对象、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来重新梳理小说中的对话结构,同时并对小说写作叙事策略的变革进行思考。② 一、小说中不同对话结构下的陈述层面和陈述对象 正如本维尼斯特所指出,书面陈述存在两个层面,一是作家陈述的层面,另一是作品内部某些个体的陈述层面。在小说作品中,第一陈述层面即为作家写作陈述的过程,而第二层面则涵盖小说叙事者和人物的陈述过程。显然这两个层面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重合:许多带有自传色彩或是回忆录性质的小说,其内部作者、叙事者与人物三者的合一即体现了作者陈述与作品内部某些个体陈述层面的合二为一,例如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的自传体系列小说《位置》(La Place)与《一个女人》(Une Femme)中,作者即叙事者即主人公分别讲述了其父母一生的故事;而在克里斯蒂安·博班(Christian Bobin)的小说《生命之上》(La Plus que vive)中作者(同时也是叙事者和主人公)则回忆了他女友吉斯莲(Ghislaine)的一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一般的自传或回忆性质的小说,这部小说不是以读者作为“你”,而是以作者已故的女友为对话目标“你”的。 由此,便引出了小说中书面陈述的另一个特点,即陈述对象的多变。不同于口头陈述,拥有两个陈述层面的书面陈述,其陈述对象也存在某种多变性。在作者写作的陈述层面上,陈述一般以读者为陈述目标,即读者处于对话结构的另一端。而在书面陈述的另一层面—作品内部一些个体的自我陈述中,陈述对象的问题更为复杂。 首先,需要将这一问题,按陈述的来源进行区分,再按陈述对象的不同进行划分,如此可以得到叙事者向读者陈述、叙事者向人物陈述和人物向人物陈述、人物向叙事者陈述四大类陈述模式。其中叙事者向读者陈述可算是小说写作最经典的对话模式之一,同样人物向人物陈述也是小说组成的基础部分,只要人物间有言语的交流,那么小说中就必定会有人物向人物的陈述出现。至于叙事者向人物陈述和人物向叙事者陈述这两种陈述模式,其出现必须以一个条件为前提:即叙事者在小说中必须也是人物,否则两者会因不处于同一对话层面而无法对话。在以上四大类陈述中,无疑叙事者向读者陈述这一陈述模式在传统小说中占据了叙述的主导地位,而其它三类陈述皆可被嵌套包涵于其中。乔治·杜阿梅尔(Georges Duhamel)的《子夜的忏悔》(La Confession de minuit)以及普雷沃神父(L'abbé Prévost)的《玛侬·列斯戈》(Histoire du chevalier Des Grieux et de Manon Lescaut)便是同时包含这四类陈述的典型例子。《子夜的忏悔》中的主人公即叙事者萨拉万(Salavin),不断地以读者为陈述对象讲述自己的经历并进行自我的心理剖析,同时在他的陈述中又充满了他与其他人物的双向对话交流以及其他人物间的对话。《玛侬·列斯戈》的叙事者在旅途中遇到骑士德·格里厄(Des Grieux),后者向他讲述自己和玛侬·列斯戈(Manon Lescaut)的故事,在叙事者向读者陈述的过程中又包含人物德·格里厄骑士向叙事者做的陈述。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包括福楼拜、于斯曼、左拉等在内的一众颇具现代意识的小说家,他们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显现出对使用自由间接引语(discours indirect libre)的某种偏爱。而这一由自由间接引语在文本中产生的特殊美学效果,正源于陈述层面的某种暧昧不明。由于标志陈述行为的动词缺失,本应归于人物陈述层面的内容经转写后被直接置于叙事者或是作者陈述的层面。陈述边界的不确定与模糊,致使多层叙事声音在话语时位上产生交错。巴赫金在《小说话语》中提出“混合陈述”(énoncé hybride)的概念,认为混合陈述的话语“按照语法(句法)标志和组成标志,只属于一个说话者,但事实上却混杂着两种陈述、两种说话方式、两种风格、两种‘言语’”。③混合陈述在不同声音、不同陈述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句法形式或是结构形式上的界限,两者的分界甚至是有意识地被处理成扑朔迷离、摇摆不定的。杜克洛(O.Ducrot)在此基础上借用巴赫金的研究,针对陈述研究提出“复调”概念,④即在叙事者—说话者的话语内可能存在囊括两位陈述者(作为叙事者的陈述者和替人物发声的陈述者)的特殊现象,因此在小说陈述中,“简单过去时叙事与自由间接引语共存的复调现象并非不可能出现”。⑤显然两者谈论的问题关键最终都回归到陈述层面的问题上。正是小说书面的陈述层面间发生异常的混淆情况,才使得自由间接引语能够在小说陈述话语中制造出特殊的文体效果。 二、小说中对话结构的不同实现形式 上文利用陈述理论梳理了小说中不同对话结构的陈述层面和陈述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小说中对话这一陈述的形象框架,其实现形式却不只是我们日常所见的会话形式那么简单。诚然,常见的会话形式是小说中对话结构最常见的实现形式。但在这里,我们想将这种最普遍的形式放在一边,先来考察一下小说中那些不那么常见的对话实现形式,更准确地说,即小说中普通会话形式的某种变体——即日记体或书信体。 与普通的日常会话一样,日记和书信都属于陈述理论下的对话结构。书信体是对话结构的物质化形式,拉克洛(Laclos)的《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至于日记,不论写日记者的陈述对象是真实的存在,还是想象的产物,都不会改变日记体之下对话结构的实质。在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田园交响曲》(La Symphonie pastorale)中,牧师的日记看似没有明显的陈述对象,在写作时既没有日后公开的打算,也不以读者为陈述对象。但这并不能说明牧师的日记没有陈述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牧师是以自己为陈述对象的。他自己既是说话人,又是受话人。在陈述的过程中,牧师本人一分为二,既是陈述的来源,又是陈述的对象。书信和日记这两种对话结构的变体形式在莫里亚克(Mauriac)的小说《蝮蛇结》(Le  de vipères)中得到完美的结合。小说的前半部由主人公写给妻子的信组成,主人公出于怨毒,要她在自己死之后看到这封正在写的信;但出乎主人公意料之外的是,妻子居然死在自己的前面,因此小说接下去的后半部转由主人公的日记构成。书信和日记这两种对话结构的变体形式在这里合理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小说形式探索过程中的经典之笔。 de vipères)中得到完美的结合。小说的前半部由主人公写给妻子的信组成,主人公出于怨毒,要她在自己死之后看到这封正在写的信;但出乎主人公意料之外的是,妻子居然死在自己的前面,因此小说接下去的后半部转由主人公的日记构成。书信和日记这两种对话结构的变体形式在这里合理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堪称小说形式探索过程中的经典之笔。在分析完小说中对话结构的两种边缘实现形式后,再让我们回到小说文本中对话结构最普通最常见的会话形式上。这一形式几乎在所有小说中都有出现,其实现形式一般不外乎以下模式: A说:“……” B说:“……” A说:“……” B说:“……” 依此类推,直至对话结构结束。如果出现多人会话的情况,那依此类推加入C说、D说、E说……即可。这种对话模式的使用是广泛的,甚至可以说直至19世纪这一模式在小说创作中一直都几乎是无处不在的。这里仅分别选取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巴尔扎克的《玄妙的杰作》(Le Chef-d'  inconnu)中的一个对话片段为例: inconnu)中的一个对话片段为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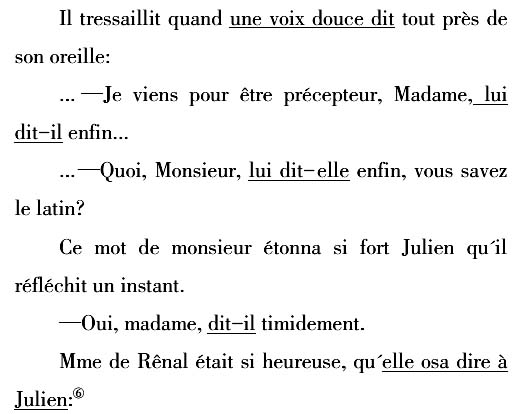 在德·雷纳尔夫人和于连首次相遇的这一对话场景中,虽然只有两人参与对话,但从用下划线作出标识的部分来看,可以发现作者几乎是不厌其烦、一板一眼地遵照这一模式进行写作的(司汤达在这个简单的对话场景中居然没有省略任何一个“XX说”!)。至于巴尔扎克的小说《玄妙的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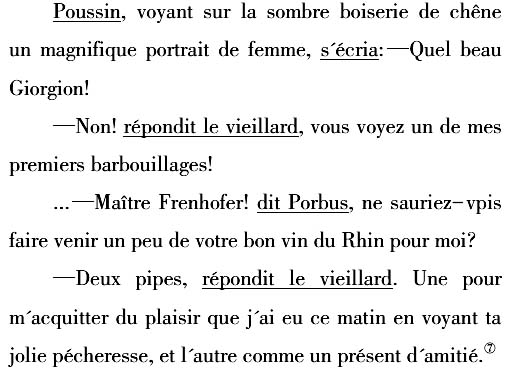 虽然此处出现的是存在两个对话者以上的多人对话场景,但巴尔扎克使用的对话模式并没有大的改变,完全可以被视为两人对话模式的简单升级类推。⑧对于这种在对话结构中不厌其烦地指明是“谁在说”的书写模式,钱钟书亦曾有观察,他指出“西文有引语符号,记言却未克摈‘曰’、‘云’、‘问’、‘答’等字而不用”,⑨“小说里报道角色对话,少不得‘甲说’、‘乙回答说’、‘丙于是说’那些引冒语”,于是“外国小说家常常花样翻新,以免比肩接踵的‘我说’、‘他说’、‘她说’,读来单调”。⑩如上文所举《玄妙的杰作》一段对话中,巴尔扎克便前后共使用了s'écrire/répondre/dire/reprendre四种同样表现陈述行为的不同动词。 不过,依照法文对话的书写习惯,除了上文所提及的一板一眼“A说:‘……’B说:‘……’A说:‘……’……”的对话模式外,在许多小说中尤其是现代小说中的对话,还可能采用一种更简单更灵活的写作模式,即将人物对话单独分行排版,用破折号(tiret)引导直接引语,以达到使对话部分与纯粹的叙事部分分开的目的;相较之下,上文提及的“A说”“B说”轮替出现的对话写作模式,似乎则更多是出于希望突出在叙事行文中插入人物对话的考虑,因此特意使用引号并配合以“他说”(dit-il)之类提示语来标明直接引语的插入。 在此,随意抽取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的小说《地铁姑娘扎姬》(Zazie dans le métro)中一段对话为例。(11)扎姬和莫阿克寡妇的对话来回有十数次之多,但作者只在三处标明了说话者(这三处标志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把作者添写人物说话神情的意图考虑在内)。不难发现,这样的省略处理并不影响读者理解。因为对话结构一旦被发动,在两个对话者交替进行陈述的过程中,两者便依次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场域”。读者只要通过两者所使用的对对方的称谓(在上文中,扎姬用您vous来称呼莫阿克寡妇,而莫阿克寡妇用你tu来称呼扎姬)、对自己的称呼、指示词甚至是说话者的口头禅(如上文中扎姬的口头禅seule mon cul)或是说话时所用语言的语级(如扎姬所用的俚语语级),就可以很容易地进入该对话结构。尽管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中缺省了标识陈述行为的“A说”“B说”,但读者仍可以毫不费力地识别出说话者和受话者在对话结构中的转化过程,弄明白两人究竟是如何交流的。 对话书写形式中,这一特殊的、将指示词“XX说”进行省略的现象,正可以用本维尼斯特在《陈述的形式配置》中所指出的陈述概念来解释。陈述在实现的时候需要满足三个初始条件:即说话者标明自己为说话者,并承担起语言;说话者为陈述预设一个受话者;说话者通过话语进行指涉,并使受话者一方能够参与共同指涉。在上文所述的情况中,在读者的阅读过程里帮助理解、起到作用的,正是陈述的那第三个初始条件:“指涉参照”。作为人称的“我”(je)、作为空间的“这里”(ici)和作为时间的“现在”(maintenant),三者一体,共同构成说话者和受话者“指涉参照”的出发点。“我—这里—现在”三个因素产生于个体性并且只发生一次的陈述行为,因此这三个因素在每一个话语时位之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有新的陈述产生,随即被重新生成,且每次都具有新的意义。而对话中的人称代词、指示词和时态又分别构成了这三个因素在陈述中的体现。(12)所以,通过对话中的人称代词、指示词以及时态,读者便可反推出对话中每一次陈述行为的发起人究竟是谁。简言之,尽管上文对话结构内部并没有出现“A说”“B说”的标识物,但其实每句对话内都已包含“A说”或是“B说”的标识,只不过呈现的方式有时较为明显有时较为隐形罢了。也因此,“A说”“B说”这样的标识物在小说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内的缺省,才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因为在事实上标识陈述行为的“XX说”从未离开过这一对话体系。 当然,如果在同一个对话场景中,出现多人参与对话的情况,那么又可能是另一种情形。例如在让·吉奥诺(Jean Giono)的小说《山冈》(La Colline)中有这么一段对话。(13)在对话场景的前半部分,作者采用的对话模式与上文提及《地铁姑娘扎姬》的选段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参与对话的若姆(Jaume)和雅内(Janet)仅仅分别通过他们在对话中对对方的称呼(黑体部分),就很容易地让读者识别出他们两人在这一对话结构中的各自位置。但是在该场景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却出现“若姆(Jaume)低声问道”(下划线部分)这样的指示词。乍一看下似乎是有些奇怪,但如果将上下文联系来考虑,便不难理解了:这是因为此处有第三者玛格丽特(Marguerite)的加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她打破了若姆和雅内间原有的对话结构,而之后由她和若姆两人开始了另一个对话结构。如果在这里没有出现“若姆问”这样的标记,那么读者将既无法确定这句问话是由谁发出的,也无法确定它是指向谁的。所以,由此看来,如果在这种简约化的对话模式下,突然出现“XX说”的指示词,那么很可能是作者发现此处如不向读者交代清楚说话者的身份,将会影响读者的阅读。 当然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一段落,不难发现玛格丽特在第一个对话场景中的插入其实要更早些,即当雅内说“格丽特,水”(Gritte,de l'eau)的时候,这句话已经将她拉入对话,并改变了原有的对话框架。那么为什么此处没有出现必要的提示词“XX说”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于雅内在说话时,多加入一个呼语“格丽特”造成的。玛格丽特是雅内的女儿,所以雅内会用昵称来称呼她。就由于这个呼语背后隐藏着两人的身份关系信息,所以反倒没有必要再使用“XX说”的标记来特意点明受话者是谁。对于读者而言,只要看到这个隐含着对话双方关系的称呼,即使此时没有“XX说”的标记出现,他们的阅读也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本维尼斯特陈述理论内的“参照指涉”系统概念,后来在巴赫金那里又被进一步扩大边界。巴赫金提出陈述行为“语言环境”的概念,用来标识陈述的暗指部分。他认为陈述行为的语言环境意味着对话者之间的共同视野,通常由时空、语义和价值成分构成(14)。这一“语言环境”的提法,等于将本氏“我—这里—现在”三位一体的指涉概念进一步扩大,把对话结构内部所有包含着的说话者的信息都囊括在内。上文示例中提到说话者扎姬所使用的俚语语级以及口头禅,雅内所使用的“格丽特”的昵称,这些隐含说话者和受话者身份信息的因素,不能被本维尼斯特的“参照指涉”概念所解释涵盖,但是正好落在经过巴赫金扩展补充之后的“语言环境”的概念区域内。 至于为何这种省略“XX说”的对话书写形式会在现代小说中更广泛地出现?也许,这与近现代以来众多小说家在小说中尽力减少叙事者的介入,并力图抛弃全知叙事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这样的对话模式在客观上将叙事者的介入影响降到最低,为读者们留下一个没有叙事者,似乎就是人物们在那里直接陈述的阅读印象。 综上所述,本文从本维尼斯特在《陈述的形式配置》一文中最后留下的开放式结尾出发,根据语言学家对口头陈述和书面陈述的区分,并利用该文所勾勒的形式框架,尝试对小说所包含的书面陈述的复杂话语形式进行分析。文章以一众法语小说为分析对象,运用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和对话结构的理论,最终按照书面陈述中的陈述层面、陈述对象以及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的不同,来重新梳理和归类小说中的对话结构。而在分析小说中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时,我们发现由于交流中主体间性的存在,因此小说对话结构的实现形式中,有时存在着说话人标志“XX说”缺失的特殊现象。陈述行为标志物“XX说”的存在并非是必需,这种更简洁的对话书写形式背后,更隐含着叙事者在书面陈述中暂时隐身现象的小说叙事革新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