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郑振铎的文学史研究 “五四”运动前后,郑振铎受到新思想的浸染,创作小说,撰写杂文,介绍西方文学,整理传统国故,表现出一个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宽广视野。郑振铎的兴趣很广泛,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追求,又有他的聚焦点,即对一切表现人类美好心灵的文学艺术作品情有独钟。譬如他生命中最后一部著作就是《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14]。当然,在他涉猎的所有学科中,自始至终,倾其毕生精力的,还是文学史研究。他的文学理想,他的学术实践,都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得到充分展现。《文学大纲》是世界文学的比较发展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表现出他对木刻版画艺术的深刻理解,《中国俗文学史》则贯彻了他的大众文学思想以及文学为社会、为大众服务的崇高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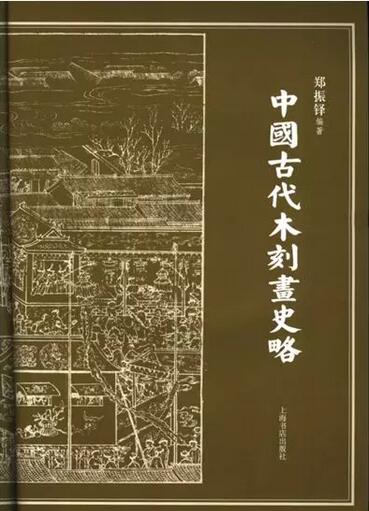 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2006年版 (一)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早年,郑振铎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认为文学史研究不仅要指出某部作品的价值及该作品在某一时代或某一地方所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要注意把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人种影响下文学作品所蕴含的人类思想情绪的进化与变异痕迹充分展示出来[15]。30年代,他发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继续阐述这种主张,认为文学研究要注意作家、作品、时代、文体几个方面,尤其要注意一个作家的文学思想,一个时代的进化观念。这一文学主张源于泰纳(Taine,1828-1873),强调文学研究要注意种族、环境、时代三个要素。所谓种族,是指一个民族在生理与遗传学意义上所具有的性格、气质、观念等体现出来的本质特征。所谓环境,是指塑造人类性格的外部力量,包括地理位置、气候状况等。所谓时代,是指一个种族中所有过去经验的积累[16]。从总体上说,大体不出进化论范畴,在当时自有其进步意义。譬如,从时代环境来看文学作品,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就超越了以往有关《金瓶梅》的研究,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长期以来,《金瓶梅》被视为淫书,历来评价不高。郑振铎则入木三分地看出《金瓶梅》“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这是因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了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这是把《金瓶梅》作为社会史资料来看待。更何况,《金瓶梅》的社会并不曾僵死,其中的人物们至今还活跃在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17]。就我目前所看到的材料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金瓶梅》研究,从总体上来说,似乎迄今还没有能出其右者。 抗战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指出,撰写文学史,“原则之一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服从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的。生产工具与生产力的进步,推动了生产关系的改变。而生产关系的改变,便影响了上层建筑的发展。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等等,人类的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基础改变了,上层建筑的面貌也就随之而改变了。‘历史’就是记录和表现这些‘改变’或发展的。文学史乃是历史的一部分,乃是记录文学创作这种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的,她乃是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原则之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既然是服从于基础的改变,故一般的发展规律,是没有例外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的特殊性”[18]。既注意到决定文学艺术发展的经济、社会的普遍因素,又注意到一个国家、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见解更加圆融深刻。 (二)中国文学分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杜威等人的文学分类法在中国影响很大。诗歌、戏曲、小说、论文、尺牍、讽刺文与滑稽文都还可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找到对应作品,而演说及杂类就很难对上号。为此,郑振铎最初将中国文学分为6类,试图有所突破:诗歌(包括韵文的与散文的)、小说、戏曲、论文、个人文学(尺牍、自叙传、回忆录、日记、忏悔)、杂类等。后来增加到9类:总集及选集、诗歌、戏曲、小说、佛曲弹词及鼓词、散文、批评文学、个人文学、杂著(包括演说、寓言、游记、制义、教训文、讽刺文、滑稽文)等。这种分类虽然不及一般文学史分诗歌、小说、戏曲、散文四类那样明晰,但是他注意到总集与选集,注意到佛曲弹词及鼓词类,最具新见。中国早期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总集和选集保存下来的。譬如《诗经》《楚辞》就保留了先秦时期的重要诗歌作品,已经成为经典。《昭明文选》《玉台新咏》是留存至今的唐代以前最重要的两部文学总集,是唐前文学研究的渊薮。论及中国文学,是不能不从总集和选集开始的。更何况,中国文学总集和选集,并非只是文学作品的简单堆积,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和精微的文学批评,是文学经典化的一个重要环节。鲁迅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博览群籍,采其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集,一法也,如《文选》是。择取一书,删其不合于自己意见的为一新书,又一法也,如《唐人万首绝句选》是。如此,则读者虽读古人书,却得了选者之意,意见也就逐渐和选者接近,终于‘就范’了。”[19] 至于佛曲、弹词及鼓词,更是以往文学史所不曾涉及的内容,就是在今天的文学史著作中,这类作品也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20]。作者将他们归为一类,确实与众不同。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郑振铎将俗文学分为五类。第一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敦煌歌谣收录其中。第二类:小说,专指话本。包括短篇的三言二拍、长篇的讲史、中篇单行的。第三类:戏曲,包括戏文、杂剧、地方戏等。第四类:讲唱文学,包括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等。第五类:游戏文章,有散文有辞赋,如《僮约》《燕子赋》等,皆为首创。 (三)文学史的新资料 郑振铎所以关注佛曲、弹词、鼓词以及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20世纪文学史资料的新发现密切相关。如前所述,20年代后期,郑振铎游学欧州,在各大博物馆看到很多流失海外的中华文物,特别是敦煌千佛洞所藏古代写本,给他很大震撼。敦煌写本中除民间俗曲、写本佛经及词调外,还有《舜子至孝变文》《目连救母变文》《降魔变文》等,“自其上皆明书‘变文’,始知变文即其本名”。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种韵散兼并的文体,直接影响到宝卷、弹词、鼓词、诸宫调等讲唱文学体裁的发展。正如作者所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改变了一个方向,那便是不袭用‘梵呗’的旧音,而改用了当时流行的歌曲来作弹唱的本身”[21]。受此启发,他特别关注新资料的发现和应用。《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指出,韦庄的《秦妇吟》,让人们了解到唐末混乱的时代。屠隆《修文记》传奇在乱书堆里被搜出,可以使我们对于明代三教混合运动有所了解。还有向来无人注意的《林子全书》《混元教宝卷》一类的东西,让善良的人民看到,那些别创一教的野心家,是如何利用旧形式给平民输灌教义,改造思想[22]。1932年,郑振铎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将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新资料加以论述,别开生面。同时,他又注意避免胡适《白话文学史》研究的缺陷:“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只是白话文学的发展。执持着这样的魔障,难怪他不得不舍弃了许多不是用白话写的伟大的作品,而只是在发掘着许多不太重要的古典著作。”[23] (四)文学史的新视野 新资料的发现,改变了中国文学史的固有格局。1938年,郑振铎出版《中国俗文学史》,开宗明义就从俗文学定义开始,认为除诗与散文外,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可归到俗文学范围里去,成为中国文学史的骨干。他认为,中国俗文学有六个特质:一是大众化,二是无名的集体创作,三是口传性,四是鲜活与粗鄙并存,五是想象力丰富奔放,六是善于引进新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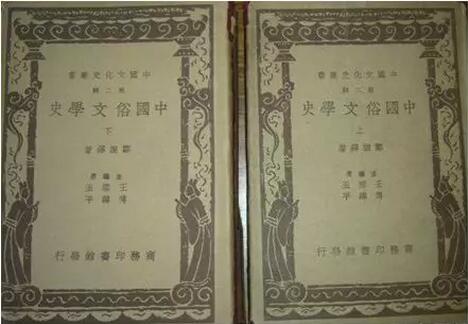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20世纪初对于平民文学的重视,引发了学术界对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的热情。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都对民俗学与人类学抱有兴趣。周作人有《童话研究》,茅盾有《神话研究》,郭绍虞有《谚语的研究》等。郑振铎早年翻译《民俗学浅说》,发表《再论民间文艺》《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等重要文章,凭借着希腊神话学的修养,为民俗文学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后来,他创办文学研究所,将民间文学研究列入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