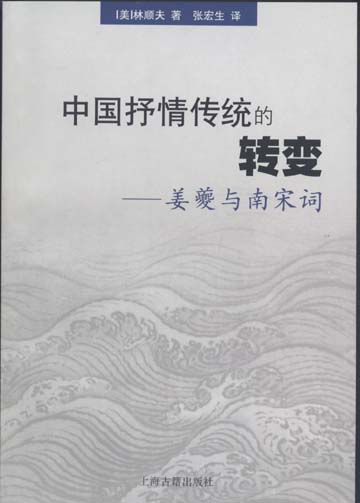 一部将近三十年前用英文写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性著作,居然在此时出中文版,有机会跟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令我感到无比的兴奋与荣幸。此书能以中文版刊行,都是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的功劳,因为从翻译本身到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交涉出版,全凭他一个人的努力。在此,我首先得向张教授表达我铭心的谢忱。同时,对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高克勤先生和责任编辑袁啸波先生,在出版本书时所表现的对学术工作的支持及认真办事的态度,我也非常感谢。此外,在准备出中文版的过程中,密西根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曾给本人宝贵的资助,在这里我也要表达衷心的感激。 一部将近三十年前用英文写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性著作,居然在此时出中文版,有机会跟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令我感到无比的兴奋与荣幸。此书能以中文版刊行,都是南京大学张宏生教授的功劳,因为从翻译本身到与上海古籍出版社交涉出版,全凭他一个人的努力。在此,我首先得向张教授表达我铭心的谢忱。同时,对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高克勤先生和责任编辑袁啸波先生,在出版本书时所表现的对学术工作的支持及认真办事的态度,我也非常感谢。此外,在准备出中文版的过程中,密西根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曾给本人宝贵的资助,在这里我也要表达衷心的感激。我是在1996年冬天跟张宏生教授结识的。在结识前不久,我收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莫砺锋编的《神女之追寻》一书,里头有题作《姜夔对于咏物词的追求》一章,其实是张宏生中译拙著的第三章。该章是拙著里比较难读的一章,然而张宏生的中译,读起来却是既精确又流畅,令我感到异常痛快、佩服。当时,我心中就极想有机会认识这位对拙著感兴趣的学者。做梦也没想到,收到莫砺锋书后不久,我就接到张宏生来信,说他正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有机会很想跟我见见面。碰巧那时候正因有事我预备到离哈佛大学不太远的Tufts大学去开会,我就回信约他,如果方便的话,等我Tufts办完事,我们就在哈佛校园附近见面,并一起吃晚饭。于是我们就在12月16日晚上在一家中国餐馆相见。这一顿饭与谈话就持续了两三个钟头,“一见如故”这句老话真可以拿来形容我们第一次相识欢谈的景况。张宏生平实恳挚的谈吐,深博的学养和谦谦君子的风度,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他跟我说,拙著是他老师程千帆先生介绍他去读的。同时他也说,他将来会尽力把拙著全部译成中文。最近十年来,也有两三位年纪比我轻的学者,向我表示要译拙著的意图,我都对他们说有位卓越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早已开始翻译了,而学术性著作的市场既然是有限的,拙著将来有部中文本也就够了。我也跟张宏生一直保持联系,知道他翻译的工作从没放弃过。 本书的英文版是于1978年在美国出版的。书的前身是我的博士论文,于1972年完成并提交。1967年我来美国留学,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东亚语文学系,而攻读的范围则以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史,以及现代英美文学文论为主。我的博士论文是很集中地分析姜夔词结构的一篇作品。论文完成后,自己觉得对于姜白石词的结构分析及其成就的历史定位,还是须从文化史的宏观视角来研究才有意义。所以,1978年出版的书,跟1972年交出的论文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可是,学术研究是不断向前进的,而三十年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出版于1978年的拙著,也应该让人把它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取自张宏生序)去看、去评价了。说至此,我要特别提一提张宏生为了这书的中文版而写的长序。张宏生确实很认真地把拙著当作一种历史现象来看待,而且序里评、介兼顾,对本书的读者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有他这篇精辟的长序,我觉得自己也就无需在此多加废话了。 在结束此短序前,我想提一件事。拙著的稿子于1976年夏天完成时,曾寄呈给我的普大老师牟复礼先生,请他指正。牟先生于来信中说了些称许的话后,提出拙稿颇为“understated”一点,即论述不够强有力,没把实情充分地表达出来的意思。因为时间与自己学力都有限,我后来对于牟先生所指出的弱点,也没有作太多的改进。牟复礼先生是对我一生治学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他三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犹清晰在耳,而他人竟已于今年2月10日归道山,想及此事,令人感慨! 林顺夫谨识 2005年5月21日 于美国密西根州安阿堡城 (责任编辑:admin) |
